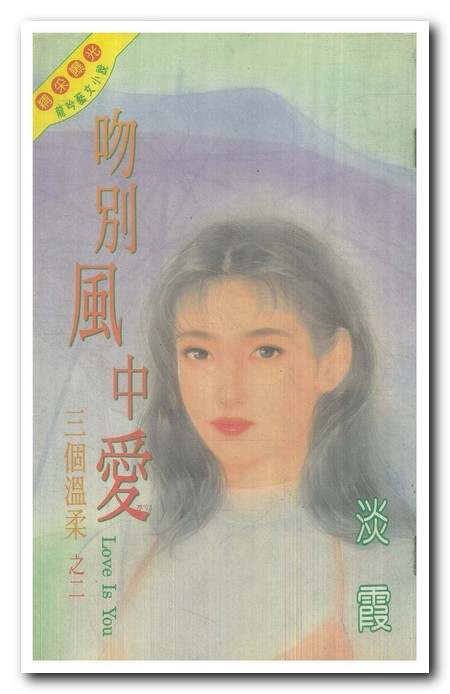the peeperby很好很酷不ok(现代)-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画面上□□的两个人跟袁梁在老家街上看过的野狗并没有区别,唐非差不多整个人都被朱旻遮住了,纠缠在身体两侧的手看上去痛苦而又享受。感觉愉快。朱旻既然是闷骚的处女座,健身这种自恋的活动必不可少,虽然这两年很少练了,胳膊还是很有料,基本上摁住谁谁就没跑。唐非不像样的挣扎了两下也就随他去了——既然这么喜欢朱旻的体温和亲吻,就干脆点承认喜欢朱旻,坦白的拥抱,何必矫情?
袁梁认真的看着,隐约间,意识从躯壳里短暂的剥离出来,有那么一刻半刻的,他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样的唐非并非难以接受,他可以很自然的把这看成是唐非的一种形态,以前他没发现过的那种,就像小时候在抽屉里乱翻,偶尔找到一块陈年的硬糖,便当成宝藏一样珍惜。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是朱旻。
他起身收拾一地狼藉的晚饭,重新把显示器排排好。卷起脏污的地毯,脱下拖鞋和袜子,连同墙角那个之前砸坏的显示器一起拿出去丢掉。想了想,又把地毯拿了回来。
外面非常冷,关门的时候他忍不住向对面看去,不过不是拉紧了窗帘的二楼,而是他曾踩过的楼梯,抚摸过的大门。钥匙在他口袋里,烫得就快藏不住了,他忽然有种冲动,想笔直的走过去打开门,弯下腰抚摸摇头摆尾的一休,然后抱着它上楼,打开卧室的门,边脱下外套边对地上摆弄相机的唐非说:“我回来了。”
唐非也要像那样笑才完满。
但如果唐非要那样笑,为什么不是对我?如果唐非一定要改变,为什么不是为我?
袁梁回到浴室里继续工作,硬盘里那本小说,他得整理一下思绪才能接着往下写。浴缸里不停冲洗的水已经淡的看不出颜色,周小鑫送他的那把小锯子非常锋利,袁梁怕会割伤手,还在锯子柄上缠了一条毛巾。他换上拖鞋,蹲在地上忙了一会儿,十分钟不到就气喘吁吁。浴室里太闷了,他想。还是搬到楼上弄吧。
地毯已经撤掉,卷在浴室一角。他找了很多旧报纸,再铺上一叠一次性的塑料桌布,然后才把东西抬上来。窗帘全都拉紧了,不好,他先是全都拉开,又再阖起一半,天早就黑了,玻璃上除了自己苍白的倒影,只有对面C7朦胧的窗。袁梁想还少些什么呢?哦对。跑过去把四个显示器全转了过来,朝向自己。
手机上有一条周小鑫的留言:“哥你还生气呢?我给你订了一个新显示器。超大。我绝对不去打扰你,你好好写,真的,快顶明天就能送到,你放心,这本书的事我一点都不跟她透露。”
袁梁放下手机,埋头苦干。
朱旻也在埋头苦干。□□的时候唐非用虎牙狠狠咬他,心里用各种方言说我操,却搂紧了朱旻的肩膀。朱旻摸索着捏住了唐非踩在他屁股上的脚丫子,低低的喘息着,笑了。
完事唐大爷敛足的推开朱旻,在床头柜上摸出烟和打火机,支着胳膊点燃。朱旻那么大一只,占够了便宜却装得像是被开苞的娘们,偎在唐大爷腿上装死。
袁梁斜着眼睛看他们,看见朱旻摸唐非的肚子,那胳膊确实很结实,充满了撕裂般爆发的欲望。
他于是对着反光的玻璃窗看了看自己。提着锯子的他,孱弱无力,像个鬼。
也许他该学学朱旻。不。也许他可以就是朱旻。
锯子上一滴水滴下来,很淡很淡的那种粉。
section 6
袁梁开始观察朱旻。他第一次注意这个人。但实际上他观察的也并非是朱旻本身。他想知道的无非是一个方法,能让唐非接受他,能让唐非听话。原本他只是看着,胆怯瑟缩,但现在他已不满足于仅仅看着,他开始有了点自信,或者说有了点执念,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取代那个人,站在唐非身边。
只是他不知道要怎样开始。唯一的借鉴,是看朱旻怎样和唐非相处。
朱旻早晨不做饭。唐非和他都是喝牛奶吃面包的。偶尔忙的忘了去超市补货,常常就要度过一个饿肚子的早晨——唐非是绝对想不起做这些的,只有朱旻自己记着。遇到断粮这种可怕的事,朱旻就赶着早晨上班,路过哪儿随便买个麦当劳,唐非则理所当然的一觉睡到中午,电话叫个外卖,两顿直接并一顿了。用唐非的话说,还省钱。
朱旻穿西装。有时候打领带,有时候不打。刚和唐非在一起的时候,多少还有点天真。骨子里还想追求个浪漫,一时脑抽试过商量唐非,让那双艺术家的手给他打个领带。唐非倒没拒绝,光着膀子叼着烟,拉领子一把拽到跟前,三下五除二,打了个蝴蝶结。回头还不许哭笑不得的朱旻解开,推开了照着屁股就是一脚。现在激情耗尽了,两个老爷们纯过日子,早上朱旻自己忙自己的,爱打条纹就打条纹,爱装金钱豹就装金钱豹,一面还得顾着床上那位在中国过美国时间的唐大爷。
“牛奶我又顺手给你热了,你起来记得再热一遍。”穿衣服路过床边,正好看见唐非露在被子外边的脚丫子,捏一把没够,一跐溜钻回到被窝里,照着唐非大腿就是一口。他行为虽然表现的非常大尾巴狼,说的话却是奶妈的台词:“别总是喝凉的,你也不怕得胃病!”
“我靠!”唐非的睡意活活被吓跑了,一激灵缓过劲来,翻身就拿枕头往出丢,“凉!没你凉!滚!”
打没打着,踹也没踹着,朱旻躲在门后边得意的□□,抻抻领带,下楼找他钥匙和电脑包。
袁梁听不到,但看到。
唐非白天一般四件事,睡觉、开会、挑照片、拍照。最近他接了个活,在徐泾拍一片预备放盘的别墅。国企炒地捞钱的土老帽,盖的房子也是土老帽。三层八百来坪,五千万到一亿一栋,能看得到的地方全是石料,放眼一搭五十四个石头疙瘩堆得黑乎乎一片,死死板板,整整齐齐。唐非一看就明白了。营销公司真没出错注意,这水准也就能到二线城市糊弄糊弄暴发户了。真在上海待过的,谁有四五千万买北九亭?不过这倒还不是卖不出去的根本原因。关键是设计没做好。唐非只是个玩摄影的,没科班碰过构图,但就算是他也看得出来,环境和结构设计是真没做到位。他拍过的好房子多了,就这个,除了大点,还乱摆谱把楼梯间弄的跟个小型游艇似的,把房间挤得贼小,活像一间间鸽子笼。比九间堂的装深沉差远了,比静鼎安邦的小巧精致更是想也不要想。
连着拍了几天室内,都是摆拍,演员、家具,搬来搬去,唐非也嫌活儿没劲,腻烦,这事要不是哥们拜托,他才不干呢。天气一直不好,连着降温,到这礼拜连雨夹雪都飘上了,外景压根没戏,还得往后拖。唐非看上去比急着回笼资金的开发商还着急,就望着赶紧把事结了,烦死人。
袁梁跟了他两次,汇贤阁——就是唐非拍片子那别墅区——管的非常严,他根本混不进去。但是他看见过唐非的臭脸,等交通灯的时候,想来是相当不顺,就等着找人发火呢。袁梁也跟过两次朱旻,纯为研究。公司、客户,跟男的女的嘻嘻哈哈,转头就搬出公事公办的脸。朱旻这个人看着随和,其实不比唐非容易接近。唐非是那种跟你不熟跟他也不熟,但不熟不熟也就熟了,走的地方又多,朋友满天下,好话孬话,嘴上不爱说,关键时候却真把你放心上。任人都能竖大拇指赞一句:小子仗义,外冷内热。朱旻则正好相反,熟着熟着,其实根本不熟,也不预备熟,认识多少人,跟谁称兄道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他真把谁放在心上过?他是外热内冷,你要真当他多在乎你呢,回头就让你栽跟头。倒不是说他阴,他办事还真就光明磊落,不搞那背后坑人的说法。但也就仅止于此,贴心的朋友,最贴也离的八丈远,劝你千万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太当真了到了伤得还是你。朱旻看人相当拎得清,他是自己站在圆心上,漫不经心的四处寻摸,其他一切,一视同仁,统统搁圆周上蹲着,像被神睥睨的众生。只有唐非一个人挪啊挪,慢慢就跟圆心重叠了,这种结果,估计连朱旻自己都没料到。
你以为朱旻有多么多么成功,多了不起。也没有。那纯粹就是性格作祟。虚伪、矫情,甚至装逼,或者你觉着这么说实在狠了点,但人家能连虚伪、矫情,甚至装逼都装得四平八稳,这就是牛人。
袁梁不懂这些。如果说一般人一知半解,看着朱旻只会肤浅的羡慕,表面不屑或者干脆连不屑都省了,转头就便模仿。再如果说还有些人,那真是因为了解了一点儿,便从心底里鄙视这恶心人的伪装,表面虚与委蛇,转脸就大骂他不是东西。袁梁纯粹多了。他只是为模仿而模仿,并不懂得常态的道德标准,也就不会做任何道德评判。对他而言,朱旻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帮助他得到唐非的手段,一条带引他通向唐非的捷径。
他学朱旻的穿衣打扮,举止表情。买了朱旻穿的西装,朱旻戴的手表,朱旻的领带看上去都差不多,但仔细看总有些微的差别,装也装的不露痕迹。学朱旻把头发剪短,头顶弄得根根直竖,台风都刮不塌。他还预备要把他的破本田卖掉,换一辆和朱旻一样的A6,他都忘了自己不会开手动档的车。袁梁以一种全然自我放弃的姿态,照着朱旻的样子把自己武装一新,对着镜子审视自己,却怎么看怎么别扭——袁梁可以不像袁梁,但袁梁怎么可以不像朱旻!
还是不像。完全不像!袁梁对着唐非冷雨地里留下的两道泛青的车胎印发了一会儿呆。他不明白为什么不像。
雨从昨夜开始,始终没有停。但唐非出门却是带着相机和防雨布的,袁梁感觉他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冲动就又来了。抓着钥匙的手不住的发抖,他无法克制表情又怕又笑,任凭脸颊上麻木的肌肉彼此牵扯成扭曲的、令人反胃的鬼面。
他心里住了一只渴望的兽,那天之后他就迷上了这种被唐非的气味完全包围的感觉,他处身于唐非的家里,暗房里,沙发上,床上,陶醉的忘乎所以,以至于重新回到他那阴暗肮脏的D7时,吸光了胸臆间留存的唐非的气味,根本无法继续呼吸。
只好整夜做鬼。不停的切碎,不停的煮食。
进门的时候他很小心。倒不是害怕留下痕迹会被发现。那只是一种习惯,他讨厌任何东西湿淋淋的样子。总想放到微波炉里烘干。
“汪!”一休只叫了这么一下,再就停在他身前一米开外,似乎又警惕又忍不住期待,小尾巴有一下没一下的摇着。倒是不陌生,袁梁已经来过好几次,每次都有好吃的讨好它。
“一休。”袁梁放下东西。靠在

![你是我的禁果[最全he 完结+番外]封面](http://www.diditxt.com/cover/31/3181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