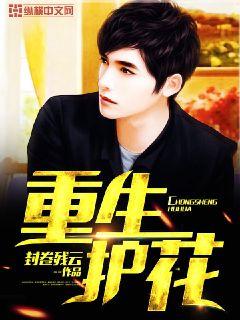重生之雍正王朝-第9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着啊,”那二百五的账房先生也来了精神立刻接道:“所以我家老爷才要修堤坝来着。”
胤禛一笑,顺口问道:“你家修了多长的堤坝?”不等李禄全答话,账房先生又插嘴道:“大概二里多地罢。”惹得李禄全心中一阵恼怒,当着胤禛又便发作,只能恨恨地想:待回到家中,一定撵了这个不着调的账房去。
胤禛又问道:“本县延混河一线有多长?”
账房终于注意到李禄全的一张黑脸,犹豫了片刻,没有再张嘴。年羹尧戏谑道:“李二老爷既是本地乡绅,自然应当知道答案了?”李禄全即便再愚笨,此时也猜到了刚才胤禛那一席话的用意,权衡了片刻,终于一横心道:“本地延混河二十余里。小的想过了,同为乡亲,小的不能只顾着自己一家。小的愿意为朝廷、为本地百姓出钱出力,修筑堤坝,造福乡里。”
“甚好!”胤禛闻言而起赞道:“若是李家果能如此,我当上折子请下皇命,将此堤定名为‘李家堤’,以表彰你李家两兄弟的义举!待到那时,便不是你沾李德全的光,而是李德全要沾的光了。”言罢,竟亲自扶了李禄全起身。有当今皇子这一扶,直教李禄全喜笑颜开,顿时觉得全身骨头没有二两重。
此时,几人才分宾主坐定,重让店小二热了酒菜,席间年羹尧又叮嘱李禄全二人不可擅自泄露胤禛的行踪。胡乱吃了小半个时辰,李禄全便满面堆笑地告罪离去了。透过雅间的窗子,看到李禄全舍了轿,气喘吁吁地带着从人远去,胤禛三人相对会心地一笑,也轻松了一口气。
第一百六十三章 国事家事(一)
在保定、霸州一带足足盘桓了二十几日,胤禛才带着宝柱和年羹尧返回京城。回到自己府中,刚喝了小半碗冰镇桂花绿豆汤,还没和乌拉纳喇氏说上两句体己的话,就见秦顺站在花厅外朝内张望。胤禛府上的规矩一向甚严,除非有要事,秦顺断不敢在这个时候打扰。
胤禛苦笑,随手将碗放下,冲着秦顺轻斥道:“也不知道让你主子享几刻清闲,还傻愣着做甚么?有事就进来回事儿!”秦顺干笑着进来打了个千,道:“于成龙大人听说主子回了京,这会儿已经在府门外候见。奴才知道主子这会儿必然疲累,见不见于大人,奴才不敢自专,还请主子示下。”
胤禛面孔一板,道:“怎么,这么多话,想在你主子面前邀功还是怎的?速去请于大人前厅用茶。爷去更衣,稍后便至。”顿了一下,又吩咐道:“去把年羹尧也寻了来。”秦顺吃了训斥不敢再多言,“着”了一声便往前院走去。
胤禛起身去更衣,却见乌拉纳喇氏一副似乎欲言又止的样子,便堪堪地停了步,道:“芸娘可是有话对我说?”乌拉纳喇氏犹豫了一下,才道:“妾觉得爷对府内的下人许是苛了些。”胤禛一楞,道:“芸娘这么认为?”乌拉纳喇氏缓缓走到胤禛身边,道:“有些事本不是妾该置喙,但事关着以后府内的安宁,妾还是不得不说道一二。爷对着那些奴才鲜有好脸,常常只罚不赏,日子久了,有些人不免生出些嫌隙,若真是与爷离心离德,便不免被人利用。”
胤禛心头一沉,沉吟道:“即如此,倒要费些心思琢磨咱们的家事了。此刻于成龙在前厅相候,倒不好让他等得太久,稍后还相烦芸娘细细再说与我听。”
匆匆换了身干净的皇阿哥四团龙服之后,胤禛便即来到前厅。于成龙有些拘谨地打偏坐着,手里半端着杯茶,却怔忡着没有往嘴边送,不知其时神在何处。胤禛轻咳了一声,才将于成龙的思绪拉转回来。于成龙连忙撇了茶,上前告罪见礼。胤禛上前扶住了,细细打量了于成龙一番,道:“自上次前营一见,振甲瞧着似乎又清减了些。晓得你运粮辛苦,本该好生让你将息几日。只是这治水一事,数朝野之中,舍振甲而其谁?太子爷亲点得将,振甲又要辛苦了。”于成龙连称不敢,道:“四阿哥此言折杀臣了。臣前几日到京,太子便传见交待了差使。臣到府上求见,才知四阿哥已往保定府探查水情而去。四阿哥如此勤勉,让臣甚感愧疚。”胤禛微微一笑,道:“我与振甲不同。于大人是治水能臣,我却空顶了个坐纛的名头,若是不提早做些功课,岂不成了尸位素餐之流?”
这时,年羹尧也提了一个包袱来到前厅,向胤禛打了个千,又以后辈之礼见了于成龙。于成龙略知他与胤禛的交情,且原先在前营也有数面之交,此刻便微笑着寒暄了两句。三人便分宾主坐定。于成龙便对胤禛、年羹尧道:“四阿哥对浑水之治有何章程教于臣?”胤禛指了指年羹尧带入的那个包裹,道:“振甲太过谦了。我与亮工、宝柱走了这一回,无非对浑水一系水情小有些心得而已。我将我三人所见,与当地县志等相关记载做了对比,写了几卷笔记。不知能否入得于大人的法眼?”
年羹尧于是将包袱打开,捡了一本递给于成龙。于成龙接过,粗翻了两页,便为其中记述之详细而感叹道:“常听人说四阿哥心细如发,如今看来,果名不虚传。笔记之中,上至水流走向、缓急,下至水中泥沙几何都是一目了然。”年羹尧笑道:“于大人说的是。四阿哥每到一地,便与我等细细沿河查看,这些天走下来,腿都细了一圈。每隔两里地,还要从河中舀出些水来,待其澄清之后检视泥沙沉积。以此对照着工部所堪浑河水系图沿河探查,竟发现了几处谬误。”于成龙颔首道:“有四阿哥和年世兄如此,何愁水患不除。观笔记之中所录浑水之势,与黄淮甚似。四阿哥,想昔年臣与靳紫垣之争,历经这十年浮沉,方知其法为治水良谋……。”
看着于成龙追忆之时颇有些懊恼之意,胤禛出言劝慰道:“振甲不必太过介怀。紫桓临去之时,不是特意将穷一生心血的治河十策交与你了吗?若是紫桓心存芥蒂,又怎会有此一举?”于成龙有些黯然地一笑,道:“四阿哥,臣唐突拜访,实是有一桩难事要求四阿哥。”见胤禛并不言语,面上似笑非笑,知自己之言太过贸然,按制朝臣不得妄交阿哥,也难怪胤禛如此,忙解释道:“怪臣言之不详。太子要四阿哥与臣一道治浑水,臣自欣然领命。然臣去户部,却被告知只可拨于河工两万银。依臣过往之经验,若要河务大治,没有十万银断不可为。臣与户部会商,户部只一味推说因朝廷两战葛尔丹,户部存银无多,断断再拨不出钱来。”胤禛心说,难怪于成龙屈驾到此,竟是为了此事而来,于是斟酌着道:“常言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也难怪于大人心忧。于大人可有将此事报于太子?”于成龙面露尴尬之色,道:“臣与太子说了,太子说,这次四阿哥掌总,命臣,命臣……。”胤禛真的只有苦笑了,难道太子以为自己是善财童子不成?足足差了八万两,即便扣去了忽悠李禄全的不算,至少还要再筹集七万余两。怪不得太子点了自己的差事。可是眼下诺敏已不再执掌户部,只剩下一个四品的主事戴铎,眼见得做不了这笔银子的主儿,还能到哪里去寻摸了这些钱来?胤禛皱紧了眉头。寻在京的王公贵胄乐捐?这若是在寻常时候,倒也不失为一招,只是目下几乎所有的宗亲都随着康熙出征去了,府里没有做主的人,难道要厚着面皮去寻女眷讨钱不成?这可真有些费思量了。
第一百六十四章 国事家事(二)
送走了愁云满面的于成龙,胤禛只觉得牙根处有些发紧,舌头轻舔了一下,竟是有些上火肿了起来,心中免不得懊恼了一番。想来还是保定这一趟有些疲了,再加上这短缺的八万黄白之物,竟惹得自己一个皇阿哥狼狈至此。胤禛轻叹了口气,吩咐秦顺取来贡菊、山楂、百合三样,泡了一杯清火的茶水。见胤禛不停地揉着脑仁,年羹尧凑上前道:“四爷,银子的事儿,您用不着这么犯难。再不济,要直隶各州府县摊在税赋之中便是。左右是桩利国利民的好事,百姓们……。”看着胤禛慢慢冷下去的眼神,年羹尧不敢再说下去。
“你糊涂!”胤禛眉头紧皱,斥道:“如今朝廷二征葛尔丹,国库吃紧之余,除西北及福建外,诸省已是多加了一至两成税赋。加之有些官员借机贪渎,百姓已在时时叹息‘苛政猛于虎’了。若是再为了此事加税,继而酿起民变,便是你我万死莫赎之罪过!”胤禛说到最末一句,突地想起乌拉纳喇氏的劝谏之词,便和缓了声色,道:“亮工,你是我的人,故爱之深,责之切。我盼你能望得高些,见得远点。我曾对你说过,假以时日,你比你阿玛的出息只怕更多些。”胤禛顿了一下,又道:“前几日,我就拟好了给皇阿玛的请安折子,禀了你与宝柱随我至保定府探访水情之事,也提了欲送你参加今年秋闱。皇阿玛多半会加恩于你,也算了了你跃龙门的心愿。这份折子我今早回府时就已命人送出去了。”
年羹尧初时被训得塌头耷脑,此刻听着温言抚慰立觉热血汹涌,当下跪地叩头道:“奴才何德何能,有主子如此眷顾!奴才结草衔环都难报万一。”自年羹尧在前营充作使节立下大功,却多少因胤禛之故未得赏赐之后,他虽仍对胤禛执礼甚恭,却很少再称胤禛为‘主子’,只是跟着宝柱叫‘四爷’,难说有了几分自外的心思。此时,年羹尧在激动之下,复又喊出‘主子’两字,倒让胤禛心头一动。虽说戴铎和年羹尧之前俱以胤禛门人自居,又都是胤禛最为倚重的人,却始终没有真的在宗人府报备。名不正言不顺,时日长了,人心总归隔肚皮,胤禛还是少不得要防上一防。现如今自己正式开了府,应该是时候正式确立这层隶属的关系,这样也能对他们有个约束。
胤禛拿定了主意,便道:“亮工,几年前,裕亲王就有意把你一家拨到我的佐领下。如今你既称了我为主子,我可就当了真,你阖府上下可是已然拿定了主意?”听了胤禛这句问,年羹尧明显楞了一下,沉吟了一下,终是下了决心,道:“奴才一家,早在那年和主子偶遇,便已注定要追随主子。只待主子行文宗人府,便举家入主子门下。”胤禛想了一想,道:“得了,你毕竟不是家主,先别说这满口的话。我不逼你。你写封信给你阿玛问过再说。”“是。”年羹尧又叩了个头。
胤禛顿了一下,问道:“你阿玛在任上几年了?”“已有四年。”年羹尧恭谨答道。胤禛微微一笑,道:“据说他官声不错。改日我去和太子撞个木钟,瞧瞧还有没有巡抚的缺儿。既然你家准备归我的门下,我这做主子的,总得有个见面礼不是?”虽说年遐龄此时已是一省藩台,却不过是个方面之员,升任巡抚,可就算是封疆大吏了。这一步,看似只是半级品轶之升,却对于大多数官宦而言,是如同跨越天堑的一步。若是以后能再加兵部侍郎或右都御史衔,那便能进正二品。继而进中枢为台阁,便再也不遥不可及了。
看着年羹尧千恩万谢的退了下去,胤禛笑容慢慢敛了去,靠在座椅之上只觉得疲累不已。胤禛闭上了眼睛,他真的觉得心累了。自重生以来,他便处处用心,时时提防身边所有的人。他只觉得眼下的自己似乎与前世的那个小职员渐行渐远,变得忧郁、漠然甚至有些冷酷,这还是自己吗?头似乎越来越痛了。正痛苦着,旁边突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