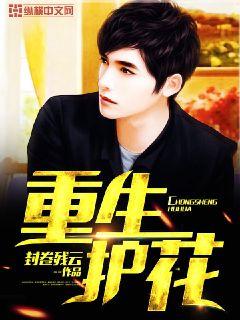重生后我回苗疆继承家业-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种事情一旦坦白,接下来的结果不是他能决定的。巫嵘讨厌失去控制的感觉,也不想受到任何束缚。
无来由的,巫嵘想起了傅清。
只有他能看出自己已死面相,说不定也能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有所了解,周巡正站在他面前却一点感应也没有,如果真是那能捏碎雷霆的大凶鬼煞,就算说出来也没有丁点办法。
见周巡还在看他,巫嵘顿了顿,目光落到他空荡荡的左臂处:“你的手……”
“哎,断了胳膊而已,没丢命算是好了,到时候再长一只就行。”
没想到巫嵘竟然会主动关心,周巡有些受宠若惊,他晃了晃衣袖,浑不在意:“现在回程的道路断了,咱们只能在招待所待上一段时间。你不是要回西江吗,这里也差不多快到了,等养好伤可以让你家人来接你。”
“嗯。”
外婆在的寨子不在西江,而是在更偏远的深山老林,几乎完全没有外人发掘的原始苗寨。西南边陲多山,古时候有十万大山的说法,山高路险,交通不便,除非寨子里的人出来接,否则肯定会在大山里迷路。外婆古板保守,这辈子都没有出过山,只是寨子里有些年轻人外出西江打工,做些文化演出之类的。
本来说好的是等列车到了西江会有专人来接巫嵘,但谁想路上出了这么严重的事故。
周巡细细跟他说了些养鬼初期可能遇到的小问题,例如半夜鬼压床啊,看到纸钱闻到香灰就想吃之类的,随后叮嘱巫嵘好好养伤便离开了,留下巫嵘一人呆在房间里。
他低头看向自己缠满绷带的左臂,手张开攥拳,一切如常。巫嵘起身拉上窗帘,开了床头小灯,然后解开绷带看了眼。猩红血纹从手腕开始一路到手肘,图纹简单却并不简陋,十分精致,看久了竟令人有种头晕目眩感。周巡说血纹刚开始时,谁也不知道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毕竟一样人养一样鬼,就算是同为饿死鬼,在不同人身上也能养出不同的效果,也说不定过不了几天鬼纹自己就没了——就跟花枯萎一样,有些人就是不适合养鬼。就算千方百计弄来了鬼纹也不能维持下去。所以说有鬼纹也不算正式踏入养鬼人行业,只有等一个月后鬼纹稳定了,才能去公安局给鬼‘上户口’。
养鬼人和天师等能力者都可以享受极高的国家待遇,包括住房,医疗,孩子上学等等,牺牲后享烈士待遇,无数人挤破脑袋毕生也想步入其中,此时巫嵘却不明所以就有了鬼纹。说出去恐怕得有千百人羡慕嫉妒,但他却没有半点侥幸心理。
如果真是那头大鬼,恐怕不是他养它,而是它把他养在身边喝血吃肉了。
只是巫嵘心态出奇平和,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发现自己身上有无数谜题,身体里还可能进了头厉鬼后他也没有成日惴惴不安,几次险死还生更让他几乎没了对死亡的恐惧,冷静后想的都是些现实问题。
比如给母亲报个平安。
重新缠好绷带,巫嵘掏出手机,手却在兜里顿住了,他一愣,抓了个东西上来,慢慢张开手。
淡紫色的纸鹤静静躺在他的手心里,只是头顶红了,染上了一滴血。
护身符没了,符篆纸鹤竟然还在!
外面传来一阵喧杂声,苗家土话夹着不知道哪儿的方言,距离他的房间越来越近,巫嵘反手收起纸鹤。下一刻门便被冒生推开:“你就是巫嵘?”
十三四岁的娇俏少女苗族打扮,声音清脆婉转,如出谷黄鹂,语气却算不上好。巫嵘抬眼看去,就见这小姑娘眼里有毫不掩饰的不忿。
这种敌意就像被抢了冰糕的小孩,只是单单纯纯的不高兴,没什么恶意,段位太低,对巫嵘造不成半点影响。看他不应话,小姑娘扁了扁嘴,不开心用有些生硬的普通话道:“我是阿蕾朵,寨老让我跟艾姐姐和牯哥哥来接你。”
“不知道你来的这么早,哥哥姐姐被青崖寨请去跳神了,只有我来接你,你不介意吧。”
“无事,我也要养伤。”
巫嵘淡淡道,展示自己缠着绷带的左手:“不急。”
“啊?你还要养伤?”
阿蕾朵急了:“可是寨子里事很急,寨老让我马上接你回去。”
“他们能被请去跳神,我没觉得事情有多急。”
巫嵘语气一直未变,却气的阿蕾朵直跺脚,脸蛋都红了:“哎!你……”
“阿蕾朵,一看不住你就出来胡闹。”
门外一女声严厉传来:“以后不准你再下山,再说谎我把你嘴撕了。”
本来正耍脾气小姑娘听了竟被吓得一哆嗦,立刻跟只鹌鹑似的乖乖站好,哭丧着脸小声告饶:“艾姐姐,我没有……”
“道歉。”
阿蕾朵很不情愿的,冲着巫嵘低了低头:“对不起……”
结果她头被直接一压,鞠了个九十度躬,新进来的女人不好意思对巫嵘道:“实在抱歉,我没有管教好妹妹,给你赔罪了。”
她盛装打扮,头上戴着闪亮亮银饰,看起来有十几斤重,一张鹅蛋脸漂亮极了,落落大方,普通话也很标准:“别听这丫头瞎说,你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本来寨老是要亲自来接的,只是前一阵子巫婆婆出了意外,摔断了腿,寨老得守在寨子里,这才嘱咐我们一定要好好把你接回来。白牯正在寨前门楼等您。”
“外婆摔断腿了?”
巫嵘皱起眉,记忆中他对这位老人印象不深,上辈子母亲去世后他送骨灰回苗疆,看了眼老人。她是个枯瘦的小老太太,脸色蜡黄,老到牙都掉了,躺在床上起不来,行将就木。巫嵘就来得及看她一眼,在回去第二天外婆也去世了。
算算时间,就在一周后。虽然世界变了,但一直到现在事情走向都是大致没有变化的。老人骨头脆,一骨折就很不容易好,说不定就是这次骨折,才让外婆本就虚弱的身体病情更加恶化。
巫嵘知道母亲对外婆感情很深,没能看她最后一眼,绝对会自责的要命。
“走吧。”
他站起身来:“先回去看外婆。”
听他松了口,两人一喜,跟周巡打了个招呼后三人向外面走去。通往寨子的路极其难走,崎岖陡峭,没有大巴也没有出租车经过。招待所门口停了辆半新不旧的摩托车。身材婀娜,眉眼如画的苗族妹子长腿一跨,坐到了车上,被训得耷眉拉眼的阿蕾朵坐在她身前。
“上来吧。”
马达声隆隆作响,摩托车就像一匹撒欢劲马,一溜烟上了山路。从招待所到寨子有段距离,呜呜风声从耳畔刮过,两侧景象风一般掠过,摩托车开的飞快,驶进了莽莽森林中。一开始还有山路,到最后都没有路了,只有原住民世世代代走出的小道,山路陡峭,车像是在悬崖峭壁上飞行。
悬崖让巫嵘眼晕,他恹恹闭了闭眼,忽然耳边听到阿蕾朵愤愤委屈声:‘为什么一定要让个外乡人来继承啊,明明牯哥哥那么优秀,巫术蛊术样样使得,远近寨子谁不夸他!’
‘阿蕾朵,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进寨子后不许再提这件事。’
艾桥语气严厉:‘巫嵘他是巫氏一脉,最为尊贵,只有他才有可能唤醒蛊王。别说继承,就算把金山银山全给他也是应该的。你再胡闹,我真会撕了你的嘴。’
蛊王?
这种事就这么正大光明在他跟前说好吗。
奇怪的是睁开眼后,两人说话声就又没了,戛然而止。再闭上眼,谈话声才又出现。忽然有什么东西动了动,巫嵘定睛一看,发现艾桥耳垂上停着只淡紫色的小蝴蝶。蝴蝶很小,不过小指甲盖那么大,落在亮银耳坠上就像装饰品一动不动。
巫嵘想起招待所时,阿蕾朵耳朵上也有同样的耳坠,和艾桥一左一右。巫嵘起初没在意,现在却有了些兴趣。这个世界的苗疆蛊术神秘,重重秘法难以想象,只是苗疆传承从来都是父传子,母传女,排外极其严重,以至于到现在苗蛊还经常被认为是传说中的东西。
现在看来倒是名不虚传。说不定能找到对付这头大鬼的办法。
即使摩托车速度很快,也走了大半天的山路才终于快到寨子。摩托车不能开进寨子,最后这节山路要步行。远远能看到一座木质鼓楼,楼上悬着一面以桦树与牛皮制成的桦鼓。鼓楼矗立在进寨的必经之路上,就像一座瞭望塔,遇到紧急事件就会敲鼓,鼓声能在山林中传到很远。
一楼敲鼓,邻寨响应,鼓声寨寨相传,守望相助,透着股苍凉古朴感。
鼓楼前站着好几个盛装打扮的苗人,都是专门来迎接巫嵘的。最中间站着的青年身姿挺拔,眉眼温柔,令人觉得如沐春风。一直蔫巴巴的阿蕾朵立刻像只欢快离笼的撒欢小鸟,直接冲着他跑了过去:“牯哥哥,牯哥哥!”
“这丫头,唉。”
艾桥头疼叹了口气,向巫嵘解释道:“凡是外出子女儿孙回到寨子前,家里的亲人长辈们都会拿着亲自缝制的传统服装等在门楼前,要换回服装才能进寨。衣服上熏了特制的草药,穿上它寨子里的虫啊蛊啊就会避开你。”
“这件衣服是婆婆亲手缝的,白牯是寨子里大巫的独子,算辈分的话是你的表弟,血缘最近,只有他才有资格代替婆婆来迎接你。”
“嗯。”
老人的一片心意,巫嵘不置可否点头,走上前去。旁人向他敬上牛角盛的酒,巫嵘一饮而尽,接下来就该换衣服了。
但这表弟好像不太正常。
刚开始白牯只是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但当巫嵘走进后,他蓦然瞪大了眼,脸色发青,浑身发抖,跟见了鬼似的。当巫嵘伸手去拿衣服时他猛地向后一躲,就像兔子见了天敌,想逃又不敢逃,脸上冷汗滋滋直冒,声音打颤:“你……您怎么这时候来了?”
“白牯,说什么傻话。”
艾桥疑惑道:“他就是巫嵘啊。”
但听到这话,青年脸色更难看了,面色煞白,不敢置信:“他就是巫嵘?!”
作者有话要说: 和苗族传统有关的知识来自《苗侗文化…贵州》
第11章 巫蛊
“牯哥哥你怎么了?”
“白牯?”
“我没事。”
很快白牯在呼唤中掩去脸上异色,冷静帮巫嵘穿上了民族服饰。和苗女比起来,苗族男装较为简单,没有层层叠叠的银饰,巫嵘身上这件左衽长衫材质像丝绸,深蓝紫色近乎黑色,都说男要俏一身皂,这身充满少数民族风情的盛装称得巫嵘更冷漠俊美,走在寨子里赢得了许多大胆热情惊艳的目光。
“咱们是远近几个寨子合到了一起,寨中有苗人也有侗人。”
恢复了正常的白牯侃侃而谈,对寨子的历史一清二楚。他普通话很标准,确实是非常好的导游。
苗族依山而居,侗族依水而居,艾桥就是侗族人,刚进寨她便告罪一声,走向一座青石小桥,从怀中取出了刚绣好的香囊轻轻放到了桥下,她脸偏向一边,言笑晏晏,像是在倾听什么,但对面却没有任何人影。
“那是艾桥的桥,桥对侗族人有特殊的含义,几乎每个侗族人都会认领一座桥,一个家族祖祖辈辈都会侍奉这座桥,每经过时小祭,过年时大祭,来获得桥的保佑。”
白牯解释道:“万物有灵……”
“白牯我们快走,桥说那些人又来了。”
匆匆回来的艾桥脸上再无笑意,白牯面色一凝,略带歉意望向巫嵘:“如今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