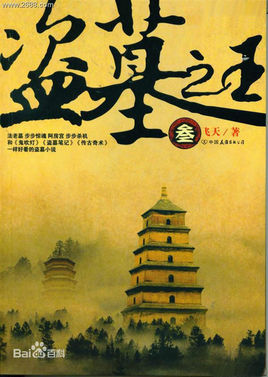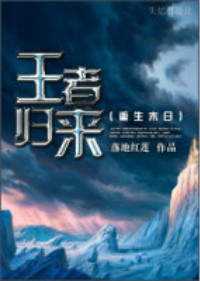万王之王楚庄王-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到任何社会应当前进的动力,也非常难以让人直观感到个人应该奋发进取。
因此,如果我们把正规武侠小说与爱情小说比较来看,就可以看出,正规武侠小说是偏男人的阳刚文学,而爱情小说则是偏女人的阴柔文学。正规武侠小说中揉合了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因素,甚至包括许多比单纯的爱情小说还要精彩和让人兴奋的爱情,可是爱情小说中,却极少能有如正规武侠小说那样的鼓励事业进取的精神。既然古往今来,描写爱情的小说已经无数,而且几乎从未受过质疑,那么为什么不能容忍描写通过事业获得爱情的小说?
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去纵观观历史,横论国族,就可以发现,凡是爱情思维过度泛滥的国族、时代,都是在滑向弱势的国族和时代。
春秋之时,中国从国君到平民,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能上阵打仗的勇士。秦汉时代,中华儿女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人人都以能堪征战为荣。唐朝前期,中国诗人中有一大派是边塞诗,至今依然激励着一代一代的爱国志士。可是到了宋朝,皇帝们和柳永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彻底阉割和腐蚀了尚武精神,终于导致中华遭受了真正的灭顶之灾。
西方的古罗马帝国以尚武精神立国,才从迦太基和希腊的阴影中走出来,成就了历经千年的大帝国。然而,当他们后期的精神衰颓和宋朝一样时,他们的结局也就惊人的相象。后来欧洲的大航海探险时代,也同样是骑士小说最为盛行的时代。骑士们勇于冒险、生死守信的精神,早已融入了西方人的血液,成为了支持西方近五百年繁荣的一根巨柱。
回顾二十世纪正规武侠小说大发展的时代,正是香港、台湾等地蓬勃发展的六七十年代。那个时代,那里的人们坚定不移地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未来一定会更美好。同样,现在正蓬勃发展着的中国大陆,武侠小说也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承认和重视。所有这一切,难道还无法说明,正规武侠小说和社会发展之间,有一种正相关关系?
一个国族要能生存,首先必须要有基本的上进精神或尚武精神。“向孰不知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精神,是每一个国族得以生存至今的根本保证。可是一旦这个国族强大到一定程度,存亡危机不那么迫在眉睫,那么一些人必然容易追求于一些安逸享乐,甚至开始藐视他们真正得以生存的精神基础。而如何让这种舍本逐末的惰性思潮不过于泛滥,从来都是国族能够长久昌盛的最大关键。从这一个观点出发,如果爱情小说能够被容许存在,那么正规武侠小说作为爱情小说有机会呻吟的根本基础,为什么不能被容许存在?如果爱情小说能登大雅之堂,那么正规武侠小说为什么不能?
没有人否认爱或者爱情对人类社会和谐的巨大作用,也没有人否认,爱情小说中努力追求的过程也是一种精化智慧和谋略的过程。但是也请不要否认,任何东西过度,都可能成为致命的毒药。纵观古往今来的历史,军队、国族冷冰冰的硬性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在大势上,从来都压倒了各种人性化的所谓“智计”或“谋略”。要让一个人去沉迷于平面的爱情游戏并不困难,可要激励一个人去忍受苦楚、去奋发向上,却往往要难得多。当生存暂时看不到立即威胁的时候,人类固有的趋易避难的惰性,永远都比上进精神更容易泛滥成灾,并一发而不可收拾。当一个人在别人创造的基础上无病呻吟的时候,对使他得以生存的这种基础的创造者和维持者,保持基本的尊重,是不是人类社会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呢?
既然一位始终跟男人一样喜好的女子,往往被人定义为铁娘子或女强人;那么如果一个男人最喜欢读爱情小说,也最喜欢做爱情小说中的那种事,这种男人就可以被定义为雌性男人。光靠教条式的训导,来避免太多男人成为雌性男人,往往是不够的,通过轻松的文学环境来颂扬上进精神,有的时候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用小说的糖衣来掩护良药的苦楚,从来都是人们的利器。如果你是一个男人,而且你拒绝去做雌性男人,那么请你读武侠小说。如果你是一个男人,而且你希望更多的男人不去做雌性男人,那么请你写武侠小说。
三.正规武侠小说主要代表作家分析
总的来说,正规武侠小说主要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开始兴盛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开始迅速衰落。如果我们希望重新激发一次正规武侠小说的浪潮,那么先去认真作一次基本的回顾和总结,认真研究和剖析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就是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环节。
梁羽生
正规武侠小说的正式开创者,一般认为是香港作家梁羽生。他被朋友所逼,被迫为香港太极门和白鹤门之间的澳门擂台赛写的一篇《龙虎斗京华》,是许多人认定的“新派武侠小说之源”。他的主要代表作有《萍踪侠影录》和《白发魔女传》等等。其中《萍踪侠影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曾经被大陆的广播电台改编为午间播音剧,那每天中午的三十分钟,曾经令无数人为之痴迷。其所写的《白发魔女传》,同样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正规武侠小说中第一个以女性为主角的著作。另外,梁羽生不但是正规武侠小说的主要开创者,而且至今依然是诸多武侠作家中,文史造诣最高的一位或几位之一。
然而,梁羽生尽管是正规武侠小说的开创者,但却似乎终生看不起武侠小说。他的古文学造诣,尤其是其诗词造诣,始终无法与其武侠作品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有人甚至评论为“有硬贴上去的感觉”。梁羽生的作品经常不是隔开完整的代数,而往往是十年一轮,与读者们“后续作品的年代差应大于或等于一代人时间的整数倍”这一习惯不大相符。也许他是希望造成一种群英荟萃的感觉,但是看其表现出来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同时,如果仔细观察他作品的历史背景,会发现其中的某些作品所描述的年代,可能已经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粱羽生写书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其写书容易“走神”。这是指其书的前半截很可能是在说某一个人物,可后半截却又开始在以巨大篇幅去描写另外一个人物。这种走神的笔法并非新意,主要见于《三侠五义》之类的古典小说,以及有“仙侠类武侠小说之王“称号的还珠楼主。“走神”写法的优点,自然是可以给读者造成一种格局很大的感觉,缺点则是容易打断读者的思绪,用起来很不好掌握,必须极为慎重。这是因为,几乎每一个读者在读小说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主角。如果突然间转换了主角,那么读者无疑有一种被凌空腰斩的感觉。如果是思绪习惯于随时跟着别人走的读者,这种感觉可能还不很明显;可如果是思维惯性比较强、全局记忆能力比较强、掌控欲望比较强的读者,其被这种腰斩感觉所激起的反应,对于作者来说自然未必是好事。
一般来说,既然武侠书最中心的特色之一,是反映人们奋发向上的上进心被满足,那么武侠书中,最好有一个很明显的主角武功进步的过程,而且最好一开始非常差,而到最后应该最强或“非常”强。但在梁羽生的著作中,男主角的武功很少能在最后达到最高、或是最高的那一阶层。这虽然与现实中的情形也许更加贴切,但毕竟读者来读武侠小说,其本来目的,就是想体会到一些现实中难以达到的冲动和满足。梁羽生之所以喜欢这样,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思维习惯中非常讲究辈份、尊卑等等传统规范,因此后辈武功要超过前辈的话,很可能本身就会是一种“原罪”。
http://
作品相关 序二:论正规武侠小说的写作方法(2)
同时,梁羽生崇尚“名士”,因此无论他想把其著作中的主人公改换成什么,总是难以完全摆脱这一骨形。由于此一原因,其男主角的性格经常受到很多无形拘束,往往显得“半死不活”。另外,其作品中男主角的夫人数目永远小于等于一个,很多还是赤裸裸的悲剧,经常难以令一些特别热爱幻想的读者们满意。
金庸
第二个最有名的武侠作家就是金庸。金庸的作品几乎无须介绍,就能被所有武侠小说读者所熟知,其中的许多人物、事件甚至早就已经融入了社会生活中。他的作品被无数次地改变成电影、电视,一部一九八三年版的《射雕英雄传》电视剧,更给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留下了永远无可磨灭的深情。如果说梁羽生是正规武侠小说的开创者,那么金庸就是正规武侠小说的发扬者和集大成者。他和古龙、梁羽生一起,构成了武侠历史上不灭的神话。
金庸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能够用非常平常的语句,来描述扣人心弦的人物和事件。他无论是对世人,还是对读者的心理,都把握得非常透彻。他真正知道读者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敏感什么,不敏感什么,并总是能在别人还察觉不到的时候,就先行迎合,完全没有任何文笔、心理或身段上的困难。他几乎从来不用大段大段的描写去赞美女主角的容貌,但任何人都能从其中得到女主角容貌无双的印象。他的一个最成功的塑造成果,就是《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因为他居然在先明言了其丑陋的情况下,依然能让程灵素成为无数读者的梦中情人。他的每一章节几乎都有分枝,他的每一章节又几乎都有合龙,他甚至能在一切都自然的同时,让一切都不平凡。正因为如此,金庸成为无数读者心中不可逾越的圣像,几乎已容不得任何人看到他的任何一丝缺点。
然而正如世上没有完人一样,金庸的作品也同样有一些瑕疵,只不过要看出这些需要眼光,说出这些需要勇气,而认同这些需要理智。
首先,金庸对于恩怨事件的了结,经常突出表现“受害者选择拒绝惩罚加害者思维”,很少有“加害者选择停止加害思维”。这是一种弱者式的、夕阳式的思维。在他的书中,几乎所有的受害者,最后都选择了“只要我自己变强,别人不来惹我也就罢了,我还是不要去报复的好,就算要惩罚,他也总会有别人去惩罚的”的老年人思维,加害者很少受受害者的直接惩罚。这种思维,当然是维护现代社会长久和平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过分推崇这种思维,却容易导致整个社会弥漫一种心理过分老龄化的衰颓气象。最起码当年梁启超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老化式思维的危害,特地写了一篇《少年中国说》。
如果过分强调这种受害者首先去原谅、去理解加害者的思维模式,容易潜意识地对加害者产生降低行恶成本的鼓励作用,甚至导致其对加害别人或别国理直气壮,拒不道歉,满脑自我舒缓“你自己都承认,你之所以被我打是因为你自己弱,那当然是你自己的错”。同时,这种模式也容易让善良的人们不自觉地远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式的强者威慑思维,导致其总爱去想“人若犯我,我则避之;无须报之,天必惩之”,只知以自我退让的方式求得和平,把惩罚罪恶的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或是某种无可捉摸的“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