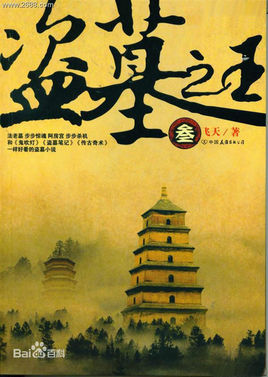万王之王楚庄王-第60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昭元怕跟她纠缠下去又会难以终了,咬了咬牙,彬彬有礼道:“在下实在不是小姐要找的人。小姐要找的人想来跟在下颇为相似,是以小姐有些迷惑。只是在下实在不是,却也不便欺骗小姐。在下告……”他话未说完,宫云兮忽然手一动,猛然一下又揪住了他耳朵,欢喜笑道:“哼,真要揪你的话,你还能闪得开么?快说,你为什么……”
昭元忽然一把推开她,冷冷道:“在下已经说过什么遍,在下的确不是那位昭公子,请小姐自重。”说着冷冷看了她一眼,就要转身离开。宫云兮从来没有被人如此推拒过,而且还是被这个自己唯一看得上眼的人这样冷冷推拒,心头委屈已极,虽还是一言不发,眼中却已是泪花直打转。
昭元极力想转过去不看她,好好来个一了百了。但她已是如此伤心,自己心头更是百倍难过,竟然说什么也无法狠下心来就此离开。昭元定了定神,道:“在下无礼,冒犯了小姐,请小姐息怒。天下形貌相似者本多,在下实在不是,还请小姐理解在下。小姐如此美丽,便白痴也当知道喜欢。小姐本当只虑本来不是者冒名认是,何以还担心有人坚决不认?”
宫云兮恨恨道:“可是这个人,偏偏就是一个连白痴都不如的东西,只有他才敢看轻我。”昭元道:“原来如此。在下虽然守礼,但终于还是知道喜欢,想来还不是白痴。在下能有此缘,与那位昭公子如此相象,得小姐青睐,实在也是荣幸之至。”
宫云兮狠狠地望着他,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却根本不理他之所言,更不答话。昭元本来就最怕女孩子流泪,这下更是悔恨无比。他叹了口气,正要离开,可居然忍不住又出言安慰道:“在下虽然不是,但那位昭公子肯定会来的,小姐又何忧之有?”
宫云兮转过身去不理他,只是嘤嘤而泣,肩头也随着微微颤动,更加显得柔弱可怜。昭元叹了口气,狠了狠心,道:“小姐保重,在下告辞。”一转身就要离开。宫云兮忽然转过身来道:“你敢发毒誓说你不是他么?”
昭元一怔,道:“在下和小姐非亲非故,又何必要发什么毒誓?”宫云兮冷冷道:“你若真的不是,那么发一下毒誓又有什么要紧?你不发,那就是心中有鬼。”昭元心头热血一冲,咬了咬牙道:“我若是昭元而不肯认,那便……”
宫云兮冷笑道:“说‘娶不到宫云兮当妻子’,别的我不认。”昭元心头如受重击,呆立半晌,竟然说不出话来。宫云兮望着他脸上神色,渐渐得意起来,笑道:“哼,你怎么知道这是最毒的誓?到现在你还不肯承认吗?”昭元忽然沉声道:“我若是昭元而不认,那便娶不到宫云兮做妻子。在下虽然鄙陋,但也甚是骄傲,愿心随圣贤,实在不愿托人之名头来行事。在下无论多么喜欢小姐,也决不会去冒名掠人之美。小姐,你这下满意了罢?”
宫云兮脸色刹那间苍白无比,颤声道:“你……你真的发出来了?”昭元之心痛如刀绞,几乎站立不住,咬了咬牙道:“小姐仙姿凤仪,人人趋之若鹜,以盼亲近。在下发此一誓,自然可说是最毒的誓了。但在下既知在下本来便无此福气,发这誓却实是丝毫不难。现在在下毒誓发完,想来是已能解小姐心中之疑了。”宫云兮泪光闪动,忽然一掌挥来要,狠狠打他一个耳光。昭元一把捉住挡开,冷冷道:“小姐还不满意么?还要逼在下做些什么?”
宫云兮冷冷道:“没什么了,你走吧。”昭元心下便如流血一般,道:“如此,在下告辞。小姐保重。”宫云兮背对着他,根本不答话,娇弱的身体在夜风中瑟瑟而抖,更显得单薄可怜,无处可依。昭元咬牙跨出一步,听得身后似乎传来嘤嘤啜泣之声,心中难过,迟疑了一下,终于又回过头来道:“在下告辞,小姐保重。”宫云兮依然不说话,只是背对着他。昭元心中更是难过,却说什么也跨不出下面一步,不知道在留恋着什么,在遐想着什么,又在等待着什么;口中也依然还在呐呐道:“在下要告辞了,小姐保重。”
宫云兮转过身来,冷冷看着他,忽然冷笑道:“你要告辞,那你赶快走啊,留在这里做什么?”昭元低下头,无言以对,心头那最后的一丝雪意也终于完全消失了,霍然转身就要飞身离去。宫云兮冷冷道:“说这么多遍,就跟多说几遍我就能保重一样,有什么用?白痴一个。”昭元心下一动:“她也是在暗示我么?”但无论如何,这却也提醒了他:自己追逐那武功高强的黑衣人,现在离城已好几里了。若要让宫云兮一个人回去,那却怎么可以?
他现在已经完全不想其他任何事了,只觉得若让宫云兮一个人走这段漫漫长路,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容忍之事。至于宫云兮是不是那个黑衣人,其真实武功高不高,她是怎么能在这当来这里的,这种种疑问全都已无丝毫可疑之处。他甚至开始觉得,那黑衣人也可能是个身形有异的男子了,而且还很好色,心头更无可抑制地萌发了要保护宫云兮回城的念头。
昭元怔了许久,终于道:“现在夜幕低垂,小姐一个弱女子行此长路,甚是不便。在下既然与小姐相见一场,正好也是回城,愿送小姐一程。”
宫云兮冷冷道:“我不需要送。我自己能来,自然能走。就算要人送,也决不要你这种口是心非之人送。你还不走?”昭元叹了口气,道:“在下确实颇有失礼之处,先前非君子所为,还请小姐见谅。在下此番送小姐回去,实在是遵循圣贤之教,绝非是想要对小姐图谋不轨。”宫云兮哼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么?你卑鄙无耻,说你口是心非都已经算轻了。这里什么人也没有,就你和我,要是我有危险,那必定是你。我为何要相信你?”
昭元叹了口气,道:“刚刚在下曾追逐一名贼人。”宫云兮冷笑道:“你这种人嘴上说自己不好色,其实口是心非。你追的一定是名女子,我怕甚么?”昭元呐呐道:“在下……在下有些疑他也可能是男子。”宫云兮哼了一声道:“又在口是心非了。就算他是男子,见了我也当知道恭敬讨好而不敢亵渎,又哪里会象某个白痴一样不知珍惜?”昭元见她句句都扣紧自己口是心非,却又句句直抵自己心间,根本无可辩驳,心下忽然气馁,叹道:“既然这样,在下便先回吧。小姐保重。”说着一拱手,咬紧牙关便扭头而行。
忽然身后宫云兮惊叫一声,昭元急忙回身便跃,根本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事。飞跃之中,他发觉林中似乎有人朝宫云兮身边扔了一块黑布,来势极缓,简直就与普通小儿抛石无异。宫云兮镇定下来,冷冷道:“你回来做什么?”昭元一看那黑布,便知是包着一块石头,疑心是范姜仪姜哪个丫头所为,却也丝毫不问,只是道:“有人偷袭小姐,在下既然亲眼看见,那便不能不管了。还请小姐三思,容在下送上一程。”
宫云兮哼了一声,不再说话,只是缓步前行。昭元默默跟了上去。宫云兮忽然回过头来道:“你跟来干什么?”昭元垂头道:“护送小姐。”宫云兮道:“护送本小姐,那便当先前探路,在后面跟着做什么?”昭元道:“是。”当下快步行前。
宫云兮走得甚慢,走走停停。昭元看了看天色,却见已是启明之星渐现,心下微急:“不一会鸡鸣城开,乡农们出来劳作,我岂不是被人看见跟她在一起了?”他极不愿意如此,便慢慢贴近她身体,伸掌与她身体只留一隙,隔空助力。宫云兮道:“你这么靠近我做什么?”昭元无奈,只好又自退开。
昭元看看天色将明,终于忍不住道:“小姐深夜出行,若是被人看见,恐怕愚夫愚妇们会有闲言闲语。”宫云兮根本不理他,只是默默而行。昭元想起要是想在开城门前入城,毕竟还是要翻跃城门,无论如何不能避免。他只好咬了咬牙,道:“在下有些轻功,可以助力,小姐莫怪。”说着贴身近前微微揽住她身体,二人立刻身形快了许多。
不一会二人翻越城墙处,潜入黑暗中。昭元深吸一口气,才要举步,忽然心头一动,却又轻声道:“敢问小姐府居何处?”宫云兮似乎看也不看他,冷冷一指道:“那边。”昭元心下幽幽一叹,面上却是丝毫不变,只是挟着她飞跃。
过了一气,已是远远看到了陈府门楼。又近了几步,昭元看看中间已再无危险,停身不动,对宫云兮道:“前面想来就是小姐尊府了。在下护送已毕,就此告辞。”宫云兮缓缓道:“我问你,你老老实实回答我。你对我真的一点情谊都没有了么?”
昭元深吸一口气,道:“在下和姑娘之缘,只在今日萍聚。在下虽然心仪小姐风采,奈何在下已有妻室曾同糟糠。在下实无可相弃贤妻,而普天之下也决无人敢屈姑娘之尊。姑娘误认在下为未婚夫,倒也是一段奇事;然在下实身属圣贤教化,即便此身碎作万段,也决不会掠人之美。日后在下自有妇,姑娘自有夫,天各一方,各安所命,又何必谈甚情意?”
宫云兮的眼睛慢慢抬了起来,一瞬不瞬地凝望着他,似乎要令他心中痛悔和虚假完全暴露无遗。她忽然道:“你是不是一开始就在瞒我骗我?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是我那个名义上的未婚夫?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冒名的?”昭元狠心道:“姑娘既然还是要认错人,在下无可辩驳,实在遗憾。在下和姑娘缘尽于此,就此告辞,后会……无期。”说着袍袖一挥,掩住自己之面,根本不待宫云兮回答,已如避洪水猛兽一般倒纵而去。
他心头那颗已经被千万利箭射得千疮百孔的心,终于完完全全地碎裂了,从此再也无法再承受一丝的痛苦,也再无法装载半丝的欢乐。这一切不是自己深思熟虑苦苦决定的么?自己不是曾经很清楚地知道,这样做无论于国于民还是于她,都是利益极大、无限美好的么?今天自己终于成功地做到了,为什么竟然还如此痛悔?
昭元拼命地凭借着记忆飞奔着,甚至不敢睁眼,因为他怕一睁开眼睛,那么眼前的将不是路,而是宫云兮的影子。宫云兮是还在那里痴痴地等自己回头么?昭元不知道,他所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已经真正永远地步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疯狂的奔跑,终于将他的躯体带回了客栈,可是却似乎根本没有带回他的心。他的心已经完全破碎了,消逝于无形之中了,又哪里能被带回?他一头扎入被子中,野兽一般地疯狂地撕咬着,似乎是要突破这明明是被自己拉来紧紧蒙住自己头、让自己无法呼吸的锦被。可是,他双手却又是本能地要将自己捂得更紧,因为与窒息相比,他更加害怕去面对被子外面的世界。
终于,昭元不再动了。被子没有丝毫被撕破被咬破,但是,它已经受过了男儿之泪的洗礼。昭元慢慢掀起被子坐起身来,呆呆地望着那根本撕不破咬不烂的被子,眼中已不再有任何神采,心中也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他只能凄凉地苦笑:自己根本就是这被子的一部分,自己又怎么可能撕得破它、咬得破它?可为什么它蒙的偏偏不是别人,而只是自己?
他越来越觉得好笑,竟然也越来越觉得坦然:自己本就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