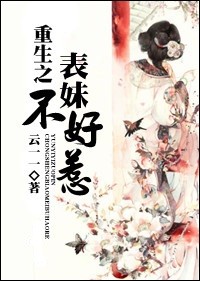表妹万福-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嘉芙就藏身在舱门后,看着萧胤棠眯了眯眼,终还是收回目光,向身边几个面露怒色的随行摇了摇头,那几人方随他一道,转身离开。
嘉芙紧张的几乎就要透不出气了,直到看着萧胤棠一行人背影渐渐远去,才觉手脚发软,张开手,手心里已捏出一层的冷汗,她扶着张椅子,慢慢地坐了下去,发起了呆。
孟夫人也见到了方才一幕,少不了又责怪儿子莽撞,甄耀庭不服,梗着脖子顶了两句,嘉芙心烦意乱,撇下母亲和哥哥,起身回了自己的房,和衣扑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前世的一幕一幕,又如走马灯般在眼前闪过。
原本以为摆脱了和裴修祉的婚事,回到泉州,不管日后京城怎么变天,和自己再无干系了,她更不可能再和萧胤棠碰面,却没有想到,老天刚帮了她一个忙,接着就和她又开了个玩笑,这辈子,竟比前世还要早,她就这样看到了他。
嘉芙想起刚才他临走前投来的那一道阴沉目光,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三王爷云中王萧列有雄才大略,识人善用的一面,也是一个心机刻薄,深沉隐忍的人,这才能从长兄天禧皇帝长达将近二十年的猜忌下保全住自己,直到最后,在三兄弟的明争暗斗中,成为了最终的赢家。
萧胤棠是他的儿子,骨血里自然流淌着来自于云中王的某些性情。嘉芙曾伴他身边多年,不敢说对他有多深的了解,但也知道,他也不乏来自其父的手段和心机,至于心狠手辣,更不用说了。
能上位的人,哪个手里不是沾着累累人血。
她记得清楚,上辈子,就在她嫁给裴修祉不久,还没一年,现在这位以辅政顺安王之身而上位的永熙帝就对一向蛰居西南的萧列动手,萧列岂会坐以待毙,兄弟冲突,终于爆发。
嘉芙实在想不出来,这种关键时候,身为云中王世子的萧胤棠突然秘密现身于此,亲自去往泉州。泉州到底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他想去做什么?
今日之事,哥哥也不算全错,但这性子,实在太过莽撞了,迟早有一天怕要吃大亏。很明显,萧胤棠这趟出来,应是秘密行动,不想惹人注目,这才放过了。否则,以哥哥骂的那话的难听程度,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就这样掉头而去?
万幸有惊无险,没出什么岔子,他就这样走了。
嘉芙心乱如麻,接连几天,除了必要之事,寸步也没走出舱房。孟夫人见女儿这几天恹恹的,面色惨淡,起先以为她生病了,来看,不像是生病,问又问不出什么,有点急,一急,又迁怒到了儿子头上,埋怨他那天吓到了妹妹,甄耀庭想起妹妹确实是那天后变成了这样子的,心里又后悔了,过来想着法子地逗嘉芙开心,照旧是说要正经开始做事。孟夫人让他去和张大学着看账,没看两页,哈欠连天,趴在那里睡了过去。
嘉芙对自己这个哥哥,也是生出了些类似孟夫人般的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只能宽慰自己,总有一天,哥哥他会真正懂事。见母亲为自己担心,且又快到家了,勉强打起精神,以应对接下来来自祖母的不满。
这日,一行人终于回到了泉州的家里。
胡老太太早半个月前就收到了信儿,且同行的下人里也有她的人,早就知道最后还是儿媳妇这边给拒了的,心里原本很不痛快,但孟夫人却一反常态,对着老太太毫无惧色,跪下去说,婚配讲究和顺生吉,这婚事一波三折,本就不吉利了,何况这些天也看了出来,裴家除了老夫人,没几个厚道的,女儿就算勉强嫁进去了,恐怕最后也是事与愿违,故擅自做了一回主。边上甄耀庭也一同下跪,一本正经地指天发誓,说自己往后要洗心革面,好好做事,再不让祖母担心了。
覆水难收,人也回了,胡老太太虽不痛快,但也无可奈何,加上年底要到了,家中船队、船坞、铺子,官府各处走动打点,各种事情林林总总,忙碌异常,这件原本寄予了厚望的婚事,也就草草算是这么过去了。
孟夫人松了一口气,终日忙忙碌碌,助老太太做事,嘉芙也帮忙打着下手,哥哥被逼着跟在张大身边,整天叫苦连天,日子看起来又恢复成了原本的模样。
但嘉芙却始终忘不掉那日在福明岛发生的意外。
她听的清清楚楚,他也是要来泉州的。唯恐和他再次碰到,从回家后,她便没出去过一步路。就这样过去了十来天,泉州城里风平浪静,慢慢开始有了过年的气氛。
要过年了,嘉芙猜测他应该已经走了。原本整天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慢慢地放了下来。
17、第 17 章
离年底只剩几天了。这日,嘉芙随母亲一道,到了甄家的船坞。
这里不仅是建造或修理船只的船厂,还有一大片的棚户。甄家厚道,祖上起就在这里给为甄家跑海的穷苦水手和船工搭屋,让他们上岸后好有个落脚的地方,后来那些人娶妻成家,人丁渐渐繁衍,棚户也越来越多,到嘉芙父亲时,这里已经有百来户人居住了。三年前,那些随父亲一道出海没有归来的水手船工的家眷,如今也依然被收留在这里,寡妇们就靠在船坞里做零工度日,虽日子艰难,但至少,头顶还有片屋瓦能够遮挡风雨,也能养活自己和孩子。这几年,每年到了年底,孟夫人都会亲自来这里给孤儿寡妇们分送米肉,每家再派两吊钱,好让他们也能过年。
嘉芙年年都陪母亲同来,今年也来了。探望完孤儿寡母,出船坞的时候,忽然想起几个月前那夜里被自己遇到后带回来治病的少年,不知道后来救活了没有,于是停了脚步,问了句近旁的一个船坞管事。
那管事起先没想起来,实在是里头做杂事的人太多了,片刻后,才拍了下脑袋,道:“想起来了!张管家那回叫人送来的那个小子!已经救回了,病也好了。如今就在船坞里干活儿。我把他唤来,让他给小娘子磕个头?”
嘉芙道:“救回了就好。我是刚才忽然想起来,就问了一句。不必特意叫他过来了。”
管事笑道:“小娘子善心,竟还记得他。也是那小子运气好,当时遇到了小娘子你,才活活捡了条命,要是金家那样的,如今早不知道葬身哪条鱼腹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嘉芙被这一句“葬身鱼腹”给触动了心事,想起父亲,心情便低落了下去。管事话说出了口,也立刻意识到失言,“啪”的用力扇了下自己的嘴巴,慌忙躬身赔罪:“怪我胡说八道。小娘子勿怪。”
嘉芙知他也是无心,略略笑了笑,转头见母亲一行人已到了船坞门口,正转头张望着自己,便提裙快步走了过去。
船坞靠港,海风向来疾劲,口子这里更是吃风。就在嘉芙经过路旁一片用来固定圆木堆的排架时,一阵风呜呜地刮了过来。
排架立在这里年长日久,接头处的绳索风吹雨打,已是腐了,却没及时更换,劲风一吹,架子咯吱咯吱晃动,绳索忽然炸裂开来,一排堆的比嘉芙个头还要高的圆木,哗啦哗啦地滚落下来,朝着嘉芙涌了过来。
圆木是前几日刚运来待用的,还没来得及拖走,不是很粗,只有碗口的直径。但即便如此,这么多的圆木一齐涌下来,若被压在了下面,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嘉芙正低头看着路,起先没留意边上的动静,等发觉到情况不对,也反应不过来了,就那么定在了原地。
孟夫人站在船坞大门口,一边和张大几人说着话,一边等着女儿上来,突然听到身后起了一阵异响,扭头看去,魂飞魄散,张大等人也发觉了,反应了过来,立即冲了过来,却已赶不及了,眼看嘉芙就要被那成堆塌下的木头给砸到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斜旁里忽然奔出来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疾步如飞,身影快的如同一道闪电,转眼便冲到了嘉芙的身边,勘勘就在第一根圆木滚到嘉芙脚边之前,一把抄住了她的腰肢,带着她往侧旁闪去。两人一起扑到了地上。
张大等人赶到了近前,固定圆木的固定圆木,救人的救人,船坞口乱成了一团。
孟夫人吓的脸色惨白,奔到近前,分开人群,见方才那少年趴在地上,将自己女儿紧紧地护在身下,慌忙扑了过来,道:“阿芙!阿芙!你可还好?你可还好?你不要吓娘啊!”
这少年动作是如此的快,以致于嘉芙竟然有些头晕目眩,被他扑在身下,此刻才回过神来,听到母亲的声音,睁开眼睛颤声道:“娘,我还好……我没事……”
那少年从她身上迅速爬了起来,挤出了人堆。孟夫人和张大替嘉芙悬着心,起先也没多留意他,只搀着嘉芙从地上起来,见她除了衣裙上沾抹了些地上的污泥,一张脸吓的变成惨白颜色之外,身上其余确实没有受伤,这才松了口气。
孟夫人惊魂未定,搂着嘉芙,不知道念了多少声佛,听张大呵斥着船坞管事疏于防范,忽然想起方才救了女儿的那少年,看了过去,见他越走越远,忙叫人扶着嘉芙先上马车歇着,自己走了过去,叫住了那少年,看了一眼,衣衫褴褛,大冬天的,脚上也只一双破了洞的草鞋,脸上沾满泥灰,但细看,容貌却生的很是俊秀,也不嫌他脏,捉住了他手,道:“好孩子,今日多亏了有你!你叫什么名字?是哪户的孩子?”
张大赶了上来,看这少年,总觉有些面熟,一时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但他既在这里现身,自然是在自家船坞里做事的,见这少年不吭声,于是转向船坞管事。
管事见因自己疏忽,方才险些酿出了大祸,面如土色,慌忙上前道:“他便是数月前小娘子叫人送来的那个小子。当时快病死了,我因记着小娘子和管家你的叮嘱,一直悉心给他治病,救活了后,就叫他在里头做些零活。”
张大这才想了起来,看了少年一眼,把先前凑巧带回他的经过向孟夫人略略地说了一遍。孟夫人感激不已,不住地称赞他,说了几句,留意到这少年没了方才冲出来时的那股子灵敏劲,只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一语不发,瞧着呆呆的,便不解地看向管事。
管事道:“禀太太,这小子是个哑巴,不会说话,又许是那回发烧烧傻了,平时脑子也不大灵活。”一边说着,一边朝那少年吆喝,要他向孟夫人见礼。
孟夫人啊了一声,更是怜惜,急忙制止管事,叹了口气:“可见这孩子的厚道。脑子都不清楚了,却还牢牢记着阿芙救了他的事,方才不顾性命也要还恩。我看他长的也是清俊,若在父母身边,不知道宝贝成什么,想是被人拐子给拐出来了,生生磨成了这样,可怜!”说完,让管事速速给这少年送身厚的新衣新鞋,又再三地叮嘱,叫往后要好好待他,不许欺负他。管事连声答应。
孟夫人又说了几句,方松开那少年的手,转身回去,也上了马车,对嘉芙道:“可怜这孩子,是个哑巴,脑子也不大灵光。”
嘉芙在马车里已经歇了片刻,人也从方才的巨大惊吓里渐渐地定下了神。看着母亲松开了他,他又转身,低着头继续朝前走去——嘉芙盯着他的背影,总觉得他步伐有些僵硬,略微蹒跚,和先前冲出来救自己时的身手判若两人,迟疑了下,叫母亲稍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