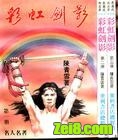山河剑影-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日月见道衍竟然拿着酒壶与他要酒;还跟他称兄道弟起来;心中想这个和尚真是假得要紧;他摊了摊手;无奈地道:“在下一介乞丐;哪有这么多好酒来喝?”
“丐帮准北舵主都没有酒喝;那丐帮存在这个世上也没有用处了。”有一个冷峻的声音从傅友德墓地后面传了过来。
日月与道衍朱棣三人相对一视;同时回头往那声音看去。
却见血红的余晖下;七八条怪异的人影;出现在了三人是视线中。
那竟是七八具尸体;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面部冰冷;毫无表情;脚不挨地;虚空踏来;忽忽之间便要至当前。
日月与道衍朱棣二人道:“假和尚;燕王爷这儿与你二人无关;你二位功夫那么好;快带那女孩离开吧。”
他说着;用手指了指那边石头边的段紫鹃;话中的意思是要道衍和尚和朱棣保护段紫鹃离开。
段紫鹃不禁心中一暖;美名其妙的感动了起来。
朱棣却说:“酒喝了;情欠了;你却要我师徒二人当逃兵;这可实在不地道。”
道衍也大手一摊;挡在了日月身前;这架势是要以命保护日月一般;日月心中也登时感触不已;很久;没有被这样保护过了。
这道衍又是何人呢?
道衍;俗姓姚;长州人;出生于元惠宗元统三年;家庭殷富;历代从医。
道衍十四岁时出家为僧;先学习天台宗;后研习密宗;打功;三密;二十岁受具足戒后;又慕禅宗。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道衍到杭州参访智及样师;智及为当时著名禅师;又是一名寺僧;一见道衍;就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和佛学见地;所以;就把法衣、佛子授予他;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佛教弘法的继承人。
三年后;道衍离开径山;住持临安普庆寺;接着;迁居杭州天龙寺和嘉庆留光寺;不意中;遇道士席应真;得传道教阴阳术数之学。
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创打天下;建立明朝政权;下令选拔高僧入京;道衍被推选;但他借口有病不赴召。
明太祖下令选学问憎入京考试;以便录用为朝官;道衍又被推选应试合格;但他硬是不愿做官。
明太祖只好n他僧服;准他回山。
道衍离开南京;准备游学;登镇江北固山;曾赋诗咏怀;感慨这个古战场。
道衍北上参学;游到河洛;在嵩山遇到著名相士袁珙;袁珙见他身为佛子;却隐含杀气;笑着告诉他:“你真是个奇怪的和尚;三角眼;形如病虎;有嗜杀之相;更有辅国之才;望君珍重。”
道衍很赞赏对自己的评价;于是;二人结为最好的朋友。
明洪武十三年;高皇后去世;太祖下召令选高僧传本王子;为他调经落福。
道衍受召入宫;与燕王面晤之后;彼此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朱棣向太祖建议;让道衍出北平;道衍后被朱棣安排在北平的庆寿寺做住持;没多久;道衍经常出入王府;成为燕王的高级谋士。
而这次道衍离开北平来到准北;就是奉了燕王妃之命;来寻找失踪多日的燕王;好请他回北平;来阻挡那朝廷的压顶黑云。
岂料朱棣竟习惯了漂泊江湖;任道衍如何劝说;他却无离开淮北的意思;道衍无法;只得藏在友德墓地的草从之中;本想最后一次感化朱棣;岂料却目睹日月手刃毛骧;血染青月剑;朱棣也深陷危机,他惊急之下;忙出来阻止。
话说当年道衍求武学艺;也颇有一番周折。
某日天气晴好;道衍于夜间出来登高观望星象;正看得认真;只听到身后有人干咳;道衍回过神来;听出是王行,速道:“施主如何也出来了?”
王行说:“时近午牌;众道友多体息了;只有你的床位空缺;故出来看看;没想到你果然一个人在此观天;近日可有喜事降临么?”
道衍道:“一片混沌;无有喜事。”
王行又问:“那么何日将远行?”
道衍叹道:“小僧志向你也知道;自小立下鸿图大志;过了年就是二十五岁矣!别说是一事无成;就连方向都是一片渺茫;不知何处为归途”
王行道:“说到方向二字;学生正要和问;
众道友近日多催问宋老何日信至;为何偏就你不置一问?”
道衍说:“有个事因见你忙;不曾说得;今晚正好相告――关于去应天之事,王施主与众道友同往;小僧就不去了。”
王行吃惊道:“你为何突然改变主意;莫非家中出了什么事不成?”
道衍吃惊道:“小僧并不曾提起;王施主如何晓得?”
王行说:“有个事;近些日因忙于杂事未与你说;就在你回妙智庵不久;你姐夫来此处找你;他急要找你;知你回了妙智庵方放下心来;还在寒居息了一晚,其余并不曾说起什么;现在想来;一定是你家中出了事情。”
道衍于是把此次回庵取讲的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番;王行听后就说:“难怪你不去应天;原来是与李行素有约!看来李行素答应不强求你传奉张士诚;但每遇到危难,他们少不得来找你,一旦你不愿意,又会与你家亲人要挟。”
道衍说:“我已与家姐说好了;等姐夫回家后尽快处理田产;去他乡隐姓埋名。”
王行点头:“也只能如此了;你自己何处何从?”
道衍:“应天去不得;妙音庵也回不去;天下之大;竟找不到可容身之处;小僧正为此苦恼一一”
王行说:“道衍师不必苦恼;若真是无处去时;学生到有一个可收纳你的地方;学生此次从杭州回来;杭州有个净慈寺你可曾听”
道衍道:“早听说了;那一座有名的古刹;只是无缘拜访。”
王行说:“净慈寺的住持智及禅师在杭州颇有文名;与学生常有交往;此次我回来时;智及讲起寺里少了一位书记;特意教我替他留意;学生修书一;改日就可以携书前往;以道衍师的能力;足能胜任书记之职。”
道衍道:“那就谢了;小僧只想快点去到杭州。”
王行便回房写了书信交于道衍;见道衍真要走;就说:“道衍师为何如此性急?”
道衍说:“不是小僧性急;实是除你之外不想再惊动他人,明日有人问我去向;你就说不知;只当小僧是不辞而别可行?”
“道衍师放心;学生绝不会与他人说知。”王行把道衍送出村口;然后返回。
且说道衍离了王行村上;到十余里外的镇上落宿。
是夜无话;次日已牌离开客栈继线前行;一路上少不得行夜宿;未及半月;道衍就到了杭州净慈寺。
道衍找到值日僧;说起自己的来意。
那值日僧二话没说;便引他去方丈室见智及禅师。
智及见道衍年轻博学;又有名士王行的介绍;当下就录用了他;自此道衍在净慈寺一边跟智及习禅法;一边书文记事。
这净慈寺不愧是名刹大寺;寺内僧人修行之高;远非妙智庵小店可比。
尤其智及禅师乃是百里难得一遇的高僧大德;道衍与之论道参学;可是受益匪浅;数日之功;竟胜似在妙智寺十一年!
道衍庆幸;来到此地有如蛟龙之入了大海;任他在佛海s航逆游。
时间一晃几年过去;就在道衍渐入住境;真正认清了佛教奥妙之际;他猛然发现:
年少时立下的雄心壮志与佛法并不矛盾,佛法的要义乃是度人脱苦海,干大事业如果是匡扶正义、济世救民;岂不与佛学有殊途同归之妙?
第三十章花落神州泪飘零【10】()
参悟到这一点后;他的内心又开始躁动不安了。
每当有相知的香客入寺,或是外出办事;他都要打听;慢慢他了解到;至正二十年;李行素自吴县王家庄回平江后;张士诚便偃旗息鼓;采取避让的办法应对朱元璋。
朱元璋见张士诚不应战;军中士气日消;便弃了张士诚;挥师南下攻打陈友谅去了。
道衍隔三差五出寺院去至市井;不时向人悉心打听。
其时;张士诚之实力已然到了鼎盛时期;他的领土已是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颖,东至薄海;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户口殷盛;国用饶富。
至正二十年;道衍于断桥边见一堆人在议论;遂近前傍听。
原来市人正在议说张士诚;说他因江浙地界富饶;早不满足于太府之职;奏请朝廷封他为王;却被帝严辞拒绝;又去到另一处;所见市人也在议论此事。
有人就以张士诚被帝拒绝后之态度相赌;赌注层层加码。
又数日;道衍自断桥附近经过;只听得那里放鞭炮;近前一问;方知道张士诚已自立为“吴王”;宣布脱离元朝;那燃放鞭炮者;正是赌张士诚反元赢了的。
得知道个消息;道衍预感到;平静了几年的江浙又要起平戈了。
至于结果如何;日下实难预测。
离了断桥;至一街头;只听得一孩孩重在唱一支重谣:
“丞相做事业;
专用黄菜叶;
一朝西风起;
风干!”
道衍不知童谣为何意;找了一个孩儿询问;那孩儿摇头说:“我们也不知道是何意;平江、长州、後江好多地方都会唱了;现在传到了杭州。”
道衍又转到一个街尾;也听到一孩在唱;旁边还坐了几个老者;于是向老者打听。
一须发皆白的老者说:“此谣无非是唱张士诫;张士诚自至正二十年来;就不再居安思危;只管享乐;在平江城内大造宫般;广征美女;朝中事务都交给了弟弟张士信;这张士信是个荒淫酒色之辈;每日朝坐白玉堂;夜宿黄金屋;将朝中事务全部交于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此三个人只会舞文弄墨空谈国事;迟早要葬送了张氏江山。”
道衍明白过来:“难怪说黄、蔡、叶';原来说的是他们。”
道衍离了市井回净慈寺;香客中有从远方来的说起来朱元璋;道是他已消灭了陈友谅;接下来就要对付张士诚。
道衍很认同香客的说法;朱元璋伐张乃是迟早的事。
果不出所料;朱元璋开始发动扫除群雄的大规模战争;张士诚成了他的第一个目标。
至正二十五年十月;朱元璋派元帅徐达率兵出征。
徐达奉命直取通州、泰州诸郡县;在强兵面前;张士诚的军队不堪一击。
徐达剪除了张士诚肘翼之后;乘胜直逼渐西
局势一日紧似一日;杭川市井中百姓的神色;少了往日的悠闲。
五月某日;道衍经一老街;见有一堆人围着一堵墙面观看。
忽有宫兵将围观者赶开;接着便从墙上揭去一张其大无比的白纸。
道衍心下生疑;去问方才那里散开的人;都惊慌e头走开。
道衍只得离开;又到一老街;也是有人围了一堵墙在看。
道衍奋力奔到前面,原来是朱元璋讨伐张士诚的平周檄:
“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
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
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二也。
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三也。
初寇我边,一战生擒亲弟;
再犯浙省,杨苗直捣其近郊;
首尾畏缩,又诈降于元,四也。
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五也。
占据江浙钱,十年不贡,六也。
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失贴木儿、南台大夫普化贴木儿,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