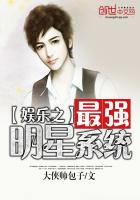ǿ��-��45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ڴ�ʱ����Ȼ�ϼ����������Ҵҵij��˽���������ү�����ˣ���С�㣬��С������˰�����
������һ�����������
��С�㣿�����»�������
�����³���֮�����������֪���ⲻ�ǻþ������ܺ��Ӷ��ϴ��ˣ���������ȴ����һ�����������ӣ������ߣ����ߣ��ٲ��߾��������ˣ���
����Ѿͷ���㣬����ô�����˰�����������δı��Ķ���Ů��������ɵ�����ˢ��һ�¾�����������
�����á�������ޱһ����ס�����õ��֣�����Ҳ����������������
��Զ��ȴ����һ��������������°����Ƕ����Ľ��������𣿡�
����������û���������������Լ�Ҫ���ġ��������¼�æ���������˰������������֪�����ǻ��д��ѣ������ǰ�ɳ����Ľ���ǰ����Ӧ���Ƕ��ң������������д�ԭ�����������ˣ��Ҳ����ĵ�����������Լ�ִ��Ҫ����һ�����ġ���
������������Զ�ر��������һ�������Ҵ���ʲôʱ���й������ǣ���
���������ڲ���˵�����ʱ����������Щ���ˣ������������Ǹ��泼����֪������Σ�����Ѿ����˺ͳ�͢�Ķ�Թ�����Ե�����������ǰ�����������ˣ���
������������һ������Զ�ص��۾�һ�������漴����Цһ��˵�������ͳ�͢�Ķ�Թ����͢������û�жԲ����������ģ������и���͢���ȣ����ȥ��������Ǹ��ܵܣ��Ҿ��ھ��ǵ���������ʲôʱ���������֮ʦ���ˣ���ʲôʱ������������ӣ���
������֪���Լ�����Ƣ���������˵�����;��Բ���ı䣬һʱ��ĸ�ס���㡢����������
�������˺α���˹�ִ�����������ʱ��һ������Ʈ��������һ����ʮ�����������أ���������������ӵ������˽�����
��������˭������Զ�ض������ʵ���
������ָ��ʹл��������ˡ���л����ɫ�����ص������ҽ���������Ӧ��ү���˳������¹��ش�л�첻��˿���������������ǰ�����ǡ����ˣ���һ·���Ҳ��Ͻӵ������鱨������������뾩�Dz���ֻ�м���·�̡��ҵ������ͻ�����Ա�Ѿ����ź��ˣ�����˼��ٴ��ż��˺���һ���뿪������һ�оͶ����ˡ���
��Զ������Ŀ�����һ�ۣ�����˵���ˣ��Ҳ��ߡ������Ǵ����ij������Ǵ����Ĺ�����������Ľ��˾��ǣ�����һ��ѳ�����ѣ���
������ֻ֪���ң��ѵ��ʹ���û����������𣿡�л�컹��������Ȼ�ص�����������Ҫ���ң�л��û�б�İ취�ܹ�Ȱ˵���������������أ�Ů���أ������أ��ѵ������Ƕ�����һ����������˵�������������£���ȴ����û������Ӧ��ֻ�������Һ����ʴ�����������������Ǽ鳼���ѵ���������������Һ�ļ���һ��һ���뿪���𣿡�
��Զ�س�Ĭ��������������Ŀ���һ���Լ��ļ��ˣ�Ȼ���Ȼ���ص�̾Ϣ��һ������ȥ�ɣ�ȥ�ɣ�����ȫ��ȥ�ɡ�������������������������Ҷ��������л�죬��ȥ����������Һ�����ǵ��Լ��Ǵ����ij��ӣ�������Ҫ�������Լ��Ǵ��������Һ��
�����������ҽ���һ����˳�����
��Զ�ز�ȻһЦ�������Dz�����Ȱ���ˣ��ҵľ����Ѷ�����⣬��Ҳ��Ҫ���ˣ�������һ���������ɡ���
������������������˶����������
��Զ��һЦ������Ⱑ������ģ��������������Ҳ�͵�������ĸ��ף����Dz��Ầ��ģ���ʱ����һ�������һ����·�ߵġ���
���������Ͳ���������������ȴ����Υ���Լ����������
����Ҳ���ߡ����������Ц�ţ����Ϸ�������ô�����ˣ��뿪���һ��ܵ���ȥ��������������������������߱��ǡ����ٶ����������ݣ��������ִ��������ṩ�������ء�
��Զ��ҲЦ�ˣ������������ӻ���ʲô�ź����أ�Ȼ�������˻��֣���ȥ�ɣ�ȥ�ɣ�ȫ����ȥ����Ͷ�����ǵ����Һ������ȥ�ɣ���
�������ʮ���¡���Ǩ��
��������������⣬Ҳ��Ϊ���ǵ����Һ��ȥһ�������������мǵ���㡣��
���ǡ���л��ĬȻ���������˻���ʲôҪ�Ը��ġ���
��Զ�س���̾Ϣһ�������ö�����������ζ���Ҫ���ˣ��Լ��ܻ��Ǵ����ij��ӡ�����������Σ�������Ϊ��������һ��Ѫ�����ɡ���
л��ĬĬ�ĵ��˵�ͷ��
���棬�����Ѿ������ˣ���ʮ������ɫ���µ����������Ļ�����������Χ��һ�ȶ��ҽ��õ�����������������Ѹ�ٵı������������������������뿪��
л�������ؿ���һ�ᶡ�ң�Ȼ��һҾ���ס�
��ʱ�ڶ��������⽹�겻������Զ��ȴ����¶Ц�����Լ��ķ���˵���������ˣ�������������ܻ�����һ���ˡ���
�������Ҳ��Ц�ţ�����ʵ���㻹�Ǻ�Ϊ�����Ժ��ģ����𣿡�
��Զ�ص��˵�ͷ˵�������ǰ��������������Ȼ�����죬����������������˶̵�ʱ���ڱ㴴������˴�Ĺ�ģ��ȴû�м������ܹ��쵽������������Ԥ�У�ֻҪ�����ڣ����ǵĴ����������ˡ���
�������ˣ������ˡ����������Ц��˵���������ǵĴ��������ˣ����ǵĶ���Ҳһ�������ˡ���
��������֣�Ϊʲô����������Ϸ����ܹ�Ц�ó���
����ʵ��û���뵽���ǣ�ս������̫ԭ�����䡢��ͬ�������ȵص��ؾ�����Ȼ����һ����һ��������ʲô���������ڻ��۵ı������µ��ܱ������Ӽξ�����������߷�����Ƿ���õ�����ʼ�յò��������ʿ�����䵽�˼��㣬�����ܵ�ǿ��ѹ���£�Ѹ�������߽⡣
���Գɵľ������¶�ʮ���չ���ƽ�������³����������ݣ����¹���̫ԭ������ʮ������̫ԭ���ϣ���������ܵ��ܱ��������ĵֿ�����ͬ�ܱ����������ܾ���Ԯ������������������Ͷ������ͬ��ս���¡����³������ܽ������ͣ����ܱ����uͶ��������ʮ�������ܽ���������Ѳ����֮�롢�ܱ�����طͶ����������ս���¡�
����ͺñȴݿ����࣬���ɨ��Ҷһ�㡣�����ѵ����������Ρ������Ѿ���������Ϊ���𣿳��������Ĵ��ǵ�Ȼ�����ģ����dzﻮ�˳�������Ǩ�������ĶԲߡ����ǣ�û��һ������Ч�ġ�
����ʮ�������³��ţ������յ����Գ��������������飬ͨ�����³�ʮ�մ���ִ�b��i�������£�˫��չ����ս��
����Ȼ�ǶԴ�������Ȩ������ս��Ҳ�Ƕ���������ս�����ļ������ӣ���˹�����֪��ս��ʱ�䡣������͢��ս��ʱ���Ѿ������ˡ�
��Ϊһ��֮���ij����ļ���٣���ʳ�Ѱ��������������ڷ�ŭ��ƣ�����跹��˼���ϳ�ʱ���������˵�������ﻰ����������֮��������������֮�������η�����֮���£�һ��ʧ֮��������Ŀ���ڵ��£���Ը��ʦ���Ծ�һս��������ɳ���������ˣ��������Ŀ����
˵�գ�ʹ�����飬�߷�Ȼ���ʴ��ǣ�������ˣ���͢����û���������������͢�IJ����ֽ��ڿݽߣ���ô���أ�������Ϊ������
����һ���ʵ۴������Զ�ʦ����һ��ս�����ҵ������ڸ����������ȱ�̬��Ը����۳�������������˼���ػش��Ϸ�������ʤ�Σ�һ�ڻؾ����ڸ�θ�κ��¡����Z�����䡢�����ġ����������ˣ��Ⱥ�������۳���������һ�Ų�ͬ�⡣
��ʱ��ȥ��ʮһ���뷽����һ������ڸ���̩�����ˣ�����������Ƿߣ�������ô�Ҳ������Լ�������������ɽ���ˣ��˽������Ը�����Լ��ļҲ���Ϊ���ã����������������
�������������������ɽ���˴����������������ı�̬����ϲ�����������ν������ұ�ʾ�������ھ���Ϊ�����У���ʾ�����۳����������ǡ�
�̩������Ҳ������ɽ���������ˣ����������ʿ���Ⱥ��ι��Ӽ���ơ����������ɣ�����ʮ����ʮһ�½����ڸ�
���˳�����ͬ��̸������ս��Ը����Ҳơ�����ƽ�ҡ���������ͦ������������Ѫ����������˼�����ġ��ʵ۵�Ȼ��֮���ã���Ϊ�̩��ɽ���ˣ�Ϊ�˺����Լ��ļ���һ��������ƴ�����ο������ǵ��ؾ������ò��ص��ģ�������ȫ������
���¶�ʮ���ա����۳�������ʽ¡�ؾ��С�����������ξ�������̫�������Żʵ�������������ν��Dz���������顰�����������ĸ����֣�������Ȩ���Ľ�����з�������һ���ʹ��̩��Ȼ��һ���˵ȳ˳����������ų�¥���ʵ��������ֽ�����ᡣһ·�϶����ֳ���ᦵ�ʿ����������һֱ���е��������⣬��������������չ�������൱�����ҡ������ų�¥�ϰ���ʮ������ϯ�������ǻʵ۵���ϯ���������ij��������������䳼�����������ϵľƾ����洫���������ʵ�ʹ�õ�����Ƕ��ʯ�Ľ𱭣�����ʹ�õ���һ��Ľ𱭡��������𣬻ʵ����̩���������������˵��������ȥ����ͬ�����Գ��������¶����Ա������¡�
������̫��Ϊ�̩���Ϻ컨�����Ϻ�ɫ������һƬ�������У��̩�뿪�����ų�¥���ʵ��ڳ�¥��ƾ��Ŀ�͡�
���¡�صij�����ʽ�������˻ʵ��볯͢�ĺ�������ô���̩���ɽ����������ܹ����������
ɽ�������ʮ�ֻ��ң��á��������ҡ������ݣ�һ��Ҳ��Ϊ�������ܻ�û�е����ؾ������ܣ�����һ�����ճǣ����Ļ̡̻�
�����ֽ�������£��̩Ӧ�������ӱޡ���ҹ��̲��У�������ƫƫ����˹������ڹŴ�������ÿ���о���������ʮ�ʵ���и��ڻʵ۵����С��ʵ����Ե��ɸ���һǧ�������Ӫʿ���������䱸�˱��������衢�ܱ����нܡ��������������Ĵ���ʿ�����������ݲ���ν��ǿ����ʿ��Դ�����涨�£��Ķ��̩���Ͽ�ǰ��̫ԭ����ʰ���ġ����������ʾ��ƽ����̫ԭ�ر����ԡ�Ȼ��һ�ж�����Ȼ���̩������ð�ŷ���ǰ��̫ԭ��ȥ��ʰ���ġ�
ɽ����������һ�ţ�ȥ��ʮ���¶�ʮһ�գ�ƽ�������Ŵ���Ա�Ƿ��������ܣ��Ѿ����ڲ������״̬���������¶�ʮ���գ����ܴ����ݵִ�ƽ����֪������Ͷ���������Ժ�ƽ���������Ϣ�Ŵ������ǡ��鱨�����������������
ɽ���ط�zh��ng������ת���飬ֱ��Ӱ���˳�͢��ս�Ծ��ߣ�ʹ���̩�����۳��������ڳ�Ϊ�ķ�ʸ�������ڡ�
��͢����û��ȷ�еľ����鱨����b��i�����ķ����ص������������̫��ɽ���涨������һ�ߣ������˱���������ͬ������һ�ߣ��뵱Ȼ����Ϊ���ر����أ�ȷ�����ݡ��ʵ۵ľ��߾��ǽ����ڱ����Ĵ�����������ϵģ��������̩�����ĵ�һ���������±��������ǿ��ǡ���֮͢�ǡ��ڱ���������������������ͬ����ʹ����ʧ�أ���������������ľ�����������ʦ��
�����ж���ʵ�������ȫ��������ʹ�̩�����г�Ч��Ҳ����ȷ����ʦ��ȫ��������ֻ�ֵܵ���������֧ƫʦ�������̩��������������ɽ����������Ϊ������һ��������̬���������ƶ��ѡ�������һǧ������������ڱ���һ�������ò�����Ҫ�͵ؽ�����ط��ٺ��������������ã����ܾ������������ǣ�Ū�����ö�ʦ������ɨ�ء��ڴ�֮ǰ����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