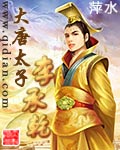梦落大唐之繁花落定-第8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车子颠簸得好厉害,到半路时,我开始呕吐,就像在现代乘车常会晕车一样,我吐得头晕目眩,却不敢叫车子慢一点。
白玛只是惊慌问我:“小姐,怎么啦?怎么啦?”
我怎么了?我也自问。这样严重的晕车,以前从不曾有过,何况现在乘的是马车!
好容易到了苏府,我的面色已经只能用惨白来形容了。
苏勖迎出来,见倚在白玛腕间的我,也慌张了,即刻命人去请大夫。
我也不敢再逞强,由着苏勖领我进了客房,先到床上躺着,拿了茶水给我喝。我的头却沉得抬不起来,只是软软趴在锦衾上,不愿动上一动。
苏勖兀自不安,不时向外询问,大夫为何还不过来?
我勉强叫道:“苏勖!”
苏勖眸子难得的又如星子般清明闪亮,他坐到床边,俯下身子,柔声问道:“书儿,什么事?还是哪里不舒服?”
我咬咬牙,问道:“我给你的那些密信,现在在哪里?”
苏勖怔了怔,道:“我早给魏王殿下了。”
我挤了一个黯淡的笑容,轻轻问道:“我,可以向你要回来么?东方清遥既然很快就能得救,我不想再牵涉无辜。”
苏勖眸里星光顿时散去,有些凌厉地看我,淡然道:“什么是无辜?难道那些不是事实?纥干承基不是和齐王有来往么?纥干承基不是太子的心腹臂助么?把此事告知皇上,于公于私,为国为民,都是件好事。”
好个于公于私!好个为国为民!好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我要救人,我要报仇可以用的借口。魏王扳倒太子可以用的借口。
我努力撑起自己的身子,冷静问道:“如果我一定要要回那些信呢?”
苏勖拂袖道:“那是不可能的。那些信,对我们很重要。”
“对太子很重要,对魏王很重要,但对你,只是些废纸!”我打断苏勖的话头,脸上滚烫,一定是因为太过激动而挣得满脸通红了。
“魏王殿下会是我未来的主上!”苏勖压低声音,在我耳边吼道。
我冷笑,同样低吼回去:“注定失败的主上!”
苏勖瞳孔蓦地收缩。
我冷冷盯着他曾经清雅迷人,如今却和我一样惨白的面孔,字字如针刺出:“你早知道我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了。一个疯子,不可能会排八字!更不可能会预知齐王谋反,甚至预知一个大臣的未来谥号封赠!”
“那么,会是谁?”苏勖双眼近乎赤红,紧紧盯着我。
我尽力笑道:“你把密信拿来,我就告诉你!”
苏勖迟疑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天色,道:“来不及了。这会子,魏王殿下应该已经拿了那些信入宫了!”
我似全身筋骨在一瞬给抽去,无力地扑倒在锦衾之中,抑制不住身体的颤抖,用手掩住了眼睛。
晚了,晚了,终究还是来晚了。
有人在外小心翼翼地敲门。
苏勖低了头,道:“嗯,多半是大夫来了。”
白玛看了我一眼,忙奔过去开门。
果是一个老大夫,背了药箱走进来,见过了苏勖,忙忙便来诊脉。
我近日总是疲乏犯困,偶尔也会犯恶心,却不曾有今日这般严重过,也不敢大意,很配合地侧过身子,让大夫细细诊断。
大夫才只一搭上我脉,便面有惊异之色,细细看我面容,似有几分揣度不安之意。
不知为何,我浑身一阵发热,居然也涌上阵阵不安。
苏勖已经忍不住,问道:“老人家,这位姑娘究竟怎么了?”
大夫只是不语,又在我脉上搭了许久,才退下道:“公子,可否屏去外人?”
这屋子里,除了我和白玛,另有苏家两个侍婢在。苏勖怔了怔,屏去了两名侍婢,大夫犹拿眼看着白玛。
我从现代而来,生理知识学得也是不少,已隐隐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只用手抓紧锦被,慢慢说道:“白玛是我的心腹之人,没什么好瞒的,老人家有话请直言!”
大夫又仔细看了看我面容,道:“姑娘,你已有一个多月的身孕,还是早作打算的好。”
猜测成真,我无语苦笑,轻轻抚住了我的小腹。说不了哽于喉间的幽幽伤痛和淡淡喜悦。冤孽么?冤孽么?纥干承基,你和我,真的是前世的冤孽么?
怪不得大夫如此谨慎,务要将人全请走了才敢说话。我的装束打扮,全然是未曾出阁的大家闺秀模样,若让人知道某家大户小姐未婚先孕,早该成了长安城的笑话了。
但大夫说的最后一句话,显然针对苏勖的。那略有些暧昧的笑容,分明认定了苏勖便是我腹中块垒的罪魁祸首了。他看着呆若木鸡面色苍白的苏勖,继续道:“姑娘身子弱,素常也必是个心思重的,不须服药,但一定得好生静养才成!”
苏勖茫然“嗯”了一声,怔怔看着我,眼神亦惊亦怜,说不出的复杂,好久才勉强笑道:“多谢大夫提醒了!我必叫下人多多注意呢。”
那大夫起身道:“既然这姑娘无恙,老朽这便告辞了。”
苏勖忙摸出两锭元宝来,塞到大夫手中,低声道:“此事关系这姑娘名誉,还请大夫不要外传的好。”
大夫悄悄将元宝掖在袖里,眉眼俱开,低笑道:“老朽明白,只是这姑娘单薄,公子以后得加意怜惜照顾才好。能成亲么,还是尽快成亲的好,免得到时大家脸上不好看呢!”
这老头年岁既大,自认见多识广,执意便将苏勖和我认作了一对。我倒没什么,苏勖却直到将老头送走了,将门掩上,面色还是苍白忐忑。
“是谁的孩子?”苏勖做到我床边,低声问着,那种轻柔怜惜和微微失落,却已暂时不见了世俗的功名势利了。
我没有回答,只默默抚着自己的小腹,感觉着那不知觉间悄然生长的小生命,心头渐渐安宁温暖。
白玛却眼珠乱转,突然伏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道:“小姐,小姐,是那个纥干承基,那个纥干承基上次欺负了你?是不是?是不是?”
苏勖眸子收缩了一下,那隐藏深处的痛惜和忿恨闪烁着,连拳头也紧紧握住,纠结起突突而跳的青筋。
“是他欺负了你?你实话跟我说,是不是因为怀上了他的孩子,你才决定要拿回密信,放过纥干承基?”苏勖声音有些沙哑,蕴着说不出的怒火。
纵然功利在他心中永远占了第一位,那月下意外邂逅的容书儿,还是他最珍惜的美好回忆吧。
我微笑,摇头,睫下却卷出晶莹的水滴,竭力平静的声音,忍不住的微微颤抖。“我也是才知道,我有了身孕。”
苏勖恨恨道:“他和汉王,原是一路人,全是禽兽,是畜生!如果不是为这个缘故,我不懂你为何还要对他手下留情?”
“因为我欠他的!”我毫不犹豫说道,抬眼瞪着苏勖,道:“每次我最危险最无助的时候,都是那纥干承基不计代价在帮我!他对别人也许是禽兽,但对我绝对不是!是我负了他!”
苏勖完全呆住了,吃吃道:“你,你跟他是自愿的?你喜欢他?”
仿若一盘雪水兜头浇在我心头,我有一瞬间屏住呼吸。苏勖的声音,和我心底的声音重合在一起:“你真的喜欢上他了么?你不是喜欢东方清遥的么?”
我摇头,回答自己,也回答着苏勖:“怎么会呢?他,一个杀手而已!我又岂会去喜欢一名杀手?我只是对不住他,对不住他!”
我喃喃念了几遍对不住,这种歉疚感深深印到心底。半闭起眼,将这种歉疚感压了又压,略觉安宁些了,才扭头转向苏勖,慢慢道:“如果不是纥干承基两次相救,如今的容书儿,连骨头都不知道会给丢弃在哪个角落里!我却为了清遥,以怨报德,把纥干承基一手送入地狱,是不是太过狠毒?”
苏勖连连摇头,道:“纥干承基行事任性随意,你又何必因他兴之所致的两次出手而耿耿于怀?你,你不过为救人而已,又狠毒在哪里?”
我苦笑道:“可是,现在我们并不需要那些密信,东方清遥也能从刑部大牢里走出来!”
苏勖又在摇头,但声音已有些迟疑,道:“书儿,你想得太多了。”
我自语道:“当年我受了辱,不但怨恨汉王,也怨恨吟容,怪她存心不良,恩将仇报,联手坏人来害了我。可现在,我的所作所为,不是比她更歹毒千百倍?如果纥干承基出了事,我,我便是死了,也是活该!”
苏勖忍不住叫道:“书儿!你别说了……”
他抬头看看天色,道:“我现在去魏王府见魏王,看看那些信,他有没有交到皇上手中!如果有可能,我们想法子把那些信再要回来。”
苏勖披了件衣衫,即刻走了出去,到门口时,还在吩咐下人为我备些清淡小粥,等我身子略略恢复时食用。
且不论他平时如何利欲熏心,但这一刻,他的身上依旧闪着人性的光辉,也许,撇开沉醉已深的浮华功名,这才该是他的本质吧。那个月下不经意般轻叩少女心怀的男子,也只在这一刻又清晰浮现。
可终究他是俗了,便如我亦俗了一般。俗得不如东方清遥,甚至不如纥干承基。
我叹一口气,抚着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小心翼翼,似守卫着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夕阳西下,漫天的晚霞流金幻紫,将窗纸映着通红如血光,并不眩目,却是伤心般的淡淡光华。
第二结局:第三十六章 路茫茫
我休息了半天,精神大有好转,遂吃了半碗粥,刚丢了碗,便见得苏勖已匆匆走了进来。背着霞光,他的面色黯淡一片,连明眸亦是低垂的,似不愿与我相触一般。
我死死抓住被角,掩藏住叫我颤抖的心痛和恐慌,嗓子变得尖锐:“你,拿到了么?”
苏勖慢慢摇头,盯着如血的天空,低沉的声音,轻轻飘过来,却如锤子般砸在我心头:“皇上看到那些密信了。已经下令京兆尹和刑部大员即刻入宫,估计很快就会收捕纥干承基。”
我顿觉舌干口燥,耳边混沌沌响着,脑中不知充斥了几多混乱无助。一个声音叫着:完了,完了!
苏勖不敢抬眼细看我,我也无心再多问一句话,凌乱地披了衣衫,站起身来道:“天晚了,我回去罢!”
“你以后,可怎么办呢?”苏勖盯着我依旧平坦的肚子,却苍白异常的脸,轻轻叹着气,忧愁担心,已经不加掩饰。一个未婚的大家闺秀,怀上了孩子,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若换了别的女子,要么匆匆嫁人,为自己的孩子找一个父亲;要么偷偷将孩子生下来,悄悄扔掉。至于堕胎,在这个时代,危险性却太大了一些,寻常女子是不敢将自己性命开玩笑的。
可我呢?我呢?
“如果纥干承基这次在劫难逃,我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好好养大。”我有些喘不过气,但对苏勖说话的口吻依旧保持着尽量的平淡:“我欠他的,也许这种方式可以还掉一些吧!”
苏勖点点头,闪过身子,目送我离去,却已无语。
我走过他身畔,又回头一笑,道:“不过,我不会看着纥干承基死。我是怎样去营救东方清遥的,我也会怎样去营救纥干承基。”
苏勖的面孔却沉浸在越来越深沉的黑暗之中,看不真面目。
我继续道:“我知道你会帮我的,有时候,帮我可能就是帮你,前面的路该往哪里走,我应该比你更清楚。”
我不再去探究他的神情心理,迈步向前走去。
白玛借了苏勖府里的一顶青布帏幕的四人小轿,将我扶了上去。
我一则不喜欢轿子行进的缓慢速度,二则也不习惯以人为骑,一惯喜爱相对迅速许多的马车,不然便是骑马,极少会坐轿子。但吐成这样,我实在不敢再乘马车,只得将就着坐了。
轿子虽是晃悠,但比马车要平稳许多,总算不再吐了,只是恶心泛酸的感觉,依旧挥之不去。
我一直以为自己最近体虚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