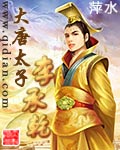梦落大唐之繁花落定-第6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白玛抬头望了望容画儿的房间,果见不时有丫头下人来回穿梭其间,透过偶尔开关门的片刻,可见得屋子里亦是人头攒动,衣香鬓影,甚至有着依稀的笑声传了过来。她一低头,道:“嗯,小姐,我们回房去。”
天渐渐黑下来,满园的梅树也暗了,在溶溶的月色下闪着静默的黯淡光泽。虽非十五,今日的月光却好得很。
可这月下徘徊的伊人,多少恨,多少爱,多少愁,多少伤,谁人能见?
孤鸿缥缈,何人省恨?且看那天涯远,婵娟共,落得几回魂梦,萦情蕴愁!
忽然很想念吐蕃略带酸甜的青稞酒,一杯下肚后那似醉非醉的暖暖感觉,很适合今夜。
可惜现在没有酒,只有深重更深重的春寒料峭。
有人将件貂皮的大斗篷披在我肩,我一回头,却是桃夭。
她见我转过头来时,脸上的担忧变成了惊怕,慌忙用手绢来擦我的脸,急匆匆道:“小姐,你哭了?为什么哭呢?”
我又哭了么?怪不得脸上这么冰凉。
我别过脸,问道:“剪碧呢?今儿是不是回二小姐他们的屋子住了?”
桃夭点头道:“大约不回来了吧。她守着东方公子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看得我好心酸。对了,东方公子问起小姐好几次,我们都只当小姐出门没回来呢!原来却一个人在这里伤神,也不怕冻坏了身子啊!”
是啊,我可不能冻坏了自己。
我叫桃夭关了窗,将因天气转热熄了几日的炭炉重又点起来,将屋子里烘得暖暖的,让那绵绵的温暖包围着自己,伴着龙涎香的芬芳,将自己的身心浸透,温暖地浸入梦乡。
这夜的温暖里却梦到了许多不曾梦过的景谦,依旧清爽温和的模样,冲我静静笑着,说着想我,要来找我,陪着我。我凝立在雪地里,整个的僵住,不知是惊,还是喜,也不知该不该如以往受了委屈一般,抱住他哀哀地哭。
但喉咙口确实已经哽住了,正哽得说不出话时,白玛摇醒了我,问着:“小姐,是不是魇住了?”
下部:第三十八章 错过(下)
我定定神,摇摇头,道:“只是做了个好梦。”
白玛放了心,侧身又睡。
我却再睡不着了,只是在床上辗转反侧,一直挨到天亮。我自回中土后一向身子不是太好,又有容锦城疼爱,素来也无人来责我晨昏定省之事,遂也偷着懒,就在床上洗了脸,吃了一点东西,便窝在暖暖的锦衾里看书休养。
近午时,剪碧拖着笨重的身子挪了过来,有些怯怯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皱眉道:“怎么了?快坐下来说话。”有了六七个月身孕,她的肚子已经好大了,我瞧那娇怯不胜的模样,心下倍感怜惜。
剪碧小心道:“三小姐,你怎么不去瞧瞧公子?他,他可念着你好几回了。”
我微笑道:“我昨天出去又着了风,病怏怏的,这回子还乏着呢,改天再看他去。他的身子还好么?”
剪碧眼圈一红,道:“嗯,休息几天,应该会慢慢好起来。现在却好瘦,身上好多的痂,新的旧的,都是受刑落下的,一直不曾好好治过,能逃出命来,也算是老天有眼了。”
我“哦”了一声,道:“那你叫人好好照顾他吧,自己就不要太操劳了,养好身子,生个白白胖胖的小子才是最重要的。”
剪碧颊上飞红,喃喃道:“嗯,看到他回来,我的心总算放下了。”
打发走剪碧,我也起了身,叫顿珠派人去打听齐王、太子等人的动静,顺便查一查吟容目前的行止。
吟容,我都不知该是鄙视她还是可怜她。为了自己,却害了我一生,她的心中,不知可曾有过一丝内疚?
汉王侧妃,好耀眼的光环!只不知这个光环之下,她能否昂首挺胸心无顾忌地享受着她的志得意满?
不久顿珠打听来消息,太子果然在竭力保着纥干承基,直指纥干承基是为人所陷害,甚至有谣言在坊间流传,说纥干承基的那些密信,系是魏王一党伪造,用来陷害纥干承基。侯君集等人亦在四处活动,直指魏王企图借纥干承基之事动摇太子根基,有不臣不轨之心。
两党各有势力,各自为主造势,乃至酒楼画舫,亦不时有二党之人针尖对麦芒相持相争,甚至有彼此殴杀之事。一时闹得凶了,京城之中人心惶惶,流言纷纷,甚嚣尘上。大理寺无法决断,几方压力逼迫下,终究亦如东方清遥之案一般,将案卷移交刑部,等待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中丞三司会审。
纥干承基虽在狱中,但深知太子势力非同小可,他自己又被从魏王势力笼罩下的大理寺转往被渗入太子势力的刑部,并连着换了几处牢房,自然必有耳目将消息源源不断传到他耳中。以他刚强个性,想他在这个情形下供出太子谋反之事,已是绝无可能。
我默想纥干承基身受之困境,一时也是一筹莫展,只在自己房中叹息。
这日阳光正好,我倚坐在窗边,看一对黄莺儿在梅下的野花丛中翻飞嘻斗,身后有熟悉的气息悄悄传来。
一回头,东方清遥正温和微笑着,站在身畔。他着一身月白的长袍,并未束腰带,松挎挎垂着;头发乌黑,亦未束冠,只用一块淡色的头巾轻系着,全然一副居家休养的装束。面色依旧是雪白的,不知是不是在牢中常年不见得阳光的缘故,但唇边已有了血色,削瘦的面颊亦因着笑的弧度而甚觉生动,往日温润如玉的风采,瞧来已经恢复大半了。
我心里动了一动,却也没有过份的狂喜。他回来这许多天我都不曾去看他一眼,算着他也该要来瞧我了。
淡淡浮上一个笑容,我叫桃夭:“快挪张软榻来,给二姑爷坐呢!”
东方清遥听我叫声二姑爷,笑容不由止了。一时在我身侧坐了,也看那野花开得绚烂,莺儿斗得可喜,出了好一会儿神,才问道:“书儿,病得重么?这么久也不见你到园里走走。”
我垂下头,道:“也没什么,不过着些凉。”
“自我回来,也好些日子了,还没好些?”东方清遥小心看我脸色。
我没有回答,静静趴在桌上,让窗外那生机昂然的浓绿,倒映在眼帘中,掩盖心底不知哪里浮上来的一层沉沉死灰色。
“书儿?”东方清遥凝视着我,好久,又轻轻唤我,却已夹杂了说不出的心痛。
心里揪了一下,似又有热热的血往外流淌着。
下部:第三十九章 情天远(上)
“二姐夫,我实在累得很,想去躺一躺了,我叫桃夭送二姐夫回二姐那里去?”我强笑着艰难说着,然后扭过头,不去看他。我们是曾经并头看那烛影摇红的一对亲密爱人哪!无法想象这声二姐夫和方才的二姑爷,会将二人的距离拉到多远!
“书儿!”东方清遥霍地站了起来,握紧了拳头,苍白的手绽出根根青筋,幽深幽深的眸子说不出的绝望伤心。他黯然道:“你怪我?你怪我娶了你二姐么?”
他眼底那抹冰冷刺痛直侵到窗外,连那两只黄莺儿也似受了惊,一张翅膀,一前一后扑簌簌飞去,留下满园芳草寂寞摇曳。
“你别辜负她,还有我的剪碧。”我刻意忽略去他眼底那抹伤心至极的刺痛,立起身来回我里间的卧室。
卧室和外间,用深深的菊花暗纹帏幕隔开,那菊花招展,却流着水一样的冷冷光泽,映着帏前帏后的两个人,彼此观望着,再看不到对方的脸,对方的心。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但他的人影消失时我似乎松了口气,却又说不出的伤心,悄然伏到了床上,压抑着不让自己痛哭出声。
不知是不是太过抑郁,抵抗力反而远不如在吐蕃的那些年,一时伤心过了,又觉头疼鼻塞,浑身乏力,慌得白玛急急叫人去请大夫。
却不知有种病大夫是不会医的,那便是心病了。
纥干承基,你可知道,现在你竟成我的心病了。
第二日一早,容画儿便来看我,开口便问:“三妹着凉可曾好些了?”
我只得强撑病体笑道:“左不过这样。自回了梅园,倒有大半的时候病着,叫二姐见笑了!”
容画儿帮我掖着被子,道:“是啊,你这次回来,人虽是清醒了,身子却远不如以往扎实,这些日子我只顾照看清遥,也不曾常来探你,真是愧煞!我去之后,你可一定得好好调理调理。”
我微怔道:“二姐要去哪里?”
容画儿抿着玫瑰色的唇,微笑道:“傻妹妹,我早就嫁给东方家了,容家只是我娘家。现在清遥的身子好得差不多了,我们自然要回我们自己的家去。”
“书苑?”我扯开一个茫然的笑容,书苑院里的曲荷幽香,书苑屋里的旖旎缠绵,一幕幕直冲脑门,海浪般冲得我头晕,连近在咫尺的容画儿面容都模糊不清起来。
容画儿正点着头,带着些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欢喜道:“我也想通了,只要他好,我也不该再求别的了。剪碧也会和我们一起回去,我一定善待她,以后她生的孩子我也视同己出,悉心抚养。”
我定定神,强笑道:“好啊,如果这样,我也放心了。她本是好人家的女子,应该能得到自己的幸福。”
容画儿微微笑了一下,美丽的面容更显得精致动人,她深深看住我,道:“三妹放心,姐姐我不会忘了妹妹救清遥的情,也不会忘了妹妹今日的情。”
今日的情?今日,我冷落了清遥,甚至拒绝了他的问侯,对我,对清遥,也许是劫,对容画儿,却是情?是不是就算我实践了我的诺言,不去和她争清遥,不去抢她的夫婿?
神思只是恍惚,连容画儿再说了些什么都听不太真,只是迷迷糊糊敷衍着,最后看着她窈窕的身影袅袅离开,桃夭礼貌地笑着送她出去。
忽觉膝上有些沉重,似有人趴在我腿上。
我揉揉眼睛,才辨出是白玛。这个身材高大丰满性情刚直的异族女子,正趴在我膝上哀哀地哭,边哭边抱怨着:“小姐,人人都幸福了,你怎么办?小姐,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我苦笑。
前路茫茫,千重万重的雾蔼如我眼前帏幕一般,遮住前路,也遮住了我。
我看不到前方的路,那是一片皑皑的白,不知道会是康庄大道,还是悬崖绝壁;别人亦看不到我,我的身形,我的泪水,和我的心,都深深掩在那重重的白雾之中,快与那片雪白融为一体。
下部:第三十九章 情天远(下)
第二日,容画儿果然带了东方清遥和一些原来东方家的下人离去,三夫人不放心爱女娇婿,也一并随了去照顾。
容锦城亲带了人送行,连素来不大露面的二夫人也出了佛堂,殷殷道别。东方清遥为人亲切温和,容家上下,只怕没有不喜欢他的吧?
而东方清遥却略显神思不属,一面保持着有礼貌的微笑,一面只朝我所在的方向张望,最后终于离去时,他眼底的怅恨和痛楚无法掩抑地浮在面容之上,连笑容也变得苦涩起来。
而我,我正紧闭了窗,隔了糊着霞影纱的窗棂,默默注视着一切,指甲深深掐入掌中,几乎掐出血来。
但自此心头似又松了口气,仿佛少了件牵挂一般。从此了了,是不是?了了!便如一页涂抹满字迹的书笺,被扯成一团烧了,显出下面新的一页空白来,从此由我涂写填画。
听说,因为太子一党的力争,刑部决定将案件押后再审,等待齐王那里进一步的取证。
延至贞观十七年三月,齐王兵败,齐王李佑连同一干部下被李世绩等押解入京,为各求性命,未等用刑,便李佑心腹之人将李佑种种不法之事一一供出,其中就有纥干承基与李佑暗通款曲之事。
真相既明,太子一党再无法公然保着纥干承基了,一时安静许多。
三月底,齐王李佑被他的父亲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