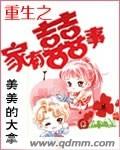音乐的故事-第5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铡�5〕洪亮的虚无主义。与丹第不同,在他那宽广的同情心里,没有狭隘的门户之见。他从不试图去批评自己所喜爱的东西;理解永远装在他的心里。也许他心安理得;但也许在他内心深处也有烦恼,他表面的大度平静可能多少给我们以假象。
他的信仰也……我知道凭一位音乐家的音乐来破译他的情感有多么危险;可在弗朗克的追随者告诉我们,表达心灵才是音乐惟一的目的和目标之后,我们舍此还能怎么办呢?通过他的音乐表达我们难道发现了他的宗教信仰总是充满了平静和安宁吗?我问那些热爱他音乐的人,结果那些人发现,他们自己的某些悲伤在他的音乐里有所反映。谁都会感受到在他的某些作品里充满了内心的痛苦和悲伤——那些短小、突然爆发的乐句升起来仿佛在乞求上帝帮助,便又常常悲伤而含着泪水落下。在弗朗克的灵魂里也不全是光明;但里面的光明并不因此而少感染我们,因为它毕竟是来自天国的光明“穿过云层的缺口,揭示了高照在深谷之上的天国之欢乐。”
在我看来,弗朗克与丹第先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像丹第那样急于追求思想的清澈。
* * * *
清澈是丹第先生心灵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他的周围没有阴影。他的思想和他的艺术一如他的表情那样明朗,使他的脸看起来那么年轻。对他而言,检查、安排、归类与合并是一种必需,在精神上,没人比他更法国了。他有时受到瓦格纳主义的强大压力,他很强烈地感受到瓦格纳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即使在他作品中有所体现,它也是表面化的;毕竟他本质的东西距离瓦格纳太遥远。在他的歌剧《费瓦尔》(Fervaal)中,你能找到有几棵树像《齐格弗里德》森林中的树,但森林本身都不一样,丹第的林中开辟有宽阔的林荫道,阳光也充满了尼伯龙根传说中的大洞穴。
热爱明朗,是丹第先生艺术实质中的统治因素。由于他的本质远谈不上单纯,所以这就更难能可贵。他受过广泛的音乐教育,他十分渴求知识,通过博闻强记,获得了五花八门、几乎互相矛盾的各类知识。他是个熟悉古今国内外音乐的音乐家,各种音乐风格体裁都装在他的脑子里。有时他面对它们好像也表现得拿不定主意。但他把这些风格体裁归纳成主要三大类;作为音乐艺术的三种典范:类似格列高利圣咏的素歌(一种不分小节的无伴奏宗教歌曲)的装饰风格是一类;帕莱斯特里纳〔6〕及其追随者的建筑般风格是一类;十七世纪意大利的那些伟大作曲家的表现风格是一类。但他的折衷主义总能尝试在这些本质不同的风格之间达成调和。我们别忘了丹第先生同我们时代的某些最伟大的音乐伟人如瓦格纳,李斯特,勃拉姆斯和弗朗克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他也随时准备接受他们的影响,因为他不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只想着自己兴趣的天才,也不是那种讲求实用的机会主义者。他总是对身外人事产生同感,乐意发现他们的不同凡响之处,并能迅速赏识他们的魅力。丹第先生虽然兼收并蓄,旁征博引,但他的作品从总体上讲总是很清晰明朗,适度有序。他可能适于清晰了;他简化得过多。
没有任何东西比他的最后一部歌剧《陌生人》〔7〕('étranger)更能有助于我们把握丹第的个性实质了。虽然他的所有作品都有他的个性这条主线,但它在《陌生人》中最为突出。
《陌生人》的剧情发生在法国沿海,从交响性序奏中我们能听到平静的海水在絮语。渔民们出海打鱼归来;最近收成一直不好。但他们中的一位“年约四十、神情庄重而悲伤的男人”比别人都幸运。别的渔民都妒嫉他,暗中怀疑他通巫术。他试着同他们友好地交谈,并主动把自己捕来的鱼送给一户穷人。可是徒劳;他的努力遭到拒绝,他的慷慨迎来怀疑的目光。他是个陌生人——剧中的这个陌生人。夜幕降临,奉告祈祷钟敲响。一群年轻女工从工厂里蜂涌而出,唱着欢快的法国民歌〔8〕。其中一位叫维塔的姑娘走过来同陌生人说话,因为全村里只有她是他的朋友。两人由一种内心的同情相互吸引而走到了一起。维塔直率地向陌生人吐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他们爱着对方,但又不肯承认。陌生人试图压抑自己的感情;因为维塔太年轻且已订婚,他觉得自己无权向她索取爱情。可是他的冷漠刺伤了她的心,她反过来也伤害他,并取得成功。后来他终于向她吐露了心迹。“是的,他爱她,她很明白这点。可现在既然他已向她表白了爱情,他就再也不会见到她了;他向她告别了。”
这就是第一幕。戏演到这儿,我们好像还在看一出十分有人情味的现实主义剧作——一段讲述一个人当好人却不得好报的普通故事,而且是一段人虽老了但心仍年轻且又无法使其变老的伤心的悲剧。可就在这时,音乐变了,使我们警觉起来。刚才陌生人在讲话时,我们分明已经听到了宗教味的音乐,而且我们好像还在主题里听到了一支礼拜仪式的曲调。难道有什么秘密向我们隐瞒了吗?难道我们不是在法国吗?可是,虽然有那支民歌和大海短暂的呼吸,空气中都充满了教堂和塞萨尔·弗朗克的味道。这个陌生人到底是谁?
他在第二幕里告诉我们:
问我的名字吗?我没有。我是那个做梦的他;我是那个爱着的他。我游历过许多国家,航行过许多海洋,我爱那些贫穷和需要帮助的人,并梦想着大同世界人人皆兄弟的欢乐。
我曾在哪里见过你?——因为我知道你。
你问在那儿吗?在所有地方:在东方的烈日下,在极地的白海边,……我在哪里都能找到你的踪影,因为你就是美本身,你就是永恒的爱!
这部歌剧的音乐里有某种高尚的气质,而且打上了一种平静而坚强的宗教信仰精神的烙印。“陌生人”这个题材同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火荒》(Feuersnot)的题材有些相像。那里的主人公也是个天涯怪客,正受到迫害;他给一个城镇带来了荣耀,却反被那里的人当成男巫虐待。但是两剧的结局不同;两位艺术家在气质上的根本不同也在剧中有明显反映。丹第的结局是一位基督徒的放弃和退隐,理查·施特劳斯的收场是(主人公)自豪而欢乐地肯定(自己的)独立。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我开始对一个人发生更浓的兴趣时,剧中的故事却只是在讲述一种存在或一个独自的实体(entity)。我怎么也不能理解这种象征主义的手法……但这毕竟只是个口味不同的问题,我对此并不感到太吃惊。这种在歌剧中从现实主义过渡到象征主义是自瓦格纳时代以来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法,对此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我们离开象征主义的抽象之后,却进入了一个更加离奇荒诞、远离现实生活的领域。
这时候,在陌生人的帽子上,有一块绿宝石的尖端闪起光来;现在轮到这块绿宝石在剧中表演。“这块绿宝石以前曾在那条运载过主耶稣的朋友拉撒路的尸体的船头上闪烁过;这条船曾平安抵过phoceans人的港口——既没有舵,也没有帆和橹。有了这块神奇宝石的保佑,一颗纯洁正直的心就能驾驭大海和风浪。”可现在陌生人既已做错了事(成了恋情的牺牲品),宝石的威力就消失了;于是他就把它送给了维塔。
紧接着发生了仙境般的奇景:维塔站在大海面前,用一种充满神奇优美的声乐的咒语,乞求这块绿宝石显灵:“哦,海啊!凶恶的大海,以您发怒的魔力;温柔的大海,以您致命的毒吻,请听我说!”大海也唱着歌作答。人声同乐队汇合,形成愈加愤怒的交响。维塔发誓她除了陌生人之外谁也不嫁。她把绿宝石高举过头,绿宝石闪着耀眼的光芒。“‘接纳它吧,大海,作为我誓言的象征,请接受这块圣石,这块神圣的绿玉!愿它的威力不再有人乞灵,愿不再有人知道它有保佑平安的美德。嫉妒的大海哟,收回您自己的,也是一个订了婚的女子的最后一个礼物吧!’接着,她用一个感人的姿势把这块绿宝石扔进波涛,大海突然发出暗绿色的光,映绿了黑色的天空。这片超自然的幽光在海面上逐渐扩散,直抵远方的地平线,大海也开始掀起巨浪。”接着,大海发出更狂暴的轰鸣;乐队鼓乐齐鸣,暴风雨来了。
渔船赶紧回港避风,其中一条好像有被撞碎在海岸上的危险。全村人都赶来观看这场灾难;但男人们都不敢冒生命危险去抢救失事的船员。这时陌生人跳上一条船,维塔跟着他跳上了船。暴风雨更猛烈了。一个大浪头撞碎在防波堤上,泛起一大片耀眼的绿光。人群吓得退缩。一阵沉默后,一个老渔夫脱下羊毛帽,拖长腔唱起“De Profundis”(《圣经》中的《诗篇》第一百三十篇,示深切的悲哀)。全村人跟着唱起来……
通过这简要介绍可以看出,这是部具有多相性的作品。内有两三个迥异的世界:维塔的母亲和情人等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基督教的象征主义以陌生人为其代表又是一个世界,充满魔力的绿宝石和能唱歌的海洋又是个神话般的世界,三者融合为一体。这种复杂性在剧中的诗文台词里已很明显,在剧中的音乐里就更突出了曲作者尝试了不同观念不同风格的音乐,有民歌、宗教音乐、瓦格纳音乐、弗朗克音乐,还有点大家熟悉的现代音乐(有点像意大利的喜歌剧)及丹第本人风格的音乐(如对感觉的细腻描写)。由于只有短短的两幕,剧情的迅速展开有助于加强上述印象。剧中的各类变化都显得很突然,丹第先生带领我们匆匆地从人的现实世界进入抽象的理念世界,又匆忙以宗教天地来到神话境界。但从音乐角度讲,该剧还是条理清楚的。丹第先生越是把复杂因素综合在一起,他就越急切想把它们弄协调。这是艰巨的工作,只有把各不同因素尽量简化并取其精华才能办到,但这样只好牺牲掉许多诸因素各自独特的韵味。丹第先生把不同风格和理念放在铁砧上猛捶一阵,加以锻造。在剧中不时可以见到这种锤炼的痕迹,以及他意志和决心的烙印;只有凭着他这种意志,他才得以把这作品焊接成一个坚固的整体。
丹第先生为他的这部“音乐情节剧”亲手写了歌词和台词等,让人想起瓦格纳也为其“音乐戏剧”亲撰脚本的榜样力量。我们已见到过一部作品的和谐因其作者的这种双重才能的发挥而遭破坏的例子,尽管丹第可能认为既谱曲又写词才能完善他的作品。但艺术家的诗歌和音乐才华并非总是等量客观。本行及旁通,不仅技巧的熟练程度不一样,就连艺术家对其分别加以处理时的性情甚至人格都会有所不同。德拉克洛瓦是浪漫主义的画家,但在文学方面他的风格却是古典主义的。著名艺术家本行很先进很革命,对其他艺术门类观念却保守落后的例子很多。丹第先生的诗歌和音乐造诣都很高,但他的理性总能同他的情感达成和谐吗?他在作文艺评论时头脑并不总和心灵达成统一。他的理性谴责文艺复兴,但直觉却驱使他欣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大画家及十六世纪的音乐家。对这种窘境,他只能靠超凡的调和能力来解决,硬说吉兰达约、利比是中世纪哥特风格的画家,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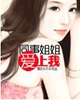
![[萧健] 月球的故事封面](http://www.diditxt.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