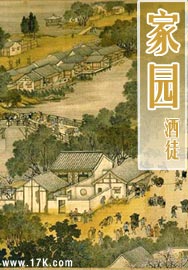����-��6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죬���ͻ�����ˡ���˹�ٶ�˹��ο�ҵ���
������˭֪���Ǹ��쵰��������������غУ����ź�Ӱ��������˹Ц���Ҹ�Բ����˹�ٶ�˹��֪��ô��������ͼ���Լ���������������������������ƭ�����������ҷ�����ȫû���ã�������˽���ɱ��Ϊ�趨�ɶ���������ʾ��Ӱ�죡��˹�ٶ�˹������Ц��
�������й涨���ɷ�һ�겻�ؼҲ�������û���κ���ϵ������»�Լ�Զ�ʧȥЧ���Բ��ԣ�˹�ٶ�˹��Ҫ��ҳ��ߣ���������������ƭ���Ҹ�����ʲô�����Ļ飬�����ƺ����������곤��û�н�飬�ҳԿ��˰�����˹�ٶ�˹�����ڿ���ĺ����ϲ�����ȥ���������ᣬ��й�Լ��ı��ƣ����������ᡣ
������С���ף��������˧�������ء����Ҿ��ŵ����ƾ���ķ���ɫ���尵��������������Ц������¶������һ��������Ц�ݿ�������Ҫ��Ҫ�����Ҹ��а飿�߶����ǿ���������
�����������������һ��������˲��������������������еľƱ������ƺ�ɫ��Һ��һ����������˵����˹�ϸ��ºͿ��������ҵ�Īŵ���ˣ���
���ţ�˵�Ǻܿ��Ҫ�ƾ����������
�������������Ǹ��õط������ҽ��ձ��ӷ����߹�����С�������������С����������ʲôʱ�飿�����һ�û������˵�����������������۾����˿�����վ�ڳDZ�����������������Խ�������DZ���ǰ���о�IJ����š�
������Щ����������һ����ȫʩ����ħ��ʹ������¶�������Ƶ�Ӱ��Ӥ��ʱ�������ڣ�������̬����������������
�����ﴫ��������������������Ϊ��������ף���յ��˲��٣������൱���ҡ�
�Ҽ����˲����������ҵ����ݣ����������Ƶ���ĸ��������˹�����档�Ǹ��ڷ�Ů�˲������ӡ����̣��һ��ǵõ�ʱʳ��ͽԽ��ʱԤ�Լ��ձ��ϵdz�����Ƭ�����ڰ�Ɲ����䳲һ�����η���ǰ������Ц���Ƿ�������Ȼ����̬���������翴������Ů�������
����ǰ���������ף����Լ�������������̸������ż������Ц�ݡ�
�Ҳ���������ʱʱ�����ȥ��
�з紩�ö�������������ī��ɫ��ȹ�ա�
�����ݣ��Ҿ����۾�ʹ�������Ƴû�������
����������������������Ц�Ż�Ӧ��������˲���������ô�f������Ҳ�����ǡ�����
��ϣ�����������������Һ�ϲ�����ֲ��ϡ�����������������Ө�����һ��������Ħ���š�
�ҿ���������ߴ����ľ���ߵ����Ӻ��������������ţ�һ�ж�����������ƽ�����ҿ���������Ȼ�ؿ��ŵ����Ƶļ�����������Ǻá�
ʱ��������£��Ҵߴ����ǻص�����ȥ����Ϊ�������ǵ�����ȱϯ̫�ò��á�
����Ҫȥ��ϴ�ּ䡣����Ц��˵�����ǿ��ȥ�ɡ���
��������ȥ��������ﲻ��Ϥ���������ſ������Ƶ��֡�
����������㣬��һ��ɳ����ϣ����Ҫ���������Բ����ϴ�����ʱ�Ĵ��������Ʊ��߱�ͷ����ֻҪ����û��������ҹ��������ļ����Ȼ������������ֶ���̫�������
����Ц�����������ҹս����ȡ�
���ϴ����ʱ�����Dz����꼶������ת��ͷ����
���Ҽǵã������촩�š���������������ҡͷ��
���Ҵ��IJҲ��̶á�����������Ц��˭�õ�������ô�����������ң�Ϊ�˳ͷ�������������һ���磬���ļ����Ӵ���ȥ���ѿ�����������ʱ������������Ȼ��ʤ���ˣ����Ƕ�ӡ����̡���
������ɭС�㣬���Ȼ��˼ά���ص��ˡ�����˵�ţ������������߽�ϴ�ּ�ĸ��䡣
�ҳ�������Щ�������ϴ�ֳ��Զ��ž�������ͷ����
�����ɫ�������������Ӱ���������˵������ҵ����֡���ϣ������
�Ҳ���������⿴ȥ��
��������ұ��������Ȼվ��¬��˹����������
��Ŷ���塭����
�����Ҹ�æϣ������
����ô��������������³�һ�����ʣ���������һ�¡��Ҹ��������������������������ϲ���ۿ�����Ҫ����������Ҫһ�����֣��������ˣ�������������
������Ҫ����ʲô����
���ܼ�������������һ�롱¬��˹����ȥ���ż�������۰����ӵĸ��ף�Ϊ�˸�����һ����ϲһ���ķ��˺ܴ���Ѫ��
�������ǻ���ʱ�䡣����Ц�Ű�ο����
�����ȸ�������������Ҫ���˿��š�����¬��˹���������˵�ţ���Ȼ�������Լ��ļƻ��С��죬���������������Ǹ��ӵ�����Ӧ������ʲô���ؿ��Ƶģ����һ������ɲ��ˣ���Ҫ������æ����һ����ɡ����õ��Ҹ�����˵һ����
�����������Dz�������֪����������ߵ����Ƶġ�����ʱ��¬��˹һ�����أ�������Բصĺ��ӡ����ðɡ�����û�ж���������߳����ȣ������������ߵ��DZ�����ȥ��
�¹�ܺã�����һǰһ���߹�ͥԺ���Ĭ�ĵ����ij滶��ؽ��š�
���ܱ�Ǹ��Ҫ������Ų��ܶ������ԾͿ������������ˡ���¬��˹��ͷǸ���Ц��
��û��ϵ��ֻҪ�����ƿ��ľͺá���
����һֱ�ߵ����߰��Ž�ɫ������¥�¡�
�Ҹ���¬��˹�߽�ȥ���������ڿռ���Ƶ���¥���������DZ�Ե˳��ʱ��������Ȧ��������ҵ�����ǽ��������¡�����������ѿ���¶��һ����ɫ��¥�ݡ�
���Ҳصĺ���ʵ�ɣ���¬��˹�Ժ��س���һЦ�������߽�ȥ��
����һ�����˲���ʱ�侫�������Ҹ�����������һ������ʹħ�ȶ��˷�����â��
¥�����̻������Ѷ�ȥ����ʪ��������Ϣӭ��������Ҳ��Ծ�������˫�硣
��о�������ʶ���Ҿ���˼�������ڼ��������ҵ�һ������Ӣ����������ׯʱ�ĸо���
�����������������ģ����ﶼ¶��δ֪�Ͳ�ȷ�������ظУ�����һ����С�ľͻ��ߴ�·����������ֹ������ѭ����ȥ��
ͬʱ����ģ����������˹�ĸ�롰�Ժ�û���ҵ����������Ҳ�֪�����߲��ڵ�����£���һ������Ҫ�����Ǹ�ׯ����ʹ�ǵ�����������ȥ�������ȥ���ɣ�һ����������֪�����Ҳ��ڵ�ʱ����ǧ��Ҫ�뿪�����ơ���
��ͷ�͵�һ������̫�����ˣ���Щ��æ����ͷ�־��һ����������ô��֮��ѹ����û�����������ľ��档�ο����ڣ������������ߡ�
������������ҪѰ�Ҹ����ᾡ���뿪��ȴ���εط����ҿ��Ʋ����Լ��ĽŲ���
��������һ���T��
���ң����е���Ҫ֪�������T����ʲô��
����㡱�Ҷ�����ת������һ����һ���ij���������¬��˹˵��˵���Լ������Ī�����
��̧��ͷ������һ�ۣ�������ǹ���һЦ���ܿ졣��
�ҷ����Լ�����ħ�ȵ����ڲ��ܿ��ƵIJ���������Ϊ�������������Ҫ�͵�Ե��ô��
�������������ꡱһ��������������������ز����Լ������飬��ȸԾ�Ĵ������εġ�
�����˹������˵������Щʱ��������ѡ�����ǡ�
�����ڱ������ߵ�С����˽��������ʱ����Ϊ����������ûʲô�����Ƿֿ�����ʹ����ֻ��һ����ʽ����ʱ�������㣬��������ȫ���綼���ԣ�����ѡ������������������ȷ�ģ�ʹ��������ȥӭ�ӷ������������ˡ���������֪�����Ҵ��ˡ�
������ѡ����������������������ѡ�����ҡ�
���Ƕ�̫���⣬���������Χ�ǻ�ȴ�Ӳ����룬������Щ��˿������
�����˹������ʧȥ����Ϥ����ò�����壬�벻Ҫ����Ⱥ�к��Ҳ����������һ��Ҫ�ϳ��ҡ�
������ʲôҲ������ס�����ǽ���ij������������꣬����Ȼ������������ߣ�����Զ�롣������˹�R�������ó��ı���αװ��
αװ��һ���۰����ӵĸ��ף��������������ֵ�������
������۵�Ϧ�����ҳ��ֶ��ݵ�ʧ����
�����ҵ�˼ά�쳣����������dz������ס��ļµ������������£��һ���������Ȼ����������
������ָ���������ڵ�ȷ�����ҵĿ���֮�¡���Υ�����ɸС�
Ȼ���ػ����ɵĿ�ϲ�ܿ챻���ĺͿ־���û��
�����ÿһ��ϸ�����ǵõ������������Dz����ҵģ��Ҷ�ô�������ǵ���һ�ε��꣬ʹ��ʧȥ���е��ж�������
�ң��������Լ����ϵ�ÿһ�����١�
����ǽ��վ�������������������ⷿ�䡣
�ҵ�˫�ְ�ס�ı�ֽ���Ǵ�Ƭ��ƬѤ�õĻ��䣬��֪�����ǽ���ʲô��
ĵ�����Ǹ�������ٸ���Ļ���
����������еļҾӶ�����ʽ�ģ���ױ̨��Բ�����³�������������ܣ�
��Щ��̾�ϸ��ľ��Ʒ��ʹ�������ɢ����Ũ�ص�̴ľζ��������Ŷ�����ʦʹ�õ�����ζ����
Ҫ���ߡ�
������Ψһ���뷨��
���ȥ����������ʽ������ľ�ţ������ܴ�
��������Ĭ�����û���á�
���д����о�����������������к���µ�ħ�������ڵ���ֻ����ӫ�⡣
����Ȼ���ڵ��ϣ������о������Ҿ���ʹ���Լ���ħ����
����ͷ�����컨�壬���в��������ŵģ��Ǿ�����
����һĻĻӿ�������������������ܡ�
û�����������ķ��䡣
���ϵõģ������趼û�б�����ͻ������һģһ����
���������е�һ�Ŷ��������صس��������DZ�֮�С�
������ǽ�ǣ�������ֻص����������յ��Ǹ�ҹ����
¬��˹���������T��
����ѾõĿռ��ͷų��ij�����Ϣ�����������ס�ҵ�˫�ۡ�
������Ӳ���ͬ�ڹ߳��ĵ����ҹ��죬���й����Բ�����������촰��
����¹�Ӵ�������б���£���Ȼ��֪������ħ���������Ч��ȴ��Ȼ��ʵ�ÿ��¡�
�����ǵ�����ô�����������뿪֮��Ž��ɵģ����������������ģ�һ�ٶ�������������������֪����¬��˹�������ͳ�����������Ȼ������ÿһ��ׯ�̳��ˡ���
���ҡ������뿪�Ժ���֪������˵ʲô�������ҵĺ������Լ���������
��տ�������������˴��СС�ij��������壬���ź�ɫ��ɴ���������ش����������¹��µ�һƬĹ�ء���������������Ǹ������ȥ��
�ҵ����Ĵ�δ��������ˮ��ʪ����ָ�ⴥ����ɫɴ������һ˲��ֻ��������Ҫ�������š�
��û�������ƿ�ɴ�����������Ҽ���֮ң��¬��˹�����Ļ�ɫ�۾������ң������侲����ʹ�ޡ�
�Ժ�������ÿһ�������������
��һ�����ڿ��������籭�ϣ����������ж���ϸ��ѯ���ҳ����Ե�ɣ��ڶ������Ǹ�����ѩ��ʥ���ڣ����ߴ�·���������˹�ң���ȴ�õ��������һؼҡ���
ÿ�ζ����������������������Ŷ�Ϥһ�У�ӵ��ǿ���ƿ�Ȩ�����硣
���벻���һ������ʲô��ϵ��Ҳ֪���ƿ���Щ��ɫɴ���ͻ����е����ţ����ҵ����Dz������Ҷ��֡��������������ĵ�Ť���һ�ţ�¬��˹ȴ����ƴ���������л��ҵ�ʱ�ڡ�����IJ���֪���㵽����˭ô�������������������ܵĹƻ���������֪�����������Ȼ���ȴΪʱ������������ߴ����ر�����
��ָ��£����ק�����Dz��ɴ��
ֻ��һ���ͻ����ѡ�
�������۾�������������ɫ���¹���ˮ��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