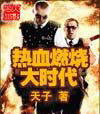大时代1958-第3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意见自然是没有的,扩大组织部门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且对外工作意味着有更多的经费支持,怎么会有人反对?
“那么我继续刚才的话题,关于我们部门一些作战力量的规划,如果同志们有意见可以打断我,这都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应该对各种军事力量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整编,提高所属武装力量的专业性。”谢洛夫双手搅在一起态度很诚恳地说道,“在应对一些国内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不会陷入被动的局面当中。”
克格勃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两大块,一块是以边防军为主的作战部队主要在边疆地区,另外一大块则是原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队,现在的内卫军。但其实克格勃各大总局下属还有军事力量,第一总局、第二总局和第五总局、分别拥有数量不等的特种渗透部队,用于处理突发事件。除了这三大总局之外,交通管理总局的交通警卫部队、国防科技保卫总局的科研警卫部队、第九警察总局的干部警卫部队、还有克格勃的基本自保力量第十五总局的机关保卫警卫部队,第十五总局的部队是驻扎在克格勃的各大机关中作为警卫。
“在这方面我们和盟国是可以合作的,在境外特种作战的领域中,我们绝对不能单独作战,而是要拉着盟国一起行动,以后将成为常态固定下来。”谢洛夫说完自己的想法等待着别人的意见。
“对于我们下属总局的警卫部队进行整编是没有问题的,更加专业当然更好,不过对外作战我们需要盟国的力量么?”伊特瓦索夫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当然了,也不能所有压力都由我们自己顶着,再说他们的力量也不弱,至少加起来不弱!”谢洛夫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其实不是所有东欧国家都和苏联一样情报部门管理边防军,波兰公安部、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部、匈牙利内务部、罗马尼亚内务国家安全总署、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部门都各有各的特点,不能全部一概而论,蚊子再小也是肉,谢洛夫不能放过他们,情报部门没人敢说自己能做到极致,哪怕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的克格勃,也必须承认各国情报部门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
然后谈了一下对于世界的监控问题方向,谢洛夫就结束了自己担任克格勃主席之后的上次克格勃主席会议,这次他担任一把手的首次会议,比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第一次开会的时候都顺利得多,和前面那两位比起来,谢洛夫完全是在克格勃成长起来的本土干部,几乎没有人把谢洛夫视为外来者,一些问题完全是内行在领导内行。
“第五总局从现在开始着重监视国内文化界的动静,任何在各种情况下流露出来对西方向往态度的作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应该全部建立安全档案,对文化界必须保持钳制,不能让第五纵队滋生在文化界。”
很快谢洛夫接任克格勃主席的消息就传遍了苏联各处,很多地方的安全干部都知道,这次的克格勃终于迎来了一个真正本系统中成长起来的干部,这应该是好事吧?
第431章 文化人
文化界一旦投敌,造成的影响将非常巨大,路线不同,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非常有道理,苏联末期的乱象中文化界绝对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克格勃第五总局虽然存在,确实是对付西方思想渗透和宗教势力复兴,但实际上目前更多对付的是后者,原来也并不难理解,赫鲁晓夫对苏联文化界时不时的言论采取包容的态度,这也是苏斯洛夫没事和赫鲁晓夫争论的原因之一。有这种第一书记存在,可想而知第五总局的工作,也仅限于采取频繁的预防性警告,真正有影响力的大作家比如索尔仁尼琴这种人,活蹦乱跳简直活的不要太滋润。
虽然心中对这个家伙充满了厌恶,但谢洛夫只能当做没有看到,闭着眼睛当索尔仁尼琴不存在。理想中的第一书记,自然性格上别向赫鲁晓夫这样有些天真,对自己有着充分的信任最好立为接班人,但实际上这两种特质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人的身上。事情就是这么不能十全十美。
“那群潜在的第五纵队,天天蹦的相当欢实,而我们的第一书记只是没事动动嘴巴让那些文化界的家伙不要乱说话,实际上那些人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谢洛夫长叹一口气对卡德波夫说道,“有时候我真的想让他们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当年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不直接死在古拉格?结果出来给我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头,要不要我们处理一批人?”卡德波夫少将比划了一个杀的收拾。
谢洛夫赶紧摇头,这是谢米恰斯内的处理办法,杀人不是不可以的,但要看回报和投入能不能形成正比,如果杀人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只会解决问题,难道以为他这头里海虎会手软么?但问题不是这样,大环境宽松克格勃如果动手玩暗杀,只会让文化界那群自认为良心的家伙炸窝,这可不是好事。
只要大环境变动了,别说索尔仁尼琴一个人,就算是整个苏联作协全死了他也不怕。因为在动手之前,国家舆论会首先收紧,切断外国人知晓的渠道,到时候克格勃做什么都没有人知道,但目前不具备这种环境。
但放过索尔仁尼琴还是有些不甘心,什么车祸、淹死致谢死法都不能考虑。因为这种死法一旦出现肯定会引起怀疑,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让这个人病死,还要做的更加像一点。
“索尔仁尼琴这个人,身体就没有什么病么?”放弃实在是不甘心,最终谢洛夫还是更进一步的问出了自己的问题,这个人一定要除掉,如果按照时间来算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应该已经开始动笔了。
为了克格勃的名誉,这个人必须死,为了苏联的名誉考虑,这个人就更应该死了。
“索尔仁尼琴原来有癌症,但是已经痊愈了!”卡德波夫也摇摇头,暗叹索尔仁尼琴的命大,在古拉格的条件下都能活过来,竟然还把癌症治好了。
“痊愈了?痊愈了就不能复发么?”谢洛夫眼中闪过一道亮色,觉得自己似乎抓住了什么东西说道,“癌症是有很大的几率复发的,有些药品不但对癌症没有抑制作用,还会促进癌细胞的再生,这就是医学的力量,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
“头,你的意思是换掉索尔仁尼琴的药品,让他的癌症重新复发,然后我们在手术台上干掉他!”卡德波夫明白了谢洛夫的意思,准备借着索尔仁尼琴的病痛要他的命。
“做的干净一点,对于这种大作家,我们尽全力的抢救,一次手术清除不了癌细胞,我们就寻找专家多做几次手术,索尔仁尼琴的岁数还不算大,完全可以多上几次手术台。给你两年的时间,时间很充裕,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谢洛夫已经打定主意让这个苏联著名的异己分子提早去见他心目中的上帝。
杀了索尔仁尼琴这个人,省的这个家伙在苏联解体之后对着俄罗斯后悔,到时候他的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苏联不会在回来。
如果谢洛夫记得没错,这个家伙和八十年代的美国总统里根很是臭味相投,因为那时冷战气氛稍缓,欧美政坛学界大吹和风;索尔仁尼琴则警告大家不可心存幻想,不是消灭苏联,就是被苏联消灭。这种主张太合里根的胃口了,他需要这种言论,好为冷战再添把火,直到拖垮苏联。更妙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简直与里根的新保守主义如出一辙,同是主张回归基督教精神,同是谴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辈子都没法化身为完美政治武器的索尔仁尼琴,这时竟然变成了里根式“新保”的助力。
他不能把这个人留给里根,里根那个美国总统说实话如果不是运气好,他的总统生涯肯定会向他的演员生涯一样失败。里根下台后的美国经济危机,就和他打鸡血的经济政策有很大关系,只不过苏联先死了,如果苏联咬牙坚持几年,以美国本身债台高筑的里根经济学后遗症,足够引爆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
很多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文化人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当你的国家已经没有资格作为美国对手的时候,你本人的利用价值就消失了。如果美苏的国力和环境反过来,谢洛夫绝对不会杀索尔仁尼琴,而是好好的对待他作为一个标杆,证明苏联对文化人非常容忍,同时在美国本土找几个被迫害的家伙进行宣传对比,可苏联没有这个条件,没资格在劣势的情况下显示国家的宽容。
索尔仁尼琴只是因为名气大被谢洛夫注意到,其他的在克格勃危险名单上的文化人,也都在第五总局特勤人员的密切注意中。在打压文化界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放松。
但这些人都没有索尔仁尼琴更加危险,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听闻他已经开始寻找在古拉格服刑的人员准备撰写小说,作为克格勃主席的谢洛夫绝不能让这件事发生。
“主席,勃列日涅夫主席已经在总部门口下车,来到我们这里参观!”就在这个时候,谢洛夫的机要秘书谢尔瓦诺夫推门报告到。
“你先回去吧,卡德波夫!”谢洛夫脸上闪过一丝迷惑说道,勃列日涅夫来卢比杨卡什么?这个时候不是应该为自己回到中央书记的岗位上庆祝么。
带着这种迷惑,谢洛夫起身准备准备汇报工作,就见到勃列日涅夫已经进来了,后面还跟着契尔年科,这位最高苏维埃秘书处主任。
“尤拉,我只是今天比较空闲所以来卢比杨卡看看,不知道我们的克格勃主席欢迎不欢迎我呢?”勃列日涅夫还是挂着那种温和的笑容,好像回到中央书记的岗位上,没有让这个已经成了苏联排名前几号的巨头喜形于色。
“当然欢迎,请坐,勃列日涅夫主席!”谢洛夫的笑容也很真诚,此时绝对不能把心中的卧槽表现出来,勃列日涅夫想要做什么,他听着就是了。谢米恰斯内那种毫无理由的装逼他可学习不过来,也不看看对面是谁?
“尤拉,三十六岁就做了安全机关的最高领导,第一书记对你的信任我们都看得到!”勃列日涅夫笑呵呵的茫然四顾,随后看到谢洛夫的办公桌上有一本书,问道,“这是什么?”
“一本西方学者写的苏联学书,我看看有什么新的观点出来了没有!”谢洛夫面不改色的回答道,“不过目前看来没让我学习到一些东西,还是那些老套的论点。通过这种学说要演变苏联,那是做梦!”
冷战时期西方的苏联研究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对于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苏联学与政治学理论之间构成了双向互动、多元协同的复杂共生关系。但由于西方苏联学所运用的真正的“内核”理论实际上只有苏联化的极权主义模式,因此,在冷战时期苏联信息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西方苏联学为了丰富自身内容,提高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只能积极借鉴和吸纳苏联学之外的多学科理论,不断扩大自己的“外延”。
这倒使得苏联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脱离了最初的极端性理论,形成了更为丰富的内容。然而,这种理论先行研究方法,在很多时候会显得削足适履,而造成西方苏联学学者在面对不断变化的苏联现实时生搬硬套既有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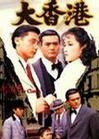
![1895淘金国度 [校对版]封面](http://www.diditxt.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