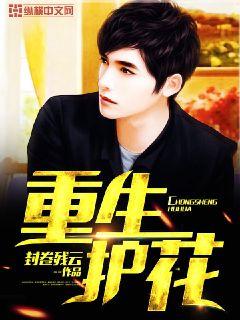重生之抗战悍将-第4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后,美国人的意见占了上3。8月27日,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一行,首先由芷江飞往南京,进行受降和接收的准备工作。下午2时,一行211人分乘的7架飞机在南京大校场机场陆续着陆。到达南京上空以后,飞机在城市空中盘旋三圈,向曾经遭受悲惨的屠城厄运的南京市民宣告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军人一下飞机,附近正在干活的农民丢下农具,舞着毛巾*帽从四面跑来,有人用篮子装着山芋、缸子盛着水送给久违的国军军人们,有人还送来新摘的水果。军人们与迎上前来的农民们激动拥抱,仿佛回到家里一般。不少的军人带着歉疚地对市民们说:“我们回来得太晚了,让你受苦了!”
9月5日,新六军坐上美国运输机飞往南京。其任务是:占领南京,控制侵华日军总部,接收京沪铁路沿线防务,确保南京、上海之间的交通畅通……
从“九一八”事变到今天,中华民族经过了整整14年的殊死抗争。在胜利时刻到来之际,国民政府决定用隆重的仪式来完成洽降、受降手续,让全体中国人充分享受百年来首次受降的喜悦———在湘西小城芷江举行洽降仪式后,国民政府确定由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各大战区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高级军政人员组成庞大的受降代表团前往南京受降,同时组织全国各大报社的记者采访受降仪式。
1945年9月9日上午,和平的阳光洒遍了曾经惨遭日军屠城的六朝古都南京。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礼堂举行。
这天南京城到处张灯结彩,人人喜形于色。一大早,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就拥到冈村宁次的车子必经的广州路、珠江路、黄埔路两侧。还有许多人聚集在收音机旁收听受降实况广播。许多的市民换上了家里最好的衣服,走出家门,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与和平。人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流露出对胜利和平的欢欣。从南京中山东路原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礼堂门前,每隔50米就竖立着一根漆成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悬联合国旗。旗杆边上,并排站着新6军的武装士兵和宪兵,头戴钢盔,身穿哔叽呢服,戴着白色手套,手持冲锋枪,威武挺立。黄埔路口还矗立着一座松柏扎成的高大牌楼,上面缀着“胜利和平”4个金色大字。
受降地黄埔路中央军校也作了专门布置,大礼堂正门上,悬挂着中苏美英的国旗。正门上方的塔楼上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以示胜利之意,下面悬着一块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14个金字。正门和其他出入口均有新6军战士和宪兵守卫,戒备森严。
礼堂正中就是签降所在,被用淡蓝色的布包围起来。受降席桌子边放着5把皮椅。礼堂内投降席与受降席之间大概相差两三米。受降席中间主座桌上放着装有笔墨纸砚的漆盒,旁边还有一个麦克3。在左右两边各有一张小方桌,一个是发文件的,一个是收文件的。投降席桌子比受降席窄,旁边有7把木椅。受降席西侧是中国和盟国高级官员观礼席,东侧为记者席,楼上是中外一般官员观礼席。礼堂大门的两侧各设一个签到处,备有两本签名册,签名册上印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签名册”字样。
在受降席的后方,12个新六军的仪仗兵站成一排。会场有一个营,还有一个宪兵连。宪兵、警卫都带了枪,不过,子弹都没上膛。
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个大型水银灯突然亮了起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上将由礼台后方走进会场,紧跟着一些国民政府和盟军的高级官员。大厅里顿时活跃起来,摄影记者争着拍照。
8时58分,由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小林浅三郎等7人,自大礼堂正门步入会场。日军军官们都是低着脑袋、哭丧着脸,呆呆地任由中外记者拍照。7名日本代表在投降席后排成横队,由冈村宁次领头脱帽肃立,向受降席鞠躬。
冈村宁次戴着眼镜,垂着头,一言不发。他平时是很骄横的,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初,他还不服气。可是,那一刻,他低下了头,放弃了幻想。受降方代表何敬之上将,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是冈村宁次的学生。冈村宁次这次不仅为失败而低头,也为自己的颜面扫地而羞耻。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原中央军校旧址)举行。受降席居中座的是陆军总司令何敬之,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墨三、陆军中将萧毅肃。投降席上有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驻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茂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7人。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方面,还有国民党将领汤恩伯、工懋功、李明扬、郑洞国等。盟军将领有美军麦克鲁中将、柏德勒少将,英军海斯中将等。
投降签字仪式在中国传统的“三九”吉时正式开始。
9时4分,何上将命令冈村宁次呈验签降代表证件。日方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恭敬地呈送到何上将的面前,弯腰鞠躬,双手向何上将捧呈相关证书和文件。何上将一一检查后留下。小林于是退回原位。
接着,何上将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用双手捧接,低头展阅。
小林在一旁帮他磨墨,冈村看完后,拿出毛笔蘸墨,他的手一直在抖,他盯着毛笔看了一下,顺手捏下了毛笔上的散毛,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紧接着,他又从上衣右上方口袋里取出一块印章,蘸了印泥后哆哆嗦嗦地盖了下去,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此时是1945年9月9日9时07分。因为紧张,冈村的印章盖歪了,他面露难色,又无可奈何,只得让小林将他签名盖章的降书呈交何上将。随后他立即起身肃立向何上将深鞠一躬,向中方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骄横跋扈的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刻,终于无条件宣告投降。
9时15分,何上将命令冈村宁次等退席,仪式至此结束。
仪式结束后,中国陆军总司令、中国受降代表何上将发表讲话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这对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从此开一新的纪元。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南京受降后,中国战区除东北地区由苏联受降外,共划分了16个受降区,分别接受日军的投降。
台湾、澎湖地区是第16受降区。
10月1日,中国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上校奉命携带一面国旗,亲自驾驭单机飞赴台北机场,直趋日本驻台北总督府,严正要求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陆军大将下令所属部队立即放下武器,降下总督府日本国旗,悬挂中国国旗。当中国军队第七十军由基隆登陆前来收复台湾时,台湾同胞群情激奋,从基隆至台北只有30公里,第七十军军长陈颐鼎等所乘专列竟走了4个小时,可见沿途欢迎人群之众多,情绪之热烈。
10月25日上午9时,台、澎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现更名中山堂)举行,中国受降官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担任,先在受降席就座。然后,安藤利吉等5人由中方人员引入会场。他们向受降人员脱帽鞠躬行礼后,即将所佩军刀解下呈上,以示台湾日军缴械投降。安藤双手颤抖地拿着降书细阅后,即用毛笔签名并加盖印章,然后呈交陈仪签名盖章,台湾日军代表签降,宣告了日本侵略者在台湾50年殖民统治的正式结束。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国内各处举行的投降仪式,刘建业是无法参加的。一来是因为没有接到来自国内的命令,他不能擅自行动;二来是因为随着美军进入东京,中国军队就要离开东京了,前往按照协议被分配给中国军队的占领区是日本本州岛的关西,中国;西国等地区,包括爱知县和岐阜县,美军占领关东,北陆,奥羽一带还有四国岛和北海道,英国军队则占领九州岛。中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设在日本的第二大城市大阪,具体的位置就是日本的大阪旧城。
刘建业并没有跟随部队一起前往大阪,因为,现在他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9月8日,麦克阿瑟及哈尔西、艾克尔伯格等一行人从横滨驱车前往东京。
来到美国大使馆,麦克阿瑟站在办公大楼的台阶上,对艾克尔伯格说:“把我们的国旗展开,让它作为被压迫者的希望象征,作为公理胜利的象征,在东京的阳光下荣耀地飘扬吧!”于是,艾克尔伯格命一名仪仗兵把那面曾飘扬在美国国会大厦和“密苏里”号上空的国旗升上旗杆。这时,军号吹响,在场的许多人面对此情此景“眼睛都潮湿了”。
麦克阿瑟决定把家就安在使馆里,而把总司令部设在商业区皇宫对面的第一大厦。使馆在大轰炸中虽未受大的破坏,也未被日本人占领,但是馆内仍破烂不堪,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有的房间地面上还淌满了水。士兵们忙了几天才把使馆收拾得整洁了一些,原来的一些老佣人也都陆续被召了回来。一切准备就绪后,麦克阿瑟即派人去马尼拉接他的家人。
第一大厦距使馆只有5分钟的汽车路程,其所有权属于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麦克阿瑟选中六楼的一个带空调的小房间作他的办公室,据说这里原来是一间储藏室。他把办公室当作一个幽闭独处的场所,连部电话也不安。室内布置得也很简单,只有一套旧沙发、一张办公桌和一个书柜,唯一的装饰是墙上挂着的华盛顿像和林肯像。
9月19日,麦克阿瑟的妻子琼和儿子阿瑟及老保姆阿珠,还有在马尼拉新近请的家庭教师吉本斯夫人,乘飞机在厚木着陆。麦克阿瑟和一名助手未带任何武器去机场迎接。在返回东京的路上,琼看见路两旁有日本兵,担心地问:“安全吗?”她的丈夫回答说:“绝对安全。”
麦克阿瑟之所以有这样的把握,是因为他对日本人有充分的了解并对自己所采取的立场有充分的信心。他在进驻东京之初即宣布:“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并非抑制日本,而是使它重新站起来。”这是他在总结了历史上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拿破仑实行占领时的经验与教训后得出的结论,当然也借鉴了他父亲老麦克阿瑟将军在菲律宾,还有他自己一战后在德国莱茵地区的占领经验与教训。在莱茵地区驻防时,他亲身体验到“军事占领形式所带来的根本弱点,文官权力为军事权力所取代,人民失掉了自尊和自信,不断占上3的是集中的专制独裁权力而不是一种地方化的代议制体制。在外国刺刀统治下,国民的精神和道德3尚日益沦丧;占领军本身也由于权力弊病渗入到他们队伍中而产生了一种种族优越感,从而不可避免地堕落下去”。他认为,在这种一方为奴隶而另一方为主子的占领状态下,“几乎所有的军事占领都孕育着未来的新的战争”。因此,他要求同盟国驻日占领军尽量采取一种克制和善意的作法以赢得日本人的信任与合作,并确定了“一切占领政策都将通过包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