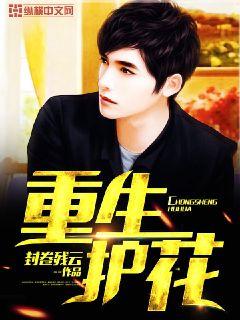重生之抗战悍将-第40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午饭后,希特勒和他的“新娘”同部下告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不久后,外边的人们听到一声枪响。希特勒坐在沙发上,用一支7.65毫米口径的手枪,冲着自己的右太阳穴开了一枪。他的头奇拉下来,血从脸上流下来,流到了沙发和地毯上。一旁的爱娃;勃劳恩吞下了剧毒的氰化钾,脸上肌肉抽搐,双脚蜷缩在沙发里。卫队长格林和几个随从军官走进来,用毛毯裹起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一起抬着走出地下室,放在总理府花园的一个小坑里,浇上汽油,然后把点燃的纸卷扔了上去,火焰熊熊燃烧起来。苏联红军的炮弹仍不时地落下,在花园里爆炸,格林等人只得站在地下室入口处看着。
随后,法西斯的第二号党魁、第三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模仿希特勒,先毒死了6个孩子,然后命令部下开枪打死自己和妻子。
最后的战斗发生在国会大厦,国会大厦是由1000余名SS的德国士兵和外籍志愿兵守卫,SS的德国士兵保卫国会大厦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群外籍志愿兵,为何愿意为德国做战到底,至今为止仍然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理由。国会大厦的战斗极其之惨烈,双方逐层逐屋的进行争夺,保卫者们勇敢的抵抗这进攻者,大部分保卫者都战死了,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证明了他们的忠诚,也实现了他们的荣辱和誓言。“忠诚既是吾之荣誉!”4月30日22时50分,俄国人终于占领了国会大厦的顶层,镰刀锤子旗帜被插在了国会大厦的屋顶。
5月2日早晨6点,柏林城防司令维尔丁将军离开了地下掩体,来到崔科夫将军的指挥所,向俄国军队投降。下午3点,剩余德国守军部队全部停止抵抗,向俄国人投降,柏林保卫战以德国的失败,苏军的胜利告终。
而在太平洋战场上,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琉球岛上。
面对着盟军地面进攻部队的日军防线,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共长十公里,大部分都是海拔标高不大的小山丘,上面长满了松树、丝柏、杉树、灌木和蒿*,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防御工事。实际上,山丘下面地道纵横、盖沟交错、有的坑道深达二三十米,任何炮弹也揭不开它的顶盖。日军已经摸熟了盟军的战术,他们修了良好的防炮洞,毫不在乎美军铺天盖地的炮击。由于双方距离太近,舰炮也发挥不出威力来。等蒙军发起冲锋,隐蔽在坑道中的各种口径火炮都推出来,按领先精确测定的距离实施毁灭性的射击,往往把阵地前沿打成一片火海。每次攻击几乎都重复同一个步骤,美军的炮火伤不着敌人,敌人的炮火却屠杀着盟军士兵。
日军沉着冷静,恪守唯一的战术原则:尽可能地迫使盟军大出血。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状况,盟军部队不得不进行了战术上的调整。
为了检验和示范新战术,很久没有亲自上战场的刘建业也再一次的披挂上阵。
刘建业的装甲指挥车在泥泞的便道上开赴火线。一路上,到处都是烧焦的美军坦克,缺了轮子的曰本山炮、青石砌成的龟甲墓。遍地泥水,有的尸体来不及掩埋,在水洼中泡得又肿又涨。曰本人没有**,山丘上看不到任何活的东西。刘建业在泥水中匍匐前进,用一架很大的炮兵望远镜一寸一寸地搜索敌人阵地,结果只能看到光秃秃的树干和密密麻麻的弹坑。
刘建业组织了一次认真的冲锋。事先,他同炮兵联系好,把敌人阵地划成方格,实施密集射击。他又从美军的342喷火坦克营调来三辆喷火“谢尔曼”,编入新14师的坦克营中,指示他们烧毁任何火力点。他对连队做了动员,人员轻装,该丢的东西都留下来。“别给我们中国人丢脸哪!让美国人他们瞧瞧,仗该怎么打。”
炮火把山头打得硝烟**。坦克几乎跟着弹坑推进。刘建业也钻入一辆闷热的“谢尔曼”里,前往观战。穿这美式军服的中国士兵发起了冲锋,几乎没费多大劲就到达了山顶。日军的火力醒过来,切断了冲锋部队与后续部队的联系。接着,一阵雷鸣,大量山炮炮弹和迫击炮弹落到山顶的中国士兵中间。他们在光秃秃的山顶上躲无处躲。美军的观察机就在头顶上转,却找不到放炮的准确位置。中国士兵被钉死在山顶上,每分每秒都在伤亡。士兵们的修叫声甚至压过了炮弹爆炸声,胳膊、大腿和肠肚被炸得到处都是,其中一些噗噗地打在刘建业乘的坦克上。
“谢尔曼”找不到目标,只好对残树桩烂树丛乱烧一气,不久,就被敌炮击中。公平说句话,整个太平洋战争中,也就是琉球岛上的日军炮兵打得最准。
刘建业命令驾驶员开上山坡去抢救伤员。经过反复努力,终于运出了几名伤兵。刘建业的坦克第三次冲上去,被一枚75毫米山炮炮弹击中。车舱里全是烟,车长下令撤退。刘建业连*带爬才从火线上撤回来,后背让炮弹片削了一块皮。四名坦克手仅回来一个人。黄昏,日军利用反斜面的屯兵坑道发动了反击,残余的陆战队士兵被赶回来。
在这些被日军占据的高地上,进攻一方的部队必须一个个清除日军的火力点和隐蔽的火炮,其中有些是从首里纵深打来的150毫米榴弹炮,否则,占领地面阵地就没有意义。
但是,要做到这一切谈何容易。
连日天气恶劣,阴云不开,豪雨滂沱,地面全是烂泥。炮兵校正机无法观察目标,连美国海军陆战队引以自豪的小轰炸机也无法活动。战斗僵持着,一个个起伏的山丘仿佛在嘲笑刘建业的无能。
尽管自己在首次进攻里显得十分狼狈,而且还挂了彩,但是,刘建业此时还没有失去应有的理智。他决不会为了虚无缥缈的荣誉悍然浪费士兵的鲜血和生命。琉球岛的大部分已经被盟军占领了,最主要的读谷机场和嘉手纳机场早就被美军的工兵部队修复并投入了使用,盟军的总体优势不可动摇。此时的急躁只会招致失败。
他指挥士兵一寸一寸地蚕食日军的阵地。用许多炮火加强一个排的姿态,有时冲上山坡拼命死守,配合炮火大量消灭反冲锋的敌军。每占领一个山头,他就加强阵地,打退敌人的反扑。天气又湿又冷,人也精疲力尽,士兵脏得象从泥浆池中捞出来,军官的脾气凶得怕人。伤兵在泥水中痛苦万分地挣扎,拖尸兵往往被敌人的冷枪打中。牛岛的部队是关东军精锐,一向以枪法准确、训练严格著称。有一次,美军派来的军医给疲惫不堪的中国士兵发了兴奋药苯异丙胺(就是现在俗称的冰毒,当时战争双方都把这个东西当作军需品使用,以提高士兵的兴奋度)。后果是始末料及的:躺在泥水里连动也懒动的士兵变得焦躁易怒,有人产生幻觉,另一些人看见双影,根本无法瞄准。只有伤兵减轻了痛苦,但有一个老兵粗鲁地抓起刘建业的胳膊:“我说伙计,那不就是安谢河吗?你快看哪!”
刘建业末置可否,安谢河还远在二千码外的山谷里,它被群山遮拦,根本看不见。刘建业很伤心。
那老兵烦躁了:“连安谢河都看不见?喏,”他手一指。指尖落在一丛烧焦的灌木上。“那里,清清楚楚,河水闪闪发光,河面上还有木头漂下来。”
身为部队的长官,刘建业的沮丧和创痛是难以形容的。这些年以来,他与鬼子打过那么多仗,几乎没有一仗是轻松的。他的痛苦中夹杂着愤怒,日军已经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却死也不肯投降。曰本人的部队伤亡越大,打起来越红眼。他看过各种各样的日军尸体,被乱枪射杀的尸体,被喷火器烧得卷曲的尸体,被炮弹开膛破肚的尸体,他从未怜悯过敌人。但是,刘建业无法把敌人从地下挖出来。
刘建业带着一个团又发动了一天进攻,伤亡达五分之二,仅仅占了两座山头。从其中一座山头上,已经可以看到浑浊的安谢河。它原本是一条溪流,连日大雨,河面漫到一百多英尺宽。正如那位得了癔病的老兵所说,上面漂浮着乱七八糟的木头。除了木头,还有涨鼓鼓的尸体:牛尸、马尸和赤裸的人尸。
当盟军高奏凯歌渡过莱因河、易北河、维斯杜拉河、奥得河和多瑙河等欧洲最著名的河川的时候,刘建业和他的骄傲的大军,竟无法抵达一条世界上最短最无名的溪流—-安谢河。
中国军队虽然进攻速度迟缓,但是,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同样也陷入了与日军的反复争夺战里,迟迟无法打开局面。因为地形的原因,美军的坦克无法顺利抵达日军阵地附近,自然也就无法顺利的向日军阵地的洞口倾倒混凝土,美军不得不采用与中国军队一样的战术,在喷火坦克的直接支援下,一寸一寸的使用步兵部队蚕食日军的阵地。
尽管盟军的进攻速度并不快,但是总还算是在前进。日军的防御阵地正在中美两国军队的攻势下一点点地被蚕食。
第三次冲锋失败以后,白朔负了伤。他率领的二百人连队,能开枪的只有一半了。他的目标是安波茶高地。他记不住很长的日G假名,因为他喜欢吃美国后勤军官给他们发放的巧克力夹心糖,所以他管这里叫做“巧克力高地”。
白朔气愤得鼻子都歪了,黑色的眼睛更小了,起皱的眼睑象面包上的一圈黄油包围着小眼睛。严峻的局面和严重的伤亡挫伤了他的热情。
白朔不象刘建业或巴克纳那样热衷于追求荣誉,他是个很实际的下级军官。柏林什么地方的打得如何与他的“巧克力高地”无关,他只想多杀些曰本鬼子。
尽管从民族感情上来说,他极为痛恨曰本人,但是从军人的角度上来看,他并不愿意轻视他的对手。他知道防御者比进攻者享有的优势,蔑视决不会带来胜利,反而会流更多的血。
由于及时卧倒,一枚日军手榴弹在离他三码的地方爆炸,使他只患了轻度的“炮弹震荡症”,脑子嗡嗡响了好久。他很害怕,害怕在桂林时候被日军炮弹造成的脑部伤会重犯。结果还好,他伸伸胳膊和腿,手脚都听使唤。他祈祷中国的各方神仙能够帮助他拿下“巧克力高地”。
安波茶山在大名高地东北方约半英里处,海拔只有230米,守敌是日军第三十二联队。它与大名高地又为犄角,正好拱卫着一英里纵深后面的古城首里。日军牛岛满中将把第三十二军的司令部设在首里,军属远程炮群密切地支援着安波茶山和大名高地。
季节3引起连绵不绝的降雨把琉球岛上简陋的道路网全毁了。洋面上台3频繁,白沙海滩到处是被吹翻的舰艇残骸。车辆陷到泥里,卡车没到车帮,吉普连顶也淹了。155毫米榴弹炮陷在泥路上,拖拉机去拖,连自己也陷没了。白沙滩头到安波茶山仅九英里,却要用飞机来空投补给品。曰本人的电台天天喊“神3”。结果召来一场妖雨。
刘建业前来看望白朔的连队。
“喂,白朔,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刘建业问白朔。
“谢谢。天气糟透了。我一直在想下面应该怎么打这一仗,无论如何,我们得设法潜入敌人的坑道网里。每次炮击,他们都躲到安全的地方,他们算准了我们攻上阵地后躲在哪里,然后就是一顿手榴弹。”白朔晃晃负伤的左手掌,痛得钻心。
“白朔,你都受了这样重的伤,我看你还是到后面的医院里好了,对你来讲,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