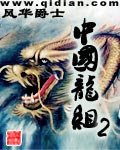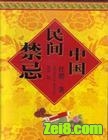中国震撼三部曲-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卫淼酶谩�
今天国内一些人还天天在贬低自己的国家,开口闭口西方如何,对于真正了解西方的人,着实有点贻笑大方。其实西方也好,中国也好,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今天的中国人对西方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而是要平视,唯有平视才能把自己和对方都看得比较清楚、比较准确,才不会被别人随便忽悠。
国内流传了一种说法:西方是“好山好水好寂寞”,中国是“好脏好乱好热闹”,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多数中国人的确害怕寂寞,喜欢热闹,所以即使有“好山好水”,时间长了也寂寞难耐。但这个说法只是看到了西方“好山好水”的一面,没有看到西方“好脏好乱”的一面。我讲的西方内部的“第三世界化”,其主要特征就是脏、乱、差,还要加上吸毒泛滥与各种犯罪情况频发。同样,中国确实有“好脏好乱”的一面,但中国壮丽秀美的大好河山还在,“好山好水”的地方也非常之多。尽管中国也像西方历史上一样,为自己的工业化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但中国模式总体上的纠错能力比西方模式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可能引领世界的新能源革命,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由过去解决温饱的“雪中送炭”阶段进入了全面实现小康的“锦上添花”阶段。通过不断努力,中国“好脏好乱好热闹”一定会转变为“好山好水好精彩”,古人说的由“乱”到“治”也包含了这层道理。
还是回到移民的话题吧。随着中国的崛起,移民问题将越来越去政治化,变成钱锺书所说的“围城”现象,即“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换一种方式生活早已是全球化后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必做过多的政治解读。此外,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任何一个谣言都可能忽悠一大批不明真相的人,一个“去伊拉克可以发财”的谣言,大概可以让10万人上当,一个“去阿富汗可以发财”的谣言,大概可以再忽悠10万人。这些年,中国“公知”编撰的美丽动听的美国故事早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难怪很多移民美国的国人竟然以为美国拥有“优厚的社会福利”,对美国的资金监管、税收、遗产继承等均毫不知情,直到移民美国后才恍然大悟,但悔之晚矣。
中国人口基数大,移民的比例迄今为止仍然非常之小。以我自己的观察,即使今天由于种种原因而移民欧美的所谓中产阶层人士,绝大多数都把自己的根留在国内,包括自己的企业和资产等,因为他们也了解至少今后的二三十年内,中国仍将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每年流入中国的资金也远远超过流出的资金,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从2009年的2万亿美元一跃到2014年6月的3。99万亿美元,远远领先世界外汇储备第二大国日本的1。28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的32%)。'2'〃留学人员回国已成潮流。2012年当年留学回国人员已达27。29万人,同比增长46。56%,占当年出国留学人数的70%左右,形成了“史上最大的回国潮”。2013年,回国的留学人员再创历史新高,达到35。35万人,比2012年又增加了29。53%,也就是8。06万人,相比之下,当年的出国留学人数仅增长3。58%。'3'专家预测,未来五年,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历史拐点,中国将从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国,转变为世界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有些人担心贪官移民,其实我们也不用过分担心。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加,贪官迟早要被通缉遣返回来,赖昌星都被遣返了,其他贪官还能持续在逃多久?
从中长期的战略视角来看,适度规模的移民其实对中国的利远远大于弊。世界上最具有移民倾向的肯定不是中国人,而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就是英、美的主要族群,过去三个世纪中他们移民到了全世界,按人口比例,他们一定是移民最勤的族群。但回头一看,效果不错,英国的影响力随其移民和语言也扩散到全世界,使英国至今享受着远超其国力的国际影响力。一些老喜欢把中国移民问题政治化的人,不妨思考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台湾地区已经“民主化”20多年了,台湾的人口是2 300万,比上海还少,但一般估计,至少有150万台湾同胞在大陆工作、生活或学习,如果一定要从意识形态解释的话,这不就是“用脚投票”吗?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大陆过去30多年如此大规模的留学生现象。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到2013年为止,留学生人数加在一起共305。86万人,其中72。83%学成后回国发展。'4'假设中国移民的人数能达到留学生一样的人数,那也才300来万人,即使再增加两倍,也就是900多万,少于我们一个苏州市的人口。这些人以后回来也好,长期待在海外也好,保留中国籍也好,加入外国籍也好,对中国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中国的利益已经覆盖全球。如果有一批人愿意克服重重困难,在海外安营扎寨,并最终加入到推动中外关系的事业中来,海内外华人一起推动整个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这才是真正蔚为壮观的前景。
我在《中国触动》一书中曾提及,有媒体问我,你是不是认为中国已经比欧美好了,我说,我没有说过欧美比中国好,也没有说过中国比欧美好,因为这样的比较太笼统、太简单。如果你看重的是官方汇率计算出来的人均GDP,那么非洲的赤道几内亚都比中国好,但它首都一半居民连自来水都没有。如果你像大部分国人一样,认为只有拥有房产才有幸福感,那么中国比瑞士要好得多,瑞士住房自有率只有中国的一半。如果你喜欢社会治安好的地方,那中国比美国好无数倍。如果你喜欢吃西餐,那么法国更好。如果仅从有品质的生活角度来说,一个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中国人生活在上海或者海南应该比生活在纽约或伦敦自在和舒服得多。对于一个仍在奋斗的年轻人,中国能够提供的发展机遇也远远多于西方。'5'
突然一想,国内极端自由派的最后一张王牌,不就是他们想象中的无比美好的西方世界吗?当这张王牌也失灵的时候,他们还剩下什么东西来帮着美国忽悠中国呢?而这种王牌的日益失灵已是一个趋势。中国崛起的广度和力度及其所提供的大量发展机遇,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从未见过,一个人能够亲历、参与和见证这个充满奇迹的时代当属真正的幸运者。如有人要放弃这种幸运而移民,把自己国内的位子让给别人,还极有可能培养出更多的爱国热诚,那岂不是太好了吗?
二、从中美首脑峰会说起
“一出国,就爱国”也是一种历史记忆。2013年6月7日至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别开生面的中美高峰会。这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也就是28年前中美之间举行的另外一场元首高峰会,一场我本人亲历的高峰会。2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中国与美国呈现了此长彼消的发展大势,中国“追赶”的速度之快、“超越”的势头之猛,令人感叹万千。
1985年7月下旬,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访问美国,随行的还有副总理李鹏和国务委员姬鹏飞等。我随团出访,担任李鹏副总理的英文翻译,参加了这次很有意义的外交活动。李先念是一位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浴血奋战、立下卓著功勋的战将,也是新中国建设的卓越领导人。从1954年开始,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长达26年。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当选为国家主席,出访美国时已76岁高龄。我印象中的李先念既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不乏幽默的长者。
记得出发前一个星期,全体出访人员参加了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预备会,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向大家汇报出访的准备情况,他提到白宫欢迎晚宴正厅限定参加人数,中方为14人。李先念笑着说:“那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当介绍到出席白宫欢迎宴会要着民族服装,请大家穿深色中山装时,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道:“美国不是最讲自由吗?怎么还要统一着装?”
比较28年前后的两次中美首脑会晤,最大的差别首先是形式。李先念主席的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美。美国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詹姆斯·利利(James Roderick Lilley)在访问前对记者吹风:“此行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1985年7月21日上午10点,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南草坪为李先念主席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高奏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李先念主席和里根总统分别致辞。里根10天前刚做了结肠肿瘤切除手术,就来主持这个仪式,对中方客人彬彬有礼,热情友好,致辞时还两次使用了中文,一次是说“欢迎”,另一次是说“互敬互惠”。李先念答辞也很得体:“总统先生,看到您迅速恢复健康,我感到十分高兴。你现在亲自接待我,使我深为感动。”
国事访问有光鲜亮丽的一面,如隆重的欢迎仪式、盛装的欢迎晚宴等,中国当时确实十分看重这些礼仪和形式。一个刚刚走出“文革”内乱,现代化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大国,渴望得到外部世界的足够尊重和平等待遇。今天中国仍然看重这些礼仪和形式,但我们已经可以放下这一切,因为我们更自信了,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我们已经很乐意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进行更为随意、更为务实的非正式会晤。
正式的国事访问有其长处,但各种礼宾的繁文缛节经常会占用双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28年前的访问中,双方考虑到里根总统刚刚动过手术,只为他安排了三场活动,一是欢迎仪式,二是正式会晤,三是欢迎晚宴。细数一下,双方首脑交谈的时间并不多。欢迎仪式上,双方领导人只做了最简单的交谈,然后就是照本宣科的致辞。随后的正式会谈只有一个半小时,翻译又去掉了一半时间。欢迎晚宴的安排,按照美方当时的礼仪,里根总统与李先念主席的夫人林佳楣坐在一起,李先念主席与里根总统的夫人南希坐在一起。我着实感到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似乎不多。
我陪李鹏副总理和乔治·布什副总统坐在第二桌,望着两位国家元首和夫人的第一桌,发现他们确实没有太多的交谈。倒是没有夫人在场的李鹏和布什坐在一起,交谈甚欢。布什展示了自己对中国的喜爱,戴着自己在中国购买的“上海牌”手表和中国生产的领带,除了交谈外交和战略的大话题外,他们主要聊的是周恩来。布什说,他对基辛格很有意见,因为在北京担任中美联络处主任的时候,基辛格会晤周恩来总理时从来不让他参加,未能见到周恩来是他一生的遗憾。
会晤形式的变化也反映了两次访问的定位差异。28年前出访的定位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美国”,目的是“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两国关系,加强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而这次习奥会晤则被定位在“战略性和历史性的会晤”。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第一次会晤就提出了三大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来实现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