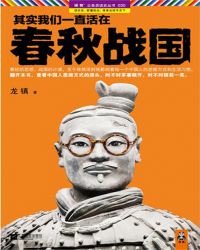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玲姐每次跟别人介绍我,都说我是她表弟。起先,我心里不舒服,后来也只好随她了。我也习惯了。
许可佳说:“好像在哪里见过的。”她伸出手看看,“我手上有水呀。”
玲姐开玩笑似的说:“见过的啊?那就拥抱一下。”
我努力留住脸上的笑容,望着许可佳,不用说,我感到这种拥抱不合适。同时又感到,我主动提出来不拥抱,好像也不合适。合适我做的,好像只有保持微笑。我记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
许可佳望着玲姐笑了,说:“这是要干什么呀?”
玲姐说:“拥抱一下又有什么?”
我很尴尬,手足无措这个词大概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许可佳似乎也很尴尬,笑的时候,抬起手腕遮着嘴。玲姐挥了一下菜刀,说:“两个小傻瓜怎么光知道笑啊!”乘许可佳不注意,玲姐不轻不重推了她一下,许可佳朝我怀里扑过来了。
我几乎是本能的张开臂抱住了她,感到全身里里外外都有点发僵。我长这么大,除了玲姐,我不记得我还跟哪个女人拥抱过。
许可佳在我怀里扭了一下,推我的动作并不是很坚决,不过很快离开了我,嘴上嚷嚷着“讨厌,讨厌”,朝玲姐扑过去作势欲打。
玲姐站着没动,乐呵呵地笑着,许可佳第一下打在了玲姐头上,要打第二下的时候,玲姐才抬起一只手护住头,笑着逃进了厨房。许可佳跟着追了进去。我听见厨房里笑得地动山摇的。
这天晚上剩下的时间过得不太自然,玲姐乐呵呵地看看我,看看许可佳,说你们俩个差不多大,怎么搞得像有代沟呀。
我和许可佳只是笑,互相几乎不说话,要么装作对电视很感兴趣的样子,要么只跟玲姐说一说。看完一盘碟子后(我现在记不清那盘碟子的具体内容了,好像是香港喜剧),许可佳起身告辞,玲姐让我送许可佳出小区,到大街上去打车。我立刻站起来走在前面,打开每一层楼道的电灯,站在楼下等许可佳。许可佳一出单元门,就出了一口长气,像是刚从深水里浮出来的一样。接着,不知道她怎么把自己弄笑了,乱笑一阵后,对我说:“你表姐真搞笑,到底什么意思嘛!”
()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还是走在前面,头也不回。许可佳问:“你们是姑表还是姨表?”我胡乱嘟哝了一句。她紧走几步,追上了我,又问了一遍。我说:“是姑表加姨表,那种拐了很远的表亲。”
许可佳格格地笑了,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没几分钟,许可佳的下一个话题又来了。
许可佳后来说了一些什么,我几乎没听进去,只是随口“嗯啊”着。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就放慢了脚步。在不太熟的女孩面前,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不时从许可佳的话中挑出几个字,然后重复一遍——这是从“新好男人”训练课上学来的,不料威力还不小,许可佳的谈兴越来越浓了。她上了出租车,出租车慢慢启动的时候,她还从车窗里伸出脑袋来跟我说了几句话。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跟女孩说话。直到20岁,我都弄不清楚该跟女孩说些什么。在女孩眼里,我是一个严肃乏味的人,一些女孩刚跟我接触时,甚至会觉得我生硬傲慢。实际上,我非常渴望跟女孩说话,非常喜欢听她们说话。有时候女孩们美好的声音一响起来,我甚至会听不进去她们在说些什么,她们像是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歌唱,她们像是一些正在演奏的乐器。我曾问玲姐,我是不是有那种什么“表达障碍”之类的毛病啊。玲姐说:这是“酷”嘛,一个人的特点。当时我还真有点高兴,觉得占了天生的便宜。此后的几天里,玲姐跟我聊别的事的时候,还不时冒出一两句格言: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等。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宽慰我。又过了几天,玲姐才开始给我上交流训练课。这天晚上能跟许可佳说这么多话,可以说,玲姐的训练课初见成效。
送走许可佳后,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心里忽然格登一响,今天怎么没人来打牌啊?这个念头飘荡了几下,很快像风中的柳絮一样不知道飘荡到哪里去了。但有很长时间那隐隐的不安还在,虽然说不清在哪儿。
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说有事要回去了。玲姐有一会儿没说话,然后让我不要在街上呆太久。我嗯了一声,她才把话筒搁下。
第三部分
星期六去书店里泡了一整天。午饭是在书店旁的小馆子里吃的,能感到塞得满满当当的大脑跟肠胃功能一样有些紊乱。那一阵子,我很不喜欢一个人在馆子里吃饭。如果吃饭跟机械加油是一回事,吃饭就真是一个麻烦。平时我在公司的食堂里麻烦,周末,如果不去玲姐那里,就只有上馆子里麻烦了。
回到书店,去美食专柜那儿转了转,很佩服那些写吃的人不厌其烦。不知不觉转到隐私专柜,看到更加不厌其烦地写性的书籍,大都写得很坦荡,找不到什么秘密能对付我的另一个麻烦。一小圈转下来,忽然意识到整个人性对于我来说就是麻烦。食和色,照我的理解,本来都应该是欢乐的,是大自然给苦难人生的微薄奖赏,现在却都成了一个21岁小伙子的麻烦。
在书架前呆呆地站了几分钟,慢慢想起了我的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书,也是在这家书店买的,想到我往这儿扔的钱应该够多了,麻烦却一个也没见少。我把已经挑好了的两本书放回去,两手空空走出了书店。
傍晚的北京,天空浑黄,车流和霓虹让人燥动不安。空着肚子在街上乱走了一气,我决定还是到玲姐那里去。玲姐接到我的电话时,说她还没吃晚饭,还说她刚买到了我喜欢吃的武昌鱼和蕨菜,“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的心情一下子欢畅起来了。走进地铁之前,朝缓缓降临的夜色看了一眼,觉得这好像是个不错的开端。假如今晚运气再好一点的话,也许可以解决另一个麻烦。
玲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我走进来,才开始拆蕨菜的真空包装袋。闻到厨房里一阵一阵飘过来的清蒸鱼的香味,我知道鱼已经做好了。如果不是因为蕨菜这东西太过娇嫩,也会炒好了的。一起走进厨房,我给玲姐系上围裙,看见煲着的汤在沙锅里轻轻翻滚,看见树影在窗外轻轻晃动,我意识到自己在等待一件事情发生。
我们一边做饭,一边闲聊着。忽然想起在书店里翻过的一本美食经,上面描写过这种下厨的情景,说跟亲密的人在一起做饭,饭菜里总会多出一些滋味。此时此刻,我觉得那个作者品尝到了人生的真味。
没多久,玲姐就聊到了许可佳,很不经意的样子。
在此之前她聊到了几个女孩,在此之后也聊到了几个女孩,都是我知道的。有的在棋院里见过,有的在玲姐家的牌桌边见过,有的只是在电视里或报刊上见过。玲姐把许可佳放在这堆女孩子里面,放在随意说说的琐事中,一点也没有要突出许可佳的意思。但我的耳朵,像是给轻轻弹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
玲姐说:“也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减肥的,随便吃,总也不见胖。”
我没搭话,想听她接下来说什么。
她接下来聊起了另外几个女孩减肥的故事,然后问我对减肥怎么看。我谈了一些看法,玲姐也谈了一些看法。那些看法基本上不值得在此重述,仿佛当时重要的只是聊天。减肥,顺手捞着的一个话题而已。
我们在餐桌上继续聊着。
玲姐给我夹了一块肥鱼,问我觉得公司里几个女孩子怎么样,接着;问我觉得许可佳怎么样。
虽然我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许可佳的名字再次灌进耳朵里的时候,心里有个地方还是晃动了一下。我慢慢嚼着嘴里的东西,尽量显得镇定一些,可能是太镇定了,突然给一根鱼刺卡着了。
我忍着痛,轻轻地说:“才见一面,哪知道人家怎么样和不怎么样。”
玲姐笑了,说:“你们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呢。”
窗外的树影晃动得更厉害了,天光更加浑黄。昨天晚上坐在街边长椅上感觉到的那一丝不安,现在飘荡在室内空气里了。我已经明白;为我找女朋友的事并没有过去。那件事依然隔在玲姐和我之间。现在,又要浮出水面了。
玲姐问我:“你怎么啦?”
我说:“我没怎么呀。”
“声音好像不对劲。”
我没说话,想听她继续说许可佳,想听她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玲姐又问:“你没事吧?”
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喉咙里实在太难受了。我说:“我好像卡着了。”
玲姐跳起来,奔到厨房里去拿醋。我咳嗽了几下,没有喝醋。玲姐更着急了,说你快点喝下去呀,慢点往下吞呀。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喝醋没有用。我走到卫生间里呕吐了几下,吐出了一些不该吐的东西。我走到沙发那儿打开电视,电视里在用动画演示沙尘暴的移动路线。
玲姐拎着醋瓶子追过来,说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没用啊。
玲姐倒了一些醋在碗里。我接过碗,立刻回到餐桌边;又往碗里加了一些醋,扔了一根鱼剌进去,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在等待醋碗里的鱼刺变软或不变软的那几分钟里,我意识到自己在生气。我走到阳台上去站了站,空气微微有点呛人,也许真的要刮沙尘暴了。我觉得,我生的气和天气正在互相影响。
十分钟后,玲姐到阳台上来了。她说:“还是到医院里去吧。”
我问:“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啊?”
玲姐说:“怎么突然就扯到相信不相信上去啦?好吧好吧,怪我怪我,是我没搞清楚,以前只是听人家说,给鱼刺卡着了要喝醋的。”
道理本来很简单,在这种普通的食用醋里,能软化鱼刺的那种化学物质,含量根本不够。可我一说话,喉咙里就很痛。不能把这个道理清楚地说出来,这个道理本身就像一根鱼剌一样卡在我喉咙里,卡得我直想冒火。
我转身走进屋,在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眼泪一直在流。透过泪水,我看见沙尘暴被动画设计师画成了一大团黄褐色,像一头庞大的变形怪兽,从西北某个荒凉的地方一跃而起,直扑北京。
玲姐在一旁给什么人打电话,问鱼刺卡着了怎么办。喝醋,可能有人把这个经不起检验的“常识”告诉了她。玲姐说不行不行,接着引用了我半个小时前的实验结果,有点激动地反驳着对方。
又是半小时后,玲姐要我跟她到医院里去,我不肯去,她说:“你就让我省省心吧。”
我说:“我死不了的,你不用担心。”
她声音大起来了,“怎么这样说话啊?”
我回答她,怎么说我也不去,我说一根鱼剌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能感觉到一根小小的鱼剌,正变得越来越重大。它卡在我的身体里,固执地占据着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带给我疼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类似快乐与恨意混合在一起。我带着喉咙里的一根鱼剌走来走去,从这间屋子到那间屋子。
玲姐一直跟在我身后,坚持要我去医院。我只是摇头,摇头,摇头。我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