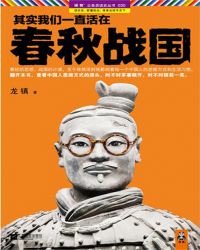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什么坏事也没干呀?”
玲姐从皮包里掏出一张报纸,说:“你自己看看吧,这可怎么得了?”
顺着她的指头看过去,版面左中位置有一条新闻。标题是《以星星的名义,见证浪漫爱情》,副标题是《中国大陆第一例用恋人的名字为星星命名》。内容不用多说了,提到玲姐时,报纸上有一句:“享受这一殊荣的是一玲小姐”。一玲就是玲姐的名字,在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申请表上,我没有填玲姐的姓。
“啊,这个呀?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这个又怎么啦?”
“你还有心情装傻,呜呜呜,我都要被你害死了,呜呜呜,你干脆窝心一刀,让我死个痛快得了,呜呜呜。”
我说:“没那么严重吧?”
玲姐走到卧室里去躺下了,只是哭,不理我。我哄了她一会儿,进厨房里看了看,冷锅冷灶的。打电话叫了送餐,然后又坐到床上去哄玲姐。她还是哭,不理我。
我觉得在路上硬起来的心肠一点一点泡软了。我用手揩干她的脸,说:“不要呜呜嘛,有话好好说好不好?”
“我不管,你惹出来的事,你自己去收拾。”
“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怎么收拾?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上午有几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详细采访,我现在还想着要不要答应呢。”
()
玲姐马上坐起来了,“你答应吧你答应吧,你就想着顺自己的意,全不管别人死活。”
我有点生气了,说:“过了晚上十二点,我就给报社热线打电话。”
玲姐又躺下了,背冲着我,不时抽泣一下。餐厅送餐来了,我叫她起来吃饭,她也不理。我怕把她哭坏了,饿坏了,拖她起床,结果把她连被子一起拖到了地上。她就裹着被子蜷在地上继续哭着。我忽然笑起来了,想起了两年前我有一次生气的情景。那一次也是她叫我起床吃饭,我不理她。她把我拖到了地上,我就裹着被子躺在地上。
我蹲在她面前又哄了她半个多小时,她才又开口说话了。她告诉我,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有个同事拿着报纸问她,这个一玲是不是她。她当时吓得要喘不过气来,慌忙说不是她,天下叫一玲的人多得很。同事撇了撇嘴,说:“我估计也不会是你。”那语气仿佛是怎么可能有人这样追求玲姐,玲姐气得差点又喘不过气来,差点说:“那就是我!”说到这里,玲姐渐渐缓和一些了,她抓着我的手,求我千万别再把事情闹大了,尽量控制局面。还说结婚的事急不得,这么久就这样过了,也不在乎急着要那个形式。我说你先起来吃饭吧,别的一切都好说。她要我答应不接受记者采访,我同意了。不到一秒钟,我就后悔了。我怎么能这样就同意了呢?她裹在被子里又是哭,又是不吃饭,这阵势,我也真是没见过。
正在微波炉里热着饭菜,韩总一个电话把我叫到茶艺馆里,要我找个高段棋手陪一位大客户下棋,公司出钱都可以。聊了几句后,我知道了那位大客户是长江水文局的一位负责人,以前在城陵矶做观测员时,闲来无事,自学围棋,在业余棋手中没遇到过什么对手。他这次进京,是想在几家通信系统公司中选一家,做长江沿线的自动观测数据处理系统。我估摸着他的实力顶多也就跟常四段差不多,不想让别人把这笔费用赚去,就找到了常四段。
我有很久没见到常四段,他瘦得吓人。常四段告诉我,他这几天心中大乱,没法子跟人下棋。前天他老婆在棋院门口堵住了林秘书,抓头发撕脸,一脚就把林秘书踢流产了。看着常四段那副悲痛的样子,我也很悲痛。默默坐了几分钟,常四段帮我联系到一名女专业棋手后,我就告辞了。几天后我给常四段打了个电话,常四段说,正在跟老婆谈判。漫长的离婚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想想真要问情为何物,世间最美妙的是男女间的感情,世间最折磨人的也是男女间的感情。
站在棋院门口,等那名女棋手的时间里,我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许可佳有一会儿没吭声,突然大声说了一句:“小天,你好……好……好你个品位不俗的大混蛋!等着吧,本姑娘跟你没完!”说完咔嚓一声挂了机。
这一声咔嚓在我大脑里嗡鸣不止。我抬头望着星空,飞马座和仙女座的四颗亮星组成了一个大方框,从方框北面的两颗星引出一条直线,向东延长一倍半的距离,就是白羊座。我找到了一玲星,望着它,心中渐渐寂静。
路上给女棋手塞了8000块钱,然后把她带到了茶艺馆里。我悄悄对韩总说,今天我很头痛,想回家了。韩总皱了皱眉,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我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儿许可佳的话,想着那近乎陌生的声音,觉得这下可以肯定她明白我的想法了。她生气骂我几句也是应该的。也好,用不着我亲口说那些想法了,甚至连普通的谈话也可有可无。如果她再多骂几句更好,让她发泄出来,我心里也更舒坦一些。跟许可佳交往一年,最后用一个大混蛋的形象在她心里定格,但愿她能为结束感到庆幸。难过是会有的,我也一样。这种难过我能够理解,但我没有什么办法。
半夜里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母亲一开口就抱怨我让她不省心。等她的唠叨告一段落了,我才明白是许可佳刚给她打过电话。
母亲说:“可佳在电话里哭得昏天黑地的,害得你娘亲也陪着哭,真是烦死了!”我没吭声。母亲继续说:“这叫什么事嘛。我已经帮你遮过几回了的,你怎么还没处理好?现在揭开了闹,闹成了这个样子。”我还是没吭声,不知道说什么,继续听母亲说下去。慢慢知道了许可佳跟母亲通话的大概内容。
许可佳告诉母亲,晚饭前她爸爸像往常一样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报纸,突然跳起来,一边撕报纸,一边大骂不已,把眼镜都摔碎了。许可佳接下来就知道了命名星星的事。许可佳问母亲:“小天他为什么?小天他为什么?阿姨你也说过是表姐的,为什么这么一个老表姐!你们合伙骗人么?”母亲支唔了一阵子,说具体怎么回事,她还不清楚。然后要许可佳把事情弄清楚,先别这么激动。末了,又安慰许可佳说:“这事顶多就是小天那个糊涂东西太年轻,一时糊涂。他一个人也糊涂不到哪里去。相信他表姐决不会跟着他糊涂的。等我什么时候打电话问问他表姐。”
说到这里,母亲问我现在的打算是什么。
我说:“我还糊涂着呢。”
母亲说:“你不会真把她娶进门吧?”
我说:“为什么不会?只要她愿意。”
母亲停了一下,说:“这事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好不好?”
我说:“好的。”
母亲又停了一下,说:“你这孩子,我现在也差不多弄明白你是怎么回事了。谁说什么你嘴上可能不反对,心里面怎么想是谁也不知道的。可做母亲的,有些话却不能不说。该说的,我在北京的时候已经跟你说得差不多了。我也知道,你现在长大了,我说什么也不管什么大用。你想怎么办,自己琢磨好了,就算你年轻经得起折腾,只是不能折腾得回不了头呀。妈求你,至少先别急着结婚好不好?”
我说:“妈呀,别说什么求不求的啊,我经不起。你说的话我会好好考虑的。”
母亲在电话那头笑了笑,说:“算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不早了。我都折腾累了,困了。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像扫帚星下了凡一样。”
接下来有很长时间,许可佳没找过我,她的声音也没在我耳朵里出现。只是做梦的时候,有两次梦见了她噙着泪水的眼睛。
一天,我把许可佳给我和母亲打电话的事都对玲姐说了,玲姐告诉我,有一个星期,许可佳天天去玲姐单位里晃悠,从这间办公室到那间办公室。许可佳的父亲在单位里负点小责,那些办公室里不少人对许可佳挺热呼的。有两次玲姐从某办公室门口路过,听见里面传出
笑声,转过脸就看见许可佳正连比带划地说得起劲。许可佳看见了玲姐,要么突然不说话,要么压低声音。玲姐再往前走,双脚重了很多,不知不觉走错了地方,还差点从楼梯上摔下去。她开始感到一些同事的眼神有些异样,有些目光像针扎过来,有些目光在扒她的衣服。突然有一个上午,许可佳走进了玲姐办公室,停在玲姐的办公桌旁微笑。玲姐顿时感到脸上一阵灼热,下意识地拿起一个文件夹挡在胸前。说到这里,玲姐对我苦笑了一下,说:“我也真是神经过敏,担心她会干出什么傻事来,毁了我也毁了她自己。”
许可佳摘下耳环,在手中抛了两下,说:“铃姐,这一对小东西,麻烦你还给你那个表弟好不好?”
玲姐勉强笑了笑,说:“佳妹这不是要考我的反应嘛?我还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呢。这些日子我东忙西忙瞎忙一气的,没顾得上关心你们。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许可佳也笑,“不敢再劳你关心啦。帮个忙,把这个还给你表弟就好了。其实你交不交给小天,大概都是可以的。”
看见有的同事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在朝这边观望,有的同事在跟许可佳笑着打招呼,玲姐觉得许可佳塞进她手里的那一对耳环,滚烫滚烫的。她能感到掌心在出汗,能感到掌心的脉跳。耳朵里嗡嗡的。
有个同事去饮水机那边续完水,端着茶杯从身边走过,问了句怎么回事。许可佳就把我母亲送给她耳环的过程讲了一遍,连先前送的一只祖母绿宝石耳环被我弄丢了的事也讲了。末了,转过头对玲姐说:“不知道那对耳环会不会落在了你家里。”
玲姐说:“你是在开玩笑吧?我有点反应不过来了,像得了老年痴呆症似的。走,我陪你上家里找找,找得到找不到我们都可以放心了。”
说完,要拉许可佳离开。许可佳笑了笑,说算了,她还有事。看见许可佳走出了办公楼,玲姐才回到办公桌前接着做事。没几天,许可佳又来了,依然这个办公室坐坐那个办公室坐坐,玲姐的办公室也不例外。玲姐对我说:“有时候真怕她会敞开了闹,有时候又宁愿她敞开了闹一场。”
我说:“怎么能这样?我找她谈谈。”
玲姐说:“这事你是谈不清楚的。说起来,到眼下为止她还不算是恶的。以后怎么样就不知道了。”玲姐叹了口气,说这也是她自作自受,怨不得许可佳。接下来把三年前她是如何在许可佳身上用心的事,大概说了一下。三年前,她给我安排的相亲一次又一次失败后,她就想到了这种古老的相亲形式可能有问题。她虽然急着为我找一个女朋友,好让女朋友拴住我的心,不再纠缠她,但她已经明白这事不能急。精心挑选了许可佳后,她仔细研究了许可佳的喜好,然后有针对性地训练我,有针对性的影响许可佳。这个过程历时近两年,把我塑造成许可佳认为的比较理想的择偶对象后,才安排我和许可佳第一次“不期而遇”,然后不时鼓励许可佳追求我,鼓励我追求许可佳。听到这件事,我心里猛地被震动了一下,像一堵墙轰然倒塌,秘室里的机关一下子暴露在眼前。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没等大脑里激荡的尘埃落定,韩总就打来电话要我陪他去天伦王朝参加一个酒会。路上,我昏昏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