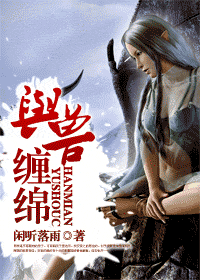水与火的缠绵-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个月之后,邝园和黄汉香结婚了。再几个月,黄汉香生了一个大胖儿子。曾芒芒不止一次地看见在太阳下出游和归来的邝园一家3口。曾芒芒的心里一片怅惋。怅惋也是一种疼,一种钝钝的落寞的疼。
党支部组织委员找曾芒芒谈了话。曾芒芒同志,我们这一次发展新党员,你还得往后靠一靠。组织上希望你不要在生活小节方面分散自己的精力。曾芒芒说:'好的。'车间主任也找曾芒芒谈话了:曾芒芒同志,你是我们厂推荐到公司的先进工作者,按说这个季度的奖金应该给你一等奖。可是,大家只给了你三等奖。希望你严肃认真地对待个人生活。曾芒芒看着自己的鼻尖,点头。
被领导找过谈话之后,群众就会用敏感的目光看待你了。曾芒芒就要做出昂首阔步谈笑风生的姿态,表明自己的清白了。曾芒芒自己都有点不认识自己了。
曾芒芒夜晚的觉不再踏实,一个噩梦老是缠绕着她。醒来之后,情节不再连续,只是隐约记得一个女人被剃了阴阳头,在群众大会上被批斗。一只大脚,朝女人的腰间踹了过来!疼痛的却是曾芒芒。
曾芒芒大叫着,挣扎着坐了起来。宿舍的电灯被拉开,有姑娘走过来,举起巴掌在她面前晃动。有一天半夜,曾芒芒瞪着眼睛,对面前晃动的巴掌说:'别晃了。刚才我已经吃过了。'
3个姑娘吓得大叫起来,奔逃出去,敲遍了所有单身宿舍的房门。这是因为宿舍流传着一个恐怖故事,故事发生在某学院学生宿舍。一个姑娘患有梦游症,每天半夜都会悄然出门,去生理解剖室,生吃尸体的内脏。而曾芒芒在半夜里忽然承认她'刚才已经吃过了'。有一个胆小的姑娘找到厂行政科,要求调换房间。姑娘的理由是:曾芒芒疯了,她的脑子出毛病了。
曾芒芒没有办法继续上班了。在心情最糟糕的一天里,曾芒芒吃过午饭就发生了强烈的胃痛。厂医说是胃痉挛,给她喝了颠茄合剂。然而,曾芒芒又腹泻了,泻得离不开厕所。医院的诊断结果是:精神性腹泻。曾芒芒知道,自己不能再去车间了。
曾芒芒惟一的去处,就是上北京看望爷爷。
爷爷曾分田是曾家的伟人和奇迹。他们这支曾姓家族,世世代代从事小农耕作。但爷爷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了。爷爷不仅改写了曾家的历史,还改写了曾家的姓氏。酷爱诗歌的爷爷,从主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一句诗中得到灵感,为他自己改名,叫做曾分田。获得了土地之后出生的儿子,取名曾分地。爷爷还武断地决定,将来曾分地的第一个孩子,名字一定得叫曾忙。新中国成立之后,爷爷定居首都,拥有了一座古老的四合院。
曾芒芒幸运地成为了曾分地的第一个孩子。她的名字,从1933年开始,就等待着她。1958年的春天,当曾分地严格地遵从父亲的旨意,给女儿取名'曾忙'的时候,'浑球!'爷爷说,'这是一个女孩子啊。女孩子要温柔,要娇丽一点的嘛!叫'芒芒',多好听啊!'
爷爷的小女儿燕子,结婚5年没有孩子,遭到丈夫的嫌弃。大家说:怎么办?爷爷说:很好办,离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芒芒,芒芒,你的血管里流着爷爷的血液呢!此时此刻的曾芒芒,必须去北京!她必须去一趟爷爷家!
爷爷曾分田派了他的警卫,在北京火车站接站。举着一张白纸,上面是爷爷用毛笔写的3个大字:曾芒芒。爷爷79岁了,又是将军,他是不便来接站的。爷爷曾分田背着手,站在四合院的枣树下,迎接他的孙女曾芒芒。
'芒芒,一下火车就看见你的名字了吧?最醒目吧?字写得漂亮吧?当然,早知道你已经长得这么漂亮,我会写得更漂亮一些。'爷爷嗓音洪亮,满不在乎地自吹自擂,说话间就朝孙女儿伸出了自己的双臂。
红奶奶跑出来了。爷爷的第二任妻子红奶奶,在包饺子,双手沾满了面粉。红奶奶说:'芒芒啊,真是想死我们了!'
红奶奶的后面,又跑出了她的女儿燕子。燕子只比曾芒芒大6岁,小的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耍和逗打,从来就是没上没下的。燕子用手指掐了一下曾芒芒的脸颊,曾芒芒嚷道:'爷爷,燕子怎么这样没轻没重啊!'曾芒芒一到爷爷家里,就有话说了,整个人就活起来了。
爷爷曾分田,率一家4口,围坐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饺子。他们和曾芒芒说话,问寒问暖。曾芒芒的所谓6次恋爱,在这里,被全部否定了。这算什么恋爱?手都不曾碰过。与锅炉工邝园的交往,充其量也就是革命友谊罢了。
红奶奶拍案而起,质问道:'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今天的红色江山。这些干部们,怎么就不懂得珍惜呢?怎么就不懂得要进步,不要倒退呢?在芒芒的个人问题上,不就充分表现了一种可怕的倒退吗?'
微笑不语的爷爷,把曾芒芒带到他的书房,说:'芒芒,给爷爷研墨。'曾芒芒为爷爷曾分田研磨了香墨。爷爷铺开宣纸,抄录了宋代词人苏轼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爷爷要说的话,全部都在这词里了。曾芒芒不敢说她全都明白,至少她领会了关键的意思。
这个夜晚,曾芒芒踏踏实实地入睡了。曾芒芒已经完全恢复了自信:她应该自己寻找男朋友,她应该主宰自己的命运。
于是,高勇出现了。
高勇似乎早就守候在前面的三岔路口,等待着曾芒芒路过。
这天,一群男女青年,在轮渡上,从武昌到汉口,他们要去参加一个婚礼:肖克的婚礼。肖克是曾芒芒大学的同班同学,诗人。肖克要结一个惊世骇俗的婚,他的恋人大他7岁,二婚,拖个10岁的小孩子,是五芳斋甜食馆卖汤圆的女服务员。肖克的婚姻遭到双方家长的强烈反对,女方的母亲甚至和女儿断绝了母女关系。但是,肖克坚决要结婚,因为爱情俘虏了他。
这是秋高气爽的一天,曾芒芒站在船舷边,心情复杂难言。高勇也站在船舷边,他与曾芒芒之间,隔着两个陌生乘客。某一时刻,曾芒芒会忽然觉得有两道目光扫过她的后背。
轮渡上的人都在用面包逗着水里的江豚。一只手出现了,高勇的手,递给她一小块面包。曾芒芒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两位乘客退开了,高勇靠近了,曾芒芒接过了面包。与此同时,曾芒芒明白了今天在她的背后,落下了谁的目光。曾芒芒将面包一点点地撕碎,洒向在江面上嬉戏的江豚。江豚很高傲,自顾自玩耍,憨态可掬。曾芒芒笑了。高勇也笑了。他们并没有面对面,却都知道对方在微笑。曾芒芒冷静地意识到,她的生活中,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一艘客轮,缓缓地驶过轮渡。客轮远去之后,巨大的排浪打了过来。轮渡猛一摇晃,高勇赶紧扶了扶曾芒芒,但随即,便收回了他的手。高勇懂得体贴女人要很有分寸。高勇嘴唇紧闭,表情肃穆,远望着,高深莫测。高勇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好看的男青年,显得比别人深沉。曾芒芒忽然觉得高勇似曾相识。原来高勇已经先于自己的形象,潜伏在了曾芒芒的盘算和理想之中。
轮渡到岸了,人们站了起来,蜂拥到门口。曾芒芒忽然问高勇:'你几班的?'高勇意外地愣住了,立刻回答:'我不是你们学校的。'曾芒芒问:'去参加婚礼的吧?'谁料高勇却说:'不,去阻止婚礼!'曾芒芒的眼睛亮了:什么?高勇迟疑了一刻,他还是抓紧时间告诉了曾芒芒:今晚的新娘子名叫高兰,她就是高勇的大姐。高勇又迟疑了一刻,有点破釜沉舟地说: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姐弟。最后一刻,曾芒芒收获了她觉得应该出现的结局:高勇告诉了她一个私人的秘密,她点头收下。仓促之中,他们毕竟还是建立了一条自己的通道。这一天,肖克的婚礼照常进行,高勇没有能够阻止事态的发展。他提前离开了,没有特意来与曾芒芒说声再见。
三天之后的一个傍晚,曾芒芒的单身宿舍。有人敲门,曾芒芒抢着去开,是高勇,身后还有一个青年。曾芒芒胜利了!曾芒芒没有流露出喜悦,她很平常和自然,好像与高勇认识了100年。她为同宿舍的3位姑娘淡淡地介绍说:'这是我大学同学的朋友高勇,这是高勇的朋友……'高勇接过去说:'常声远。'首次配合,他们还算默契。常声远是高勇的好朋友,他们是大学同学,不同专业,但是同在学校篮球队。常声远似乎进门就明白了自己扮演的角色,他主动地与曾芒芒打了招呼。喜欢说话的常声远为高勇争取了空间和时间,高勇却说不出多少话来。高勇翻翻她床头的小说,明知故问地说:'喜欢看小说啊。'而曾芒芒,只用点点头就够了。
半个小时之后,高勇和常声远告辞离去。
曾芒芒的恋爱开始了,平淡无奇,连她自己都有气无力。
高勇又来了,常声远在他的身后。高勇给曾芒芒带了一套《基督山伯爵》。
常声远从挎包里拿出了一包瓜子和花生,放在桌子中央,请大家吃。高勇很少说话,是腼腆还是深沉?曾芒芒太需要了解了。姑娘们都喜欢与常声远说话。她们了解到常声远是搞水生物研究的,马上就要去读研究生了。她们也了解到高勇是电器设备技术员,是工农兵大学生。姑娘们明显喜欢常声远,一致认为他聪明善良又可爱。高勇则一般,不风趣,有架子,算是一个单纯的年轻人吧。
高勇第三次来到曾芒芒的宿舍,就是他一个人了。他拿出一本书,递给曾芒芒的同时用目光暗示了她一下。曾芒芒翻开书,里面是两张电影票。曾芒芒迅速合上了书,高勇则客气地与姑娘们说再见。他将会在外面的马路边等候曾芒芒。他们在铺满落叶的人行道深处相会了,然后步行去一家稍远的电影院看电影。
转眼就是深秋了,日子过得很平静。一周看两三次电影。电影票总是高勇购买,高勇总是在人行道的深处等候曾芒芒。偶尔在电影散场之后,他们去吃点夜宵。当然,也是高勇掏钱买票,然后持票去窗口领取食物。谈恋爱的过程如此平静,使曾芒芒大惑不解。
感情生活,应该如此平静吗?忽然,有一天,曾芒芒决定去常声远的单位看看。看看常声远在干什么,看看常声远对于高勇的真实感觉。
这天,常声远正在为江豚体检。'欢迎光临!'常声远说,意外的惊喜从他的眼睛深处掠过。他们到他办公室去坐了一会儿,曾芒芒不经允许就翻看了常声远的论文草稿,她大声念出了论文的标题:《论淡水豚与海豚的哨叫声》。常声远强行制止了曾芒芒,他用力捉住她的手,夺过了文章,批评她的无礼。
晚饭后,他们在水生所的鱼塘边散步。接着,他们打了两局羽毛球,常声远带她去淋浴室冲了一个热水澡。洗澡出来,曾芒芒只得穿上常声远的衣服。常声远用研究室的烘箱烘烤曾芒芒的内衣。在等待内衣烘干的时候,他们坐在办公楼后面的山坡上,眺望夕阳。
曾芒芒玩得太高兴了。她很久很久,或者几乎可以说从来没有玩得这么放松、放肆和开心。
曾芒芒说:'声远,高勇爱玩吗?'曾芒芒突然袭击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