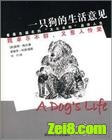慈禧后私生活实录(前清宫廷女官德龄著)-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且它们还能仗着这一些浊水的滋养,不断的长叶子,长蓓蕾,一直到开花。
脚底下,有一条厚约两寸左右的地毯,铺遍了这一座小朝廷的全部它的质料是天鹅绒,它的颜色是浅蓝,这样已是很够美丽的了,何况上面还有一簇簇的金色的图案画堆砌着,都是些牡丹花和鸟中的凤凰,的确可以称赞它一声“金碧辉煌”。
这一间屋子里的窗洞,却并不象太后那间寝室里的窗一样的阔,大约是三与二之比。这些窗的所以较前者为狭,乃是故意造成的。那么为什么要故意这样造成呢?说来也是很可笑的:因为太后有一种极浓烈的嗜好,便是欢喜玩弄伊自己所有的一切珍宝;当伊决定要上奉天去的时候,同时,伊就想到要把一部分的珠宝古玩,带上火车来。伊虽然并不曾把这个意思明白告诉我,或庆善,或李莲英,但我们根据伊平日的嗜好而推测,大家都早就明白了。于是便由庆善在监修专备太后乘坐的那一辆火车的当儿,定下了一个计划,就是把车窗开得小一些,使中间都留一些空隙,就在这些空隙上,加钉了许多式样各不相同的小架子,准备给太后安放那些珍宝。这一项设计居然大为太后所称赏,在伊没有上车之前,就忙着都人把那些珍宝尽先安放上去,待到上车之后,伊越发左顾右盼的看得出神了,倒象是伊自己从前并不曾看见过一样。
窗虽然是比较的狭一些,可是上面所挂的帘幔,却尤比那小小的寝宫里所用的来得考究。幔的本身还是一般的用不绣花的黄缎制的,但下面又多了一排用金线做的短须,这样便觉得格外的好看一些了。车壁上也漆着许多五色斑斓的壁画,不过画的内容已偏重于故事;而这些故事,又都是从中国那些有名的旧小说或传奇上摘下来的。譬如象“姜子牙斩将封神”,“关云长千里走单骑”,也不乏激发人们忠孝心的用意。就是在那四个满盛鲜花的大瓶上,也同样有这种故事画绘着,而且是绘得很精细的。
太后生性很欢喜花,除掉那四个大瓶里所供养着的四种之外,伊另有许多小巧玲珑的花瓶,——每一个花瓶都有一只特制的红木架子,雕刻得非常工细。——东一个西一个的随意安放着。瓶里也盛着一些水,然后拣伊自己所爱好的几种花草,教人截断了长的梗子,分插在里面浸润着。因此,这一座小朝廷上差不多已满布了花的香味,何况那些花的颜色,又都是异常的悦目!
除掉那一间小小的寝宫,和这一座富丽无比的小朝廷之外,这一辆火车所余的地位已是很有限的了。但在后端,也还有两间斗一般大的小房间栏出着,一间便是供给我们几个女官当不轮到值班的时候,在里面休息着,以便随时承应太后。在这一间屋子的后面,还有一间比较小一些,其中只安着一具小小的炭炉,那是专给太后预备茶水用的。负责照料这件事务的太监便是张德,也就是每次当太后进膳的时候,站在旁边拜会碗端茶的这个人。然而在事实上,他的地位已较别人为高,这些烹茶煮茗的小事情,那里还高兴认真担当,好在也没有人去监察他,他尽可以在那些小太监里面,挑一两个比较精细些的来代替他工作,待到太后要茶喝的时候,却仍由他自己端上去,这样太后当然不会再根问他了。提起喝茶,我不妨附带的报告一声,太后是一个很有研究的“品茶者”。伊所常用的茶叶,也有好几十种;茉莉和莲花,只是最普通的两种而已。其余许多,真是名目繁多,记不胜记,且多是外面所不经见的希品,因此它们的名称,尽有至此刻还不听见有人道及的。
这辆车上,虽然分成了四间不同的屋子,但我们的趣味的集中点,当然还是那一座列车上的小朝廷。在这一座小朝廷里,可以随意发出不同的号令来,教这列整齐的列车向前开,或向后退,或停止;不但如此,便是关于中国全部的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种种变动和更调的主动力,——太后的上谕,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也无一不是打这仅占半节车厢的小朝廷里发下去的。
在我们那间休息室和这一座小朝廷的中间,也是同样的用一排很精致的木板隔离着,而在这一排木板的上部,另有一个非常庄严的华盖装置着,象一柄撑开的伞一般的笼置在上面。它的底下,便是太后的御座。在宫中,在颐和园里,专为太后所备的御座,多至一二十张,它们的尺寸,都较车上这一张来得高大,可是外观的形式,却是一般的美丽,并无丝毫上下这些御座的原料,都是用的最高贵的紫檀木,上面还满缀着无数的珍珠宝石,到了晚上,兀是闪闪地发出耀眼的光来,可是在那坐垫上,为着要求坐的人舒服起见,当然不能再用什么珠宝,但就是一方单纯的杏黄色的丝绒,也已十分夺目了。在这一张御座的后面,照例不可避免的有一幅插屏安着,它的质料也是紫檀木,漆得非常光亮,上面也有价值绝大的美玉和宝石镶嵌着。然而没有人能够说出它有什么实在的用处,只知道它总是和御座相连的!凡有御座,后面必有插屏,凡有插屏,前面必有一张御座。这两件东西简直已成一套不分离的家具。据说这个习惯,历代相沿已久,固不仅清宫中而此。可惜没有人能够说得出当初是怎样造成这一种特殊的习惯的!
我方才说御座后的那架插屏,谁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实在的用处,但到了火车上,却就显出它的一部分的功效来了。太后向例是时常要睡午觉的,于是我们便特地替他备了一张小小的软榻,安放在这一座插屏的后面,让伊在白天里,可以随时休息,也无须特地回到那一间小小的被动宫里去。
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这一次的旅行才开始的当儿,在永定门车站上,太后由我和另外几个人扶掖着,初次踏上了这一具新颖的交通利器之后,伊最初似乎很有几分为难的神气;因为虽然这一座小朝廷和那寝宫中的布置,都已经过了许多人的设计和努力,较之宫中所有的各座大殿和寝宫,已级神似,尽可够得上称赞一声“匠心别运”,但是它们的面积,却终为火车的地位所限,无论请教任何一位大工程师,怕也没法子能把它扩大出来。而太后往日又是习惯于宽敞宏大的场所的,一旦突然置身于这样狭窄的屋子里,精神上当然要感觉到几许异样。然而过了五六分钟,伊也渐渐地习惯起来了。第一句话,伊便吩咐那些太监去查看清楚伊的这一张御座的方向,是不是确和这一列车前进的方向相同,因为伊觉得如果背转着身子,让这一列火车拖着伊,老是向后倒退的话,对于伊尊严是十分有关系的。这一点问清楚之后,拉着伊又发出了许多的命令,打发那些太监去用心布置那车壁上所吊着许多古玩玉器;大概是伊对列们所用的陈列方法,兀是不能认为满意,帮不惜出心裁,再把它们来重新陈列一番;及至变更妥当,伊自己看看也觉得无可疵议了,才下令开车。除掉这些古玩玉器之外,伊对于其他的一切装设布置,如壁画,窗帘,花瓶,地毯等等,都表示十二分的合意,因此伊的精神也较往日格外兴奋一些。伊那时候的年纪虽然已将到七十,但伊一上了车之后,便满脸都现着得意的笑容,指东说西的高兴得真象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拿到了一件新的玩具一样。而其中最使伊感觉到极度的得意的一点,便是在这列御用火车上,皇太后的权威的显露,尤比别处来得清楚,影响也特别的迅捷;伊只要低声地哼一句,整列的火车,就会前进,后退,或停止了。同时,伊这一座小朝廷又可绝不费力的在分兵所统治着的土地上随意移动,这在那时候的人的目光看来,的确可算是一桩万分得意的事情。
当我未曾进宫以前,不但在外国已经坐过了无数次的火车,便是在自己国内,也曾搭过好几次火车,都不觉得有什么异样的感触;惟有这一次的旅行,却使我从最初的一刹那起——便是在准备的时候——就怀了一重极紧张的情绪,自始至终,老是紧握着两大把的冷汗,惟恐有什么意外的祸事要发生。因为太后根本没有见过火车,也许火车的种种行动,对于伊不免有些不惬意的地方,这样,路上便不用想平安无事了!尤其使我担心的便是那火车初开时的一震,这一震对于别人,当然决无影响,可是对于太后,就不能说了。无奈不论全世界上那一个老资格的司机,要他在开车时绝对不使车辆震动,怕是一桩永远没有的事情吧!至少限度,目前在这里替我们开驶这一列御用火车的司机,他就没有这样好的本领!
开车的命令下去了,火车便正式开始行动起来;这时候,我们大家都端端正正地站立在那一间小朝廷里。太后一个人高坐在御座上,满脸堆着笑,正待好好地领略作初次乘坐火车的滋味,不料整列的火车,猛可里望后一退,又猛可进而往前一冲,震得我们几个人都几乎突然翻倒,而同时车壁上那些小木架上所搁的许多最为太后所爱好的古玩玉器,已因受不住这一震而纷纷地掉下来了。这样一来龙去脉,可真把我吓得魂飞天外了!一个苦力似的司机夫,竟敢大胆把太后所心爱的东西震落到地上来,他还能不受一番严厉的惩处吗?我想其时在皇太后的心上,或者确然有这种思想。不管伊究竟有没有这种思想,但是我们却也不能再照顾那司机夫了,我们还是赶快照顾照顾自己吧!因为这一列火车上的布置,差不多全是我和庆善两个人所主办的,便是在车壁上另装这些小木架,以备太后安放伊的古玩玉器的主意,也是我们所定下的;如今北京城不没有出其不意,光是火车第一个行动,这些东西已全掉下来了,要如火车再往前行去,以后的把戏还能说没有吗?我想这些人的中间,一定有人要牺牲他的脑袋了!当然,我自己也不敢确信这个挨刀的人,决不是我,也许竟然是我!谁敢保得?何况当我在簇拥太后出宫上轿之前,我还很得意地在伊面前夸赞过那火车上的布置怎样周到,一切陈设,安排得怎样妥贴,哪知隔不到两个时辰,便得到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反证。读者试想:太后对于我,还能有什么好感吗?
但是,我虽然一个人在暗暗的担忧,其余的那些女官,宫女,太监,却一些没有什么感想;他们只知道眼前起一件小小的变故,便是太后所心爱的那些古玩玉器,已翻下来了,他们便象寻常的人遇见了这类事情一样,来不及的纷纷抢上前来,把已经掉下去的,赶快用手扶住,差不多每个人已使出了他的全部的力量,可是这样一闹,便把一座列车上的小朝廷闹得秩序大乱,不成体统了。在宫中,或在颐和园里,可说是几百年来,从不曾有过这样大大失态的情形的!我想要如给先前拼命上奏章,反对太后冒险乘坐火车往奉天去的那些朝臣们见到了这种情形,他们一定会摇着头,顿足长叹着:“我们可谏劝得是吗?现在你看:这不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吗?”
我因为一来已经承认这件事情已是闹得不可收拾了,二来也许可以说我简直是吓昏了,所以我只是袖手旁观地候着,希望太后自己或者会想出什么好的方法来,补救这个缺陷;但是伊也不作一声。我忍不住旋过头去看了伊一眼,——心里是怀着十二分的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