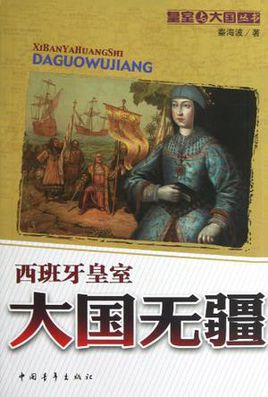行者无疆-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万万个文盲。怎能设想,这个不肯签名的人不仅亲笔一字一句地写出了三十几部堪称世界经典的辉煌巨著,而且奇妙地动用了二万多个英语单词,是历史上词汇最为丰富的作家之一!这些问题,终于使人怀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亚,难道真是从这个小镇走出的那个人?这样的怀疑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集中发表,文化界就像发生了一次地震。怀疑论者并不怀疑从这个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的存在,他们只怀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学者身份和上层身份的人,借用这个人的名字作为自己发表剧本的笔名。
这么说来,这个躲在笔名背后的作者,才是真正的文化伟人。既然是文化伟人总会有多方面的光亮泄漏,他也应该是那个时候伦敦的重要人物。那么,他究竟是谁?
怀疑论者们按照他们的文化逻辑,分别“考定”了好几个人。
有人说是那位十二岁就进了剑桥大学读书,后来成了大哲学家的培根;有人说是“牛津伯爵”维尔:有人说是另一位剧作家马洛,他与莎士比亚同龄,但他获得过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有人更大胆地断言,真正的作者是伊丽莎白女王,因为只有她才能体验那些宫廷悲剧的深刻心境,而且有那么丰厚的学识和词汇;顺着这条思路,有人认为,女王周围的一些著名贵族,可能都参与过这些剧本的创作。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怀疑论者选定的对象不同,但隐藏在背后的理由却惊人地统一,那就是,大文豪只能来自于大学,若说有例外,除非是女王和贵族。
他们的考证文章很长,也有大量注释和引证,完全符合大学的学术规格。只可惜,一年年过去,被他们吸引的人很多,被他们说服的人很少。莎士比亚的戏一直到处上演,没有哪个观众会认为,今天晚上买票去欣赏哲学家培根爵士或伊丽莎白女王的才华。
在他们拟定的名单中,真正懂创作的只有一个马洛,因为他本人确实也是杰出的剧作家,尽管怀疑论者看中的是他的剑桥学历。结果,时间一长,稍稍懂点事理的怀疑论者便放弃了别人,只抓住他不放。恰恰马洛这个人有可能参加过当时英国政府的情报工作,二十九岁时又在伦敦附近的一家酒店被人刺杀,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一个叫卡尔文·霍夫曼的美国人提出一个构想:可能那天被刺杀的不是马洛,情报机构玩了一个“掉包计”,真的马洛已经逃到欧洲大陆,隐姓埋名,写了剧本便用“莎士比亚”的笔名寄回英国,因此莎士比亚剧本的发表也正巧在马洛被刺之后不久。
这个构想作为一部小说的梗概听起来不错,却带有明显的好莱坞性质,即只求奇险过渡,不问所留漏洞。例如:马洛要隐姓埋名,为什么不随便起一个笔名,偏偏要找一个真实存在的同行的名字?如果真实的莎士比亚不会写这样的剧本,他剧团里的大批同事怎么会看不出破绽,然后传扬出去,造成马洛的不安全?还有,延续二十几年的伟大创作工程,到完成之时,世事人情早已大变,伊丽莎白女王也早已去世,马洛隐姓埋名的理由至少已应松弛,他和其他知情人又不会不知道这项工程的重量,为什么没有点滴的真相透露,或留下片言只语告知后世呢?
其实,按照学术的逻辑,有两个事实足以驳倒那些怀疑论者:一是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在剧团里为演出赶写的,后来收集起来的是同一剧团里的两位演员,莎士比亚本人也在剧团之中,整个创作行为处于一种“群体互动的透明状态”,不存在书斋学者个体写作时作假的便利;二是莎士比亚的同代同行、剧作家本·琼森为那两位演员收集的莎士比亚全集写了献诗。
那么,既然从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没有冒名,为什么会出现本文前面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与那个时代英国强大的贵族统治所造成的普遍社会心态有关。王室和贵族可以欣赏戏剧,却不可能尊重剧团中人,他们不能设想,这些“戏子”不仅能够搬演、而且还能完整地创作出这样的艺术精品。
莎士比亚当然明白环境的不公,偶有吐露,又遭嘲谑,于是他也就无话可说。今天的读者早已熟知莎士比亚的内心世界,因此也充分理解他在那个环境里无话可说的原因,也能猜测他为什么正当盛年就回到了小镇。
可以想像,莎士比亚回到小镇的心态非常奇特。自己在伦敦的种种怨屈,都与出生于这么一个小镇有关,似乎只有小镇最能体谅自己,但是,当自己真的决定在这里度过余生时,突然发现竟然比在伦敦更要无话可说。一颗已经翱翔过精神天宇的心灵很难找到交流对象,包括在自己家乡。于是他也就不为难家乡了,只让乡民知道最通俗意义上的他,不忍心把自己略为艰深的部分让他们慌张。他已经非常乡镇化却又与乡民十分隔膜,这是必然的,因为乡民最拥戴的一定是水平基本与他们相齐又稍稍高于他们的人,莎士比亚没有本事把自己打扮成这样,因此也就很快被他们淡忘。
一个伟人的寂寞,没有比这更必然、更彻底了。
于是,今天一切热爱莎士比亚的人都不难理解,他在这样一个小镇里面对着几双木然的眼睛口述临终遗嘱,不会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的著作。
我想,一个作家临终时,他的著作大致会出现三个等级的状态:第一等级是著作早已深入人心,无须言说,人们只是念诵他的名字;中间等级是著作进入悼词,进入挽联,让大家重新记起,一片唏嘘;最后等级是著作进入遗嘱,让子女们与财物一起承接。
当然这几个等级也会互相交错。
莎士比亚连第一等级也超越了。他知道戏剧演出是过程艺术,没有奢望哪一部能深入人心,只把它们看作过眼烟云。对于那些剧本,他像一切只从演出来看待戏剧生命的戏剧实践家一样,虽然内心珍爱,却未曾想像它们的历史命运,演过了也就过去了。何况在当时,社会对于演出背后的剧本,尚未建立著作权意识。
因此,我们便进一步理解,要他在记录的遗嘱前签名,他却轻轻摇头。Shakespeare,他知道这些字母连贯在一起的意思,因此不愿最后一次,亲笔写在这页没有表述自己灵魂的纸张上。
这个样子,确实很像个文盲。
同一个小镇,同样的文盲,他又回到了出生的状态。
他觉得这个结尾很有戏剧性,可以谢幕了。
但是在我的想像中,他还是会再一次睁开眼睛,问身边的亲属,今天是几号。
回答是:四月二十三日。
他笑了,随即闭上了眼睛,永远不再睁开。
这个结尾比刚刚想的还要精彩。因为这正是他的生日。他在四月二十三日来到这个世界,又在四月二十三日离开,一天不差。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日子。
也许,这是上帝给一位戏剧家的特殊恩惠,上帝也学会了编剧。
3还需要说一说怀疑论者。
我走在斯特拉福小镇的街道上想,怎么能责怪这个小镇在莎士比亚临终前表现出来的漠然呢?它后来终究以数百年的热闹、忙碌和接待,否定了一切怀疑论者。
怀疑永远是允许的,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反怀疑”。我们已经看到了怀疑论者内心的轨迹,因此也不妨对他们怀疑一番。
时至今日,他们那种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地把女王、爵士、贵族硬说成是莎士比亚剧本真正创作者的可笑心态就不必再作剖析了,我剩下的最大怀疑是:他们有没有研究和谈论莎士比亚的资格?
资格,这是他们审核莎士比亚的基本工具。我们现在反过来用同一个词汇审核他们,里边包含的内容却完全不同。不讲身份,不讲地位,不讲学历,只讲一个最起码的资格:公开发表文章谈论莎士比亚,至少要稍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认为没有进过牛津、剑桥大学的门就不可能成为莎士比亚,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当他们永远只着眼于莎士比亚在知识领域的涉猎,完全无视他在美的领域的构建,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当他们不知道种种所谓“学问”的东西多数正常人只要花足够时间都能追补,唯一无法追补的是创造性灵感,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当他们想像不到一个处于创造过程中的天才人物有无限的生命潜力,一个敏于感受的智者可以从自己有限的生活经历中领悟辽阔的时空,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不懂艺术创作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世界上有很多别的事情可做,然而他们偏偏要来研究莎士比亚,而且对他的存在状态进行根本否定,那就不能不让人质疑他们的资格了。
然而他们名义上又有一种资格,譬如,大学教师,那就容易混淆视听了。
大学是一种很奇特的社会构建,就其主干而言,无疑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用巨大,但也有一些令人厌烦的侧面。例如在贵族统治构架的边上,它衍生出另一种社会等级,使很多创造能力薄弱的人有可能在里边借半官方、半学术之名,凭群体之力,沾名师之光,获得一种社会认定。其中,越是勉强获得这种认定的人总是越要摆出一副学者架势,指手画脚,最后甚至自以为也懂得艺术创作,着手否认莎士比亚。这一来,连原先热爱莎士比亚的人也开始混乱,因为莎士比亚背后没有任何东西支撑,而这些人背后却是一所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这些人从那个虚幻的大学背景里拉开,然后单个审核他们的资格,盯着他们追问一声:“你是谁?”
否则,莎士比亚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莎士比亚来路明确,他们来路不清;莎士比亚有作品也就是有可以攻击的目标,他们没有作品也就是没有可以攻击的目标;莎士比亚在尽力感动民众,他们在大声左右舆论——总之,这是一场失衡的对峙,蒙面的偷袭。
追问之后我们就能宣布:不要再在莎士比亚的著作归属问题上分成相信派和怀疑派了,怀疑派不成其派,因为他们完全不懂艺术创作,因此不具备公开谈论莎士比亚的资格。
这种反问批评者资格的思路,使我豁然开朗。因为直到今天,单方面蒙面偷袭的闹剧还处处发生。前两天听一位欧洲经济学家告诉我,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即将规定,公共媒体上的“股评家”,必须公布自己的财产和持股状况。我虽然至今与股票无缘,却立即领会了此举的别无选择。因为据我亲身经历,至少已见到两拨真正的罪犯遮住了自己的面目在传媒上义正辞严地揭发和声讨受害者。看来古今同一,只有昭示批评者的真实面貌,结束“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状态,才能使批评开始变得稍有意义。
其实,即使闻到的声音,也有隐显两层。外显层次的声音往往非常学术,格外正义,而内隐层次,则沙哑焦躁,很不好听。有时一不小心,内隐层次会突显其外,让人吃惊。
对于这一切,即便在生前,莎士比亚也都领略到了。
例如,一五九二年吧,莎士比亚二十八岁,伦敦戏剧界有一篇文章流传,其中有一段话,针对性十分明确,而声调却有点刺耳:……有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点自己,用一张演员的皮,包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写了几句虚夸的无韵诗就自以为能同你们中最优秀的作家媲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却恬不知耻地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