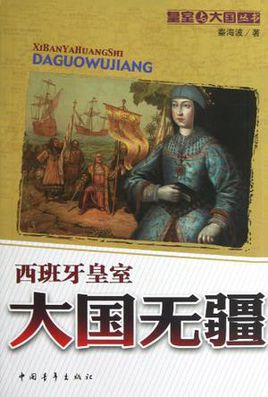行者无疆-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薄薄的爱因斯坦著作,谁知一翻就见到一帧惊人的黑白照片。须发皆白,满脸皱纹,穿着一件厚毛线衣,两手紧紧地扣在一起,两眼却定定地注视着前方。侧逆光强化了他皱纹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来了。当时我们的眼睛看惯了溜光水滑、大红大绿的图像,一见这帧照片很不习惯,甚至觉得丑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过去了还想翻回来,一看再看。他苍老的眼神充满了平静、天真和慈悲,正好与我们经常在书刊照片里看到的那种亢奋激昂状态相反。我渐渐觉得这是一种丑中之美,但几分钟之后又立即否定:何丑之有?这是一种特殊的美!——我一生无数次地转换过自己的审美感觉,但在几分钟之内如雷轰电击般地把丑转为美,却仅此一次。我立即买下了这本书,努力啃读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那时正好又热衷英文,也就顺便把扉页中的英文标题记住了。书中没有注明拍那张照片的摄影师名字,这便成了我的人生悬案,后来当然知道了,原来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人像摄影大师卡希(Karsh),我现在连卡希的摄影集都收集齐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于一张照片中的眼神,这很奇怪,在我却是事实。我仍然搞不清相对论,只对爱因斯坦的生平切切关心起来。因此站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依稀说出,爱因斯坦住在这里时应该还是一名专利局的技术员,结婚才一二年吧,刚做父亲。
管理故居的老妇见我们这群中国人指指点点,也就递过来一份英文资料,可惜她本人不大会说英文。接过资料一看,才明白爱因斯坦在这里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〇五年惊天动地: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说,从而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四月,完成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五月,完成了对布朗运动理论的研究;六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九月,提出质能相当关系理论;……
这一年,这间房子里的时间价值需要用分分秒秒来计算,而每个价值都指向着世界一流、历史一流。
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去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世纪人物,结果整个二十世纪,那么多国家和行当,那么多英雄和大师,只留下一位,即爱因斯坦。记得我当时正考察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抵达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麓加德满都的街市间全是爱因斯坦的照片,连世界屋脊的雪峰绝壁都在为他壮威。
二十世纪大事连连,胜迹处处,而它的最高光辉却闪耀在刚刚开始了五年的一九〇五年,它的最大胜迹却躲缩在这座城市这条大街的这个房间,真是不可思议。难道,那么多战旗猎猎的高地、雄辩滔滔的厅堂、金光熠熠的权位都被比下去了?
很想在这里寻找一点历史逻辑,但想来想去都十分困难。
连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到伯尔尼,为什么会住在这间房,后来为什么离开,也只有一些偶然原因,没有必然逻辑。
正想着,抬头看到墙上还有他的一句话,勉强翻译应该是:一切发现都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尽管那些结果看起来很接近逻辑规律。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否定逻辑思维是为了肯定什么,于是心中窃喜。
这便是我知道的那位爱因斯坦,虽然身为物理学家,却经常为人文科学张目。近年来爱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出版,里边有大量人文科学方面的篇章,尤其是他对宗教、伦理、和平、人权、生活目标、个人良心、道义责任和人类未来的论述,我读得津津有味,有不少句子甚至刻骨铭心。前年黑龙江有一位读者在报纸上发表一封公开信,问我在被文化盗窃集团组织的威胁、诬陷、围攻浊浪中如何自处,我回信说:“读爱因斯坦。”
在故居里转了两圈,没找到卫生间,开始为爱因斯坦着急起来。怕他也像当初我们住房困难时那样,与别人合用卫生间。这种每天无数次的等待、谦让、道谢、规避,发生在他身上是多么不应该。但一问之下,果然不出所料,顺楼梯往下走,转弯处一个小门,便是爱因斯坦家与另外一家合用的卫生间。
正在这时,钟楼的钟声响了。这是爱因斯坦无数次听到过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分。他在这钟声中怔怔地思考着宇宙的时间,于是,这间小房也就成了无限的空间。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搬过好几次家,由于这间小房是相对论的诞生地,因此最为重要。但瑞士不喜欢张扬,你看这儿,只让一位老妇人管着,有人敲门时她就去开一下,动作很轻,怕吵了邻居。楼下那个嘈杂的小餐厅,也没有让它搬走,那就只能让它的名字在玻璃门上与爱因斯坦并立,很多旅人看到后猜测疑惑,以为那家餐厅的名字就叫“爱因斯坦故居”,也算得上一种巧思,终于没有推门面人。
伯尔尼以如此平淡的方式摆出了一种派头,意思是,再伟大的人物在这里也只是一个普通市民。我觉得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有点过头,爱因斯坦的这处故居还应该再好好打理一下;但比之于我们常见的那种不分等级便大肆张扬的各色名人故居,这里的淡然方式更让人舒服。其实也正因为这样淡然,才会吸引真正的大师巨匠来安静居住。
另一种贫富
世人皆知瑞士,但如果追问瑞士的首都在哪里,多数答不出来。
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作为首都的伯尔尼居然没有机场。
在现代社会,没有机场等于阻拦很多政要和传媒的轻松进入,等于拒绝大量活动在这里举办,因此,各国民众很少有机会听到它。人们更多地知道日内瓦和苏黎世,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旅客乘飞机到这两个城市≮我们备用网址:≯,下机后立即转乘汽车,长途跋涉去找首都。
这连想一想都烦不胜烦。
瑞士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又是国际金融中心,首都没个机场实在有点荒诞。问原因,瑞士朋友不好意思地耸耸肩,说这是伯尔尼公民投票的结果,他们怕飞机降落声太吵。
“还有更奇怪的呢,”这位瑞士朋友说:“联合国欧洲总部在日内瓦,日内瓦在瑞士,但瑞士恰恰不参加联合国,也是公民投票的结果。”
不想缴联合国的会费倒也罢了,我听这儿的几位中国学者说,最不可理喻的是一些早已经过充分论证的大型交通项目,多年的基础工程完成了,大笔经费也用了,一投票却被否定,投票者多数是不出门的农民,否定的理由既琐碎又具体,但只有这样的理由才能左右他们。
我觉得老是拿着这样的事情进行公民投票,看似民主,恰恰违背了支撑民主精神的理性原则。在一个个人声鼎沸的投票之夜,当那些显而易见的自私考虑一次次压倒了那些着眼于整体尊严的决策,瑞士也就暴露了自己在精神文化上的贫乏。
它确实很富,富在近一百多年,主要出于一种生存策略。由此,出现了它的文化积淀和经济地位之间的严重反差。它在现代城市生态外壳中,依然澎湃着村社式的原始民主情绪,结果只能不断地让人瞠目结舌。
它让我联想到一些快速富裕起来的农民企业家,有充分的生存智谋,却缺少足够的文化道义。后来逐渐听说,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中立却与纳粹德国有隐蔽的经济往来,而近年来又位居发达国家对贫困、受灾国家外援比例的末位,我也就不奇怪了。它缺少另一种更重要的富裕,因此虽然频频得利,却又频频露怯。
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经自我觉察,昨天晚上还特意写了一段话相送:骄人的富裕培养了你的自负,百年的成功鼓励了你的保守,长久的安宁增加了你的琐碎,太多的福利吞食了你的追求,缺少文化积淀和精神主轴,你的美丽中埋藏着太多的隐忧。
但这段话只是发送到香港凤凰卫视播出,华人观众听听罢了。那么,这段话中的“你”就应该改成“它”。只是这样一改,也就变成了躲在人家背后的说三道四,不大光彩。
每个国家各有自己的命运。与瑞士相比,很多国家在近百年间连遭厄运,例如,或蒙战火荼毒,或受恶魔统治,或被贫困控制,但是灾难也会养育另一种成果,何况有些国家还有辉煌的精神文化遗产。瑞士常常从反面证明那些国家毕竟根基深厚,就像一个暴发户常常在某些生活细节上反衬出别人并不寒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立的意义已不存在,幸好有冷战使它勉强延伸;现在冷战也已过去,中立完全失去了身份。那么瑞士,在往后的日子里,你将会有什么动静?
我只想提醒,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中立不得的。人类在抖落各种历史对抗之后必将重新面对最本质的矛盾,即文明与野蛮、善良和邪恶、和平和恐怖、正常与极端的矛盾,在这些矛盾前面,最需要的,恰恰是你比较缺少的文化道义。这儿容不得生存计谋,这儿来不得暗通关节,这儿不存在中立空间。
希隆的囚徒
1瑞士小,无所谓长途。从伯尔尼到洛桑,本来就不远,加上风景那么好,更觉其近。
然而,就在算来快到的时候,却浩浩然荡荡然,弥漫出一个大湖。这便是日内瓦湖,又叫莱芒湖,也译作雷梦湖。我们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这些不同的名字,其实是同一个湖。瑞士有好几个语言族群,使不少相同的东西戴有不同的名目,谁也不愿改口,给外来人造成不少麻烦。但日内瓦湖的不同叫法可以原谅,它是边境湖,一小半伸到法国去了,而且又是山围雪映、波谲云诡,丰富得让人们不好意思用一个称呼把它叫尽。
前几天拜识的苏黎世湖美则美矣,还不至于让人一见之下便起赖着不走的念头,而日内瓦湖便粘人多了。只可惜日程不许,我们在心中一会儿诅咒一会儿祈祷,希望出现奇迹般的理由留下几天。越往前走景象越美,而大美本身就是停步的理由,但大家面面相觑,似乎还缺少最后拍板的那一槌。
终于,槌子响了,我和伙伴们看到了湖边的一座古堡。在欧洲,古堡比比皆是,但一见这座,谁也挪不动步了,于是哐当一声,槌下如锤。
为使逗留的时间长一点,先得找旅馆住下。古堡前有个小镇叫蒙特尔,镇边山坡上有很多散落的小旅馆,都很老旧,我们找了一家最老的人住,满心都是富足。富足感大多因“横财”而起,而所谓“横财”也就是计划外所得,我们在计划外揪住了一两天,可以毫无工作压力地亲近古堡和大湖,得意得不知该把脚步放重还是放轻。
这家旅馆在山坡上,开车上去已十分吃力,下车后便见一扇老式玻璃木门,用力推开,冲眼就是高高的石梯。扛着行李箱一步步挪上去,终于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柜台。办理登记的女士一见我们扛了那么多行李有点慌张,忙说有搬运工,便当着楼梯仰头呼喊一个名字,没有答应,又一迭连声地抱歉着为我们办登记手续,发放钥匙。
我分到三楼的一间,扛起行李走到楼梯口,发现从这里往上的楼梯全是木质的,狭窄、跨度高,用脚一踩咯吱咯吱地响。我咬了咬牙往上爬,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楼面,抬头一看标的是“一楼”,那么,还要爬上去两层。斜眼看到边上有一个公共起坐间,不大,却有钢琴、烛台、丝绒沙发、刺绣靠垫,很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