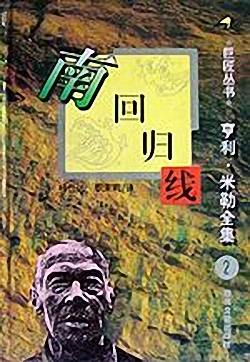南回归线-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吹幕熬拖袢垩遥娜馓逄袄返匾プ∈裁矗镜郊峁獭⑹翟诘亩魃先ィ员阒匦伦楹希⑿菹⑵獭U饩拖癯链戏⒖袼频胤⒊龅脑毒嗬胄藕牛桓銮缶刃藕拧F鸪跷医蠼馕で椋蠼馕馔蚰Σ敛目裣病N乙晕曳⑾至艘蛔罨鹕剑蛔缘奈胀N揖挥邢氲剑惶跞死嘀诰暮Q螅谘麴舻穆砦苍搴3撩弧O衷谖蚁氲侥强磐腹ヅ窨吡⒆盼⒐獾暮谛切牵强判以谖颐欠渴露肥疑戏降墓潭ㄐ切牵染缘纳系鄹潭ǎT叮抑勒饩褪撬嬲陨淼囊磺幸鸦谟校阂桓雒挥型夤鄣乃劳龅暮谔簟N抑溃颐蔷拖窳礁鍪酝几糇盘裾ぷ霭姆枳樱诟鞍闭飧龆时湮弧N宜倒诤诎抵新易ヂ依匆黄氖焙颍彝撬拿郑哪Q撬U馐钦娴摹N以诤诎抵幸蚯笾倍О堋N一肴夤欤胛薇叩男钥占洌肽掣鋈私⒌牟ǖ溃豪纾辉谝黄鸫袅硕潭桃桓鱿挛绲那侵窝拍取<版蛔犹ǘ辍⒘咚甑呐⒆涌逅⒗取⑽谀取⒛取⒙旮翊铮魑铩⒐砘稹⒘场⑸硖濉⒋笸取⒉辽矶牡靥⒁怀∶巍⒁桓龌匾洹⒁恢中脑浮⒁恢挚释N铱梢韵却右桓鲂瞧谌障挛缭谔辣叩那侵窝拍冉财穑谴愕愕娜鹗苛氯梗“诘钠ü桑哪戏角坏鳎翘舳盒缘淖彀停乃中兀晃铱梢韵却忧侵窝拍瓤迹奘蛄吮昙堑男灾蛱ǎο蛲庀蛏希ü吡鄱斐傻慕峁氲降趎维的性空间,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乔治雅娜就像被称之为性的未完成怪兽小耳朵的耳膜。她透明、活跃,按照关于大道上一个简短下午的记忆,她吸吸着做爱世界最初的确切气味和物质,这个世界实质上是一种无限的、不可界定的存在,就像我们人类世界一样。整个做爱世界跟我们称之为性的动物越来越增大的耳膜一样,像另一种存在长入我们自己的存在,并渐渐取而代之,以致人类世界最终仅仅成为对这种正在自己产生,又包罗万像、生育一切的新存在的模糊记忆。
正是在黑暗中的这种蛇一般的交媾,这种双重关节、双管齐下的勾搭,使我穿上了怀疑、妒忌、恐惧、孤寂的拘束衣。如果我从乔治雅娜和无数打了标记的性烛台开始一点儿一点儿进行描述的话,那我确信,她也在努力,正在建造耳膜,制造耳朵、眼睛、脚趾、头皮以及诸如此类的性东西。她会从强奸她的怪兽开始,假定故事里有实情;总之,她也在平行轨道上的某个地方开始,努力向上向外完成这种多重形式的不存在的存在,我们俩正拼命努力争取通过其主体相见。尽管只了解她的一点点生活,只拥有一袋谎言、一袋发明、一袋想象、一袋迷惑与欺骗,只是把支离破碎的东西、可卡因造成的幻觉、沉思、未完成的句子、混乱的梦话、歇斯底里的疯话、拙劣装扮成的幻象、病态的愿望拼凑在一起,不时遇到一个与肉体相应的名字,偷听到零零星星的谈话,观察到偷偷摸摸的眼光,半抑制状况的姿势,但我完全能够认为她拥有一个她自己的做爱之神的神殿,一个实在太生动活泼的血肉创造物的神殿,这些创造物便是那个下午的男人们。也许只是在一个小时以前,她的窟窿眼儿也许还堵塞着刚操完后留下的精子。她越是柔顺,越是表现得热情洋溢,越是显得没有约束,我就越变得反复无常。没有开始,没有个人的、个别的出发点;我们就像有经验的剑客在决斗场上相见,这决斗场现在挤满了胜利与失败的幽灵。我们对哪怕轻轻一击都很警惕,都很负责,这只有那些击剑能手可以做到。
我们在黑暗的掩护下与我们的军队会合。我们两面夹攻,强行将城堡大门打开。我们的血腥行为没有受到任何抵抗;我们不要求生命保障,我们也不宽耍我们在血泊中游着泳会合到一块儿,同所有那些已经熄灭了的星星的一种血淋淋的浅灰蓝重逢,除了那颗像头皮一样悬挂在顶篷窟窿之上的那颗固定黑星星。如果她真正受了麻醉品的刺激,她会像吐神谕一般将它吐出来,一切,今天,昨天,前天,前年,直至她出生那天发生的一切。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细节是真的。她一刻也没有停下,因为如果她停下来,她在飞行中造成的真空就会引起爆炸,会把世界炸得粉碎。她是世界在小宇宙中的说谎机器,用来对付同样无穷无尽的巨大恐惧,这种恐惧能使人们把他们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死亡器械的创造上。看着她,人们会认为她是无畏的,会认为她是勇气的化身,不过她确实如此,只要她不必重蹈她自己的足迹。在她身后是一片宁静的现实,一个处处跟踪她的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一天天越变越大,一天天越变越可怕,越变越使人目瞪口呆。每天她都必须长出飞得更快的翅膀,更锐利的牙齿,更敏锐更有催眠作用的眼睛。这是朝世界最边缘处奔跑的赛跑,一种从一开始就失败的赛跑,没有人来阻止它。在这真空的边缘,站立着真,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复被窃取的地盘。它如此简单明了,竟使她发了狂。调遣上千种个性,强占最大的枪炮,欺骗最伟大的心灵,作最长的迂回——最终仍然是失败。在最后的会合中,一切注定要崩溃——狡猾、技巧、强力、一切。她将成为汪洋大海岸上的一粒沙子,格外糟糕的是,她跟大洋岸上的每一粒沙子一模一样。
她将不得不承认到处都有她独一无二的自我,直至时间的终结。
她为自己选择了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啊!她的独一无二被吞没在普遍之中!她的强力被降至最为消极的消极状态!这是令人发疯、令人产生幻觉的。它不可能存在!它绝不能存在!前进!像黑色军团。前进!穿越各种程度的空前广阔的圈。前进,离开自我,直至灵魂的最后一粒物质被伸展到无限。在她惊慌失措的飞行中,她似乎在子宫里怀有整个世界。我们正被驱逐出宇宙的范围,被驱向一片没有一种工具可以使其显形的星云。我们被驱赶着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如此安静,如此长久,以致相比之下,死亡似乎成了一个疯女巫的狂欢。
早晨,注视着她死火山口似的苍白面孔。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没有一点儿瑕疵。造物主怀里天使的模样。谁杀死了科克·罗宾?谁对易洛魁人进行了大屠杀?不是我,我可爱的天使会说,老天作证。注视着那张纯洁无瑕的面孔,谁又能拒绝相信她呢?谁能在那天真无邪的睡眠中看到,那张面孔的一半属于上帝,另一半属于魔鬼?那面具摸上去像死一样光滑、冰凉、可爱,它是蜡制的,像迎着一丝微风开放的花瓣。它如此诱人地平静、坦诚,人们会在其中淹死,会全身心地深入其中,就像一个潜水员,再也不回来。直至眼睛朝世界睁开,她会就那样躺着,彻底熄灭,只发出反照的微光,就像月亮那样。在她天真无邪的死一般昏睡状态中,她更加迷人;她的罪恶溶解,从毛孔渗出,她蜷缩着躺在那里,像一条钉牢在地上的睡眠中的大蛇。机体强壮、柔软,肌肉发达,像是具有非同寻常的重量;她有大于人类的重量,人们几乎可以说,是一具有热气的尸体的重量。人们可以想象,她就像美丽的奈费尔提蒂在变成木乃伊的最初一千年之后的模样,一种完美丧葬的奇迹,一场保存肉体免于衰朽的梦幻。她蜷缩着躺在中空的金字塔基座上,裹在她自己创造的真空中,像过去的神圣遗迹。甚至她的呼吸也似乎停止了,她睡得那么死。她掉到了人类水平之下、动物水平之下,甚至植物水平之下:她已经下降到矿物世界的水平,在那里,有生气只比死亡高一个档次。她已经将欺骗的艺术掌握得如此之好,即使梦幻也无力泄漏她心的真情。她已经学会如何不做梦:当她在睡眠中蜷缩起来的时候,她自动切断电流。如果人们能这样抓住她,打开她的脑壳,人们会发现它完全是空的。她不保留任何令人烦恼的秘密;可以按人的方式杀死的一切都被消灭。她可以无穷无尽地生活下去,像月亮,像任何死亡的行星,发出催眠的光辉,创造激情之潮,将世界吞没在疯狂之中,以其磁性的金属之光使地球上的一切物质改变颜色。她在使周围每一个人狂热到极点的同时也播下了她自己死亡的种子。在她睡眠的可怕寂静中,她通过同无生命的行星世界冷却岩浆的结合,重新开始她磁性的死亡。她魔术般地保持原样。她的凝视具有穿透性地固定在一个人身上:这是月亮的凝视,通过这凝视,死亡的生命之龙喷发出冷火。一只眼睛是暖和的褐色,一片秋叶的颜色;另一只眼睛是淡褐色的,这是一只使指南针摇曳不定的磁性眼睛。就是在睡眠中,这只眼睛也还在眼皮底下摇曳不定,这是她身上唯一明显的生命标志。
她一睁开眼睛,就全醒了。她猛地一下惊醒过来,好像看到世界及其人类道具会大为震惊。她立即充分活动起来,像一条大蟒似地爬来爬去。使她恼火的是光!她一边醒来,一边诅咒太阳,诅咒现实中眩目的强光。房间必须是黑洞洞的,点燃蜡烛,紧闭窗户,防止街上的嘈杂声渗透到房间里来。她裸露着四处转悠,嘴角叼着一支香烟。她的梳妆打扮是她十分偏爱的事情;就是穿一件浴衣,她也要在此之前留意去照料上千个琐碎的细节。她就像一个田径运动员,准备参加当天了不起的比赛项目。从她专心致志研究的头发根,到她的脚趾甲的形状和长度,她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她坐下来吃早饭以前被彻底检查过。尽管我说她像田径运动员,但是在脸上,她更像一个机械师为一次试飞而彻底检修一架高速飞机。一旦她穿上连衣裙,她就开始工作,开始飞行,这飞行也许最终会在伊尔库茨克或德黑兰告终。她在早餐时将装下足够的燃料,来维持整个旅行。早餐是一件漫长的事情:这是她闲混闲荡一天中的唯一仪式。它确实长得令人恼怒。人们很想知道,她是否还起飞;人们很想知道,她是否忘记了她发誓要每天完成的伟大使命。也许她正梦见她的旅程,或者,也许她根本没有做梦,而只是规定时间来进行她神奇机器的工作过程,以便一旦干起来,便不回头。她在当天的这个时刻非常沉着镇静,她就像空中的大鸟,栖息在山崖上,神情恍惚地俯瞰底下的地面。她不是从餐桌上猛扑到她的食物上。不,是从凌晨的高山之巅,她威严地慢慢起飞,使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同马达有节奏的震动相一致。她面前有着所有空间,她反复无常地确定方向。要不是因为她的身体有着土星般的重量,她的翅膀有着异常的长度,她几乎可以说是自由的形象。无论她姿势如何,人们都会感觉到驱使她每天飞行的恐怖。她既顺从命运,又发狂地想要征服命运。她从高山之巅起飞,高高翱翔,如同在喜玛拉雅山的某个山峰之上盘旋;她似乎总是想飞到某个未知的地区,如果一切顺利,她会永远消失在这个地区里。每天早晨,她似乎都带着这绝望的、最后一分钟的希望翱翔;她镇静、庄严地告别,就像一个准备进入坟墓的人。她从来不在飞行区域周围转圈;从来不回头看一眼那些她正抛弃的人。她不留下最少一点儿个性;她将她的所有全部带到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