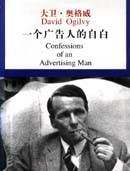三个人的天堂-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哥曾这样对贝贝解释“天堂”:“我们家就是天堂,天堂就是我们家”。他脱口而出地解释“天堂”时,其实是在解释他心中的“家”。我们从此知道,他是多么享受我们的家。
老哥曾对我说:“你如果回家,我就兴高采烈地要回家和你玩,你如果不回家,我想着贝贝不好玩,就要回家和贝贝玩。”所以,老哥几乎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
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谁都知道,干律师这个行当的,晚上的应酬一定会多。要争取案源,要应酬客户、要分析案情等等。但老哥这个律师不会,他很少晚上在外面吃饭。
老哥的沟通方式一直比较特别,要么去他办公室谈、要么一起喝杯咖啡。实在不行,一起吃个工作午餐。他说:“做律师要靠专业上的实力”。久而久之,他的客户们都知道了他的风格,慢慢地受他的影响,并且开始欣赏他的方式,戏称:“此人不吃饭。”
虽然没有“请客吃饭”,但老哥和他的客户们却成了很好的朋友。
老哥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被‘请客吃饭’所累,请和被请的人都恨不得所有的酒楼都关门大吉。”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深圳流传着“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论调,但是,当人们走过躁动的时代,吃过浮华的盛宴以后,家常菜变成渴望,家庭的温暖变成向往,深圳人,开始成熟、安静了。“革命”又回归本质,不再是“请客吃饭”了,商务合作中,“专业性”、“服务质素”成为达成合作的决定性因素。
老哥常说,家里最自在、最舒服,最轻松。他在家看着书、读着报、研究着新淘来的碟、上网浏览着新闻逛着论坛、听着经典音乐,都感觉无比地享受。他的快乐也常常感染着我们,我们的家就充满欢乐的气氛。
我有时晚上才去报社编版,他白天没啥要紧事时,也常和我在家“鬼混”。为了我的午餐问题,他经常找各种理由不去律师所上班,然后得以和我共进午餐。有时我们把剩饭煮成菜泡饭,或做成蛋炒饭,有时下点面条或吃面疙瘩,有时去山姆买来牛扒,煎好在自家阳台上吃,还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找点浪漫。
老哥只要在家,他情不自禁地哼着的歌,就是王菲的——“一切都好,只缺烦恼”。我有时会想,老哥爱家,莫非是天生的?
老哥在家是个大忙人
在工作上,从不见老哥有多忙,但在家,他却是个大忙人,老哥在家几乎一刻也不会闲着。他忙起那些家常琐事来,我们家就成了创意产业园,连最平常的小事,似乎都得有相当的智慧含量才搞得掂。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把家务事做得如此得意,又如此富有创新精神。有些小事情,被他做起来,简直严谨得一塌糊涂,不亚于科学实验,多一点少一点,问题大了去了。
老哥在家偶尔会做饭,总像是美味实验室要推出重大发明。他用一个个被我们扫光的盘子,来宣布发明的市场价值。
老哥抹起地板来,要么笑称自己是“灰姑娘”和贝贝套交情,要么给自己颁发最具专业特质的清洁工奖,要求我奖赏个吻之类的“以资鼓励”,然后边哼着歌,边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抹地杰作,俨然一位雕塑家在炫耀自己的伟大作品。
给几个阳台的花花草草浇水、剪枝时,老哥总会声称自己这辈子最想干的活,就是当园艺工程师。
我有时在家,半天也想不起要干啥,但老哥永远都能找到事做。他把贝贝的画装裱装裱挂在墙上;把书柜整理整理,找出最近想再看的书;将家里的花移个位,找点不同的感觉;实在不行,他把抽油烟机清洗一遍,以此来换我骗他一句:“啊?咱家换了新的抽油烟机?”
奇怪的是,对于那些家常琐事,老哥做起来总是甘之如饴,自得其乐,还总有研究报告发布,就连洗碗、装饭等事情,他都能讲出一套套的技巧。
我常边洗碗,边听他隆重地介绍着洗碗操作规程,然后取笑他:“老哥,你为什么不写一篇有关洗碗的论文呢?”或者调侃他:“老哥,你如果写一本《家庭琐事技巧大全》,绝对畅销。”
老哥总能把那些无聊的琐事,说得无比生动。我们俩经常边洗碗,边在厨房里大笑,惹得贝贝循笑声而来,一定要加入我们有趣的洗碗游戏中来。他完成类似洗碗这样芝麻大的小事,跟推动他所负责的公司开展资产重组的态度一样,有条不紊、层层推进,最后终成正果。
()好看的txt电子书
家里事无巨细,老哥都喜欢上心。如果在律师所上班,他突然发现下雨了,必定一个电话打回家里,提醒关窗户。他去一趟山姆会员店,一个小时就能买下我们一周所需的日常用品,家里什么洗洁精、餐巾纸之类的东西有没有,他全知道。
有时我真担心老哥脑袋里装的东西太多,一不小心会像气球一样爆掉。他要做律师,那些投、融资项目,挺伤脑筋的,还经常出入法院、仲裁委,办一件件复杂的案件。
我有时叫他有些小事不用管。他认真地说:“我没有大事,只有小事,也可以说,没有小事,只有大事。应该做的事,都是大事。”
在老哥看来,下雨的时候,打电话提醒家里人关窗户,和确认第二天案件的开庭时间,一样重要,一样都是大事,也一样都是小事。
他说:“工作也好,事业也罢,转个弯回来,还不是为了家?不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更幸福、更快乐?”
逗我们发笑是他的成就
我和老哥总被“双面胶粘住”,有80%以上的时间都粘在一块,形影不离。
老哥说:“一丈之内才叫夫,所以叫‘丈夫’,我必须得履行做丈夫的职责,保持跟你在一丈之内的距离。”他总是张口即来地把我逗笑,我只要一笑,他就开心。我们这样粘在一块许多年,总也不腻,一直都觉得彼此是最好玩的人。
和我们在一起时,老哥总致力于搞笑,奇怪的是,他并不费劲,要不早疲劳了。他用自己的方式幽默着,随时都能把我弄得爆笑。
和他乘电梯下楼去散步,他会在电梯里挤眉弄眼一下,或者扭动扭动身子,来个怪动作,还有时会伸出手臂,挡住电梯里的摄像头,亲我们一下,再对着摄像头来个鬼脸,说:“我什么也没干啊。”
我和老哥不在一块的时候,常发信息或打电话联络,他发的信息总把我乐翻。有时啥事也没有,他就发“妹,我爱你!”或“乖乖,你在哪里?”当我回来说到他的信息时,他赶紧问:“那你笑了没有?你笑了没有?”只要我说“笑了”,他脸上就像办完了一件超棘手的案子,飞扬着成就感。
有一天晚上,他跟客户有个迫不得已的饭局,到了七点半,我发信息给他:“哥,在哪?估计几时回?”他立马回复说:“在宝安,客未到,菜未点,人已饿,吃了饭,交了货,就拜拜。你别急,我想你。”他后来真的九点钟就回到了家,我说他的“三字经”太搞笑了,他马上认真地问:“你笑了吧?我边写边笑的,想让你笑一笑嘛。”
去年我和闺密杨杨在巴厘岛玩疯了,几天下来根本没打电话回家,老哥发的信息也没听到。
这当然得怪杨杨,如果我是江湖上某门派的掌门人,如果我老了实在统领不了这个门派了,如果我得找一个人来接管我的门派,那这个人,必定是杨杨。因为这家伙比我小那么多,又那么像我。在巴厘岛的那几天,臭味相投的我俩玩得昏天黑地,把所有的一切都扔到蓝天碧海里了。
有一天晚上,我收到老哥这条信息:“妹,将来我们去海边,中午吃完||乳鸽有地方睡觉了,傍晚游完泳不用再往市里赶了,东部华侨城玩了一天可就地睡大觉了,因为哥今天在海边买房送给你了,怎么样?送大礼了,请笑纳吧。”我大笑着读出来,跟杨杨开心地“笑纳”了。回来之后说到这条短信,他忙问:“那你笑了没有?我不搞笑一点你就不理我嘛,一个电话也不打回来,哼哼!”
老哥还有一项搞笑本领就是顽皮,他的顽皮总让我们笑得东倒西歪。
老哥和贝贝一起玩时,完全就像两个同龄的孩子,两个人超有共同语言,玩起游戏来特认真。他总是边和贝贝玩着,把贝贝逗得大笑,边偷眼看看我笑没笑。
老哥常跟贝贝学芭蕾舞,他总是伸出粗壮有力的老胳膊老腿,拼命做着轻盈的动作,让我和贝贝肚子笑痛。他跟贝贝学在幼儿园流行的民间段子,总被贝贝骂“你怎么这么笨呢”。贝贝常常边笑边说:“从来没见过这么搞笑的爸爸!”
老哥甚至害得我也变得顽皮。有时我们俩起个床就要顽皮上半个小时,边玩边搞笑。我有时吊住他的脖子,让他把我“起重”,结果几个回合下来,不但吊不起我,连他自己也给牺牲了。他有时要求我“亲死”才肯起床,我常要求他说十声“我爱你”才挪窝。
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起床以后,忽然发现他翻了个身,又趴下了,问他怎么不起来,他说:“我不敢面对生活,只想面对床,舒服。”。
玛亚总对我说:“你是阳光,见你得擦防晒霜,还得高倍数的,超贵的那种。”她指的是我的快乐指数,和脸上的幸福光泽,我想,这笔费用只能算在老哥账上。我的阳光,都是因为有他这个太阳。
书包 网 想看书来
“我的特长是会找老婆”(1)
无论是只能吃5块钱的晚餐,还是吃高档的王品西餐牛排,老哥总是很满足。
他经常穿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衣服。当我提出那些衣服穿得太久了,得去给他买些新衣服时,他总是扯着那些上了年纪的衣服得意地说:“这衣服96年才买的!”或者说:“这衣服多好,十年还像新的一样!”
除衣服外,他对所有的东西都比我们懂得爱惜。他看书时不舍得折角,不舍得在书上划线、做笔记。他收起影碟来,绝不会让手或别的东西碰到数据面。家里的杯子、碗、碟之类易碎品的破坏事件,从来没他的份,不会因为他而“光荣”掉。
老哥在任何东西面前,都有一种平和的谦卑,有一种连他自己都感觉不到的虔诚,一种生命情怀。似乎任何东西都被赋予了生命,在他的世界里,永远被尊重。他买回来的东西,怎么看,怎么喜欢。他一旦买回来了什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必定是从多方面论证这东西的好。
所以,我这个满身都是缺点的老婆,总被他当成掌中宝。他常宣扬说:“我的特长是会找老婆,可惜这特长再也没法发挥了。”老哥说起我的好来,总让我脸红心跳地疑心他说的是不是另外一个人。他为了说明自己的老婆是“天下第一”,从不说别人坏话的他,不得不以诽谤的语气评论着别人的老婆。
有一天早晨,一个平常而意识混沌的早晨,老哥先醒来了,他的大鼻子逐渐靠近我的鼻子,然后一下下地拱着我,挠着我,我故意不睁开眼。
()
他盯着我看了一小会儿,笑了,然后,用双手捧着我的胖脸,亲了一下我毫无反应的嘴唇,然后嘴里极其轻微地喊出一声:“宝宝——”他似乎想叫又不忍心叫,声音低得显然是叫给他自己听的。
这时我的心里澎湃着一个巨大的疑问:“天啦,是什么让他这么毫无理由的爱着我?”这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