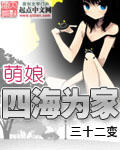红楼之林海-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歉鍪室顺鲂械暮萌兆印S谑翘嫠急负昧顺德砹闶常辉缇徒统隽硕牛�
“少爷好好逛逛,别总闷在家里。”
连翘就是当日林海醒来时,随母亲杨氏一起守在床边的小姑娘。她是林家家生子,自八岁分到林海身边,一心一意侍奉公子,更兼她从不往攀高枝上想,早早求了杨氏许了自己将来到林家茶园终老,因而深得杨氏信任,是林海身边一等一的大丫鬟,她说的话,在林海看来,基本等同于杨氏的话。
母亲的代言人有令,林海不敢不从,于是带着四个小厮往枫桥镇上而来。可巧,朱轼二月时又静极思动,说是要到扬州访友,月余方归,临走时特特叮嘱林海务必于三月时找个时间去寒山寺替自己施舍一番,林海虽百般推脱,但朱轼见不得他小小年纪学什么“慎独”,终究逼得他答应去一次寒山寺方休。
于是,林海一行人在枫桥镇的茶楼里要了二楼临窗的雅座,喝了三杯茶,吃了四块点心,做了五次心理建设之后,终于准备向寒山寺出发了。
刚从座位上站起来,就见旁边雅座上自他上得楼来就坐在那里喝茶的公子也站起来,那人身边跟着两个随从,其中一个在那人略有起身之意时便伸手相扶,另一个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径直向林海走来,离得三四步距离,对他大礼深揖,轻声道:“我家主人烦请这位公子移步一叙。”
4寒山寺外(修)
第四章寒山寺外
寒山寺虽在姑苏城外,但其地绝不偏僻,山头不高,平日里人来人往着实热闹,林海虽然是姑苏人氏,但他少有出门,家里并没有什么人给他讲解,便一直以为这整个山头就是一座寒山寺,没想到这位徒景之徒公子居然愣是在如此繁华之地找出个冷清小庙来。
无匾无额,只有三进,连住持带小沙弥一共也就七八人。正堂供奉的只有一尊佛像,不是现在佛如来,反而是过去佛燃灯,与外间寺庙都不相同。不过林海并不懂这些,在他看来,只是一尊佛像罢了。
他烦恼的另有其事。
那日徒景之遇有难事,身边刚巧没了可用之人,眼见林海带着四个小厮,看举止用度是大家出身,同时眼神纯净,并非一般纨绔,加上已经戴冠,想是个能做主的人了,便起了利用之心。
林海被徒景之派人相邀,他毕竟涉世不深,三言两语间便被人将身家打听得一清二楚。徒景之知道他是安平侯府的人后,更加满意。林氏的安平侯自开国封在姑苏,若从爵位上说,姑苏城里再没有盖过林家的了,如果跋扈起来,在姑苏便是横着走也没人说什么,但林家向来便是低调做人,族中三四代都是干领着侯爵俸禄,自初代安平侯之后既不出仕也从不上书言事,偏还子嗣不旺,家规又严谨,从不扰乱地方,低调得自己都差点把他们家给忘了……
徒景之随之更加和颜悦色,打点起精神,刻意与林海结交。他本就形容甚美,阅历之广又不在朱轼之下,与林海对谈,引得林海两辈子的小心肝都颤了起来。
来到大夏两年时间,林海的生活实在有些乏味。林谨知一直是严父的派头,平日里除了和朱轼忙着茶园,就是打点林家藏书楼和铺子,并不曾和儿子谈过心,杨氏是慈母,把儿子的身心健康看得比天都重,但她终究是个极为传统的内宅妇人,和林海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可说,自家亲戚又少,年节时见面除了互相恭维和被老爹拿出来展示读书成果外,也没有什么知心朋友。虽有朱先生的广闻博识可以交流,但在林海看来,朱轼的性格实在太怪,他为了茶叶留在林家,其实只是借口,实在是在家乡也呆不下去的缘故。朱轼并不是个好相处的人,仿佛前世林海的博导一般,甘愿为了科学奉献终身,却不曾注意观察周围的人和事,结果弄得自己诺大年纪还得带着弟子干些非常初级的调研……林谨知自己看不起腐儒,朱轼这样的正好合他的胃口,两人相交莫逆,林海却只是拿出当初在老师面前的老实态度,哄着朱轼高兴,好知道些外界事物罢了。
直到林海成了秀才,渐渐有了自己的交游圈子,他性子和顺,出身又好,以安平侯府的尊贵,却肯折节下交,才算有了可以说话的朋友。只是这些朋友多是林谨知口中的腐儒之后,大家在一起时,可以赏花弄月,可以吟诗作对,可以探讨科举,却无法有更多的交流。
如今这位“徒兄”出现在林海的面前,对林海而言,简直可以称得上惊艳了——无论是容姿还是谈吐,都极合林海的胃口。说地理,两人都对江河湖海了若指掌,说海事,两人都对海外贸易有很好的印象……林海浑然不觉话题是被徒景之带着走的,他只觉得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能真正交流的人,一个知音,一个可心之人。
是的,林海的春心,动了。
不论前世二十九岁还是个只看过动作片的清纯宅男,今生的林海已经十四岁,正值少年青春之期,母亲杨氏已经开始谋算着给他找个屋里人教导人事了,而林海自己虽不知母亲的心理活动,但他当初也是上过生理卫生课的,加上那隐蔽的性向,如今面对徒景之,那颤悠的心肝是怎么回事,他再不能骗自己的心的。
徒景之对林海也有惊艳之感,不过此惊艳非彼惊艳。在他看来,如海弟年仅十四,却对国事如此上心,尤其对于大夏地理所知之广博简直不在自己之下。他自己知道得多是必然的,无论是谁坐上了皇位,但凡想有些作为,就要知道这些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而林如海所知所闻又是为何呢?他深知林家一向低调,到林如海这一代没了袭爵,若还想忠于王事,就必然得走科举之路,如今知道林如海已经中了秀才,加上他对国事如此上心,可以肯定林家终究是精忠之臣了。看少年在自己面前眼神越来越亮,面颊也因谈话热切而微微发红,整个人似乎散发着光彩一般,饶是阅人无数的徒景之,也无法不动容,觉得自己这趟来姑苏,虽然遭伏中毒,却终究得了个未来的良臣,也还算不错。
两人越谈越投机,待到徒景之说出要请林海帮忙时,两人已经一个“徒兄”,一个“如海弟”地叫起来了。终使得林海在“徒兄”有难,自己岂能坐视不理的言辞下,跑前跑后,在徒兄指点之下,带着徒景之来到这么个奇怪的小庙里休养。
林海因着家教,不能在外留宿,当日只将徒景之送到小庙,看确实有人接应才告辞而去。随后几天,他每天都来小庙报到,在家中打的是为朱先生施舍的幌子,出得门来却是一头探到这无名之庙里去。
这无名小庙看似狭小,内里却有乾坤,短短几天功夫,林海已经见识到了不少奇事。比如第二天赶来侍奉徒兄的人突然增加了不少,而那两个贴身仆人,怎么看怎么都不像正常男人啦;比如自己每次进徒兄的寝室前,总觉得门外的卫士眼神扫射得太凶狠,好像自己是什么危险之物似的啦;比如有一回张太医来给徒兄诊脉,见到他竟端坐在徒兄身边时,失态得手都抖了一下,他本就是跪着的,这下彻底伏下/身去了啦……
这林林种种,加上前世王霸小说看得多了,林海自己其实也有了不少猜测。联想到前些时候父亲提到圣驾南巡,目下就住在扬州甄氏别院,要林海比平日更加谨慎,以防惹上什么祸事,他觉得自己的猜测八/九不离十,这位徒景之,徒兄,可能真是什么天潢贵胄微服吧?那么,自己的那点小心思,还是早早断了的好啊……
5当断不断(修)
第五章当断不断
林海很烦恼,就像所有进入青春期的小男生一样,他自从觉出了对徒景之的别样心思,又发觉了这位徒兄的身份非比寻常,就陷入了两难之中。
理智告诉他,必须迅速了断此事,不光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自己的家族。来到大夏两年多,他虽涉世不深,但已经感受到宗族对于一个人的束缚和支持。看江南甄家,宗族繁盛,从京中到四塞,都有他家的子弟,曾经号称“甄半朝”,就连皇帝南巡,也要将他家别院辟为行宫。反观自家,安平林氏四世列侯,在大夏也算是贵族世家了,但因宗族不盛,迫不得已只能保持低调,明哲保身。再看朱轼朱先生,他因个性狂放不见容于宗族,堂堂进士竟落得出走他乡、身无旁物。林海一来年纪尚小,二来他从来不是反抗体/制的思想先锋,既已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就更无法做出惊世骇俗之举。
前世看的那些小说里,什么天煞孤星,一个人挑战一个世界之类的,那必然是玄幻,林海虽诧异于自己的灵魂穿越,但两年来再没听过什么神异之事,在这实打实的大夏朝,玄幻小说的路数显然是行不通的!
不站队、不挑事、不跟风,是林家得以在大夏生存的基础,倘若徒景之真的是皇亲国戚,那自己和他交往就已经犯了宗族的大忌讳,更别说他内心深处的妄想了。
日思夜想,于是小小少年之烦恼便写在了脸上。他一时想着,还是应该趁着此时情根未深之时毅然挥刀,再不去见徒景之了,可是两世为人,第一次春心萌动,加上毕竟少年心性,这“再不去见”几个字在心里翻来倒去,终究成了虚话。
何况徒景之即便不当爱人,也是个极好的朋友。林海自知和徒景之的来往终究是镜花水月一场,因此在徒景之面前,林海将许多不能、不敢、不愿和父母、老师、诗酒朋友讲的话,都倒了出来,从天文数理到衣食住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徒景之呢,从未表现出对他那些奇谈怪论过于惊诧,反而能够和他探讨一番。
一日两人不知为何说起行路之时马车颠簸,林海随口说起安装弹簧可以减震,徒景之大感兴趣,虽然林海自己说得不甚清楚——前世他学的虽是物理,但动手能力极差,何况研究生以后的物理前边还有“理论”二字,可称是理论达人行动矮子的典范,但过不了几天,徒景之邀他同车出游,那车竟是加了减震弹簧的!
那一时的少年人,心里的震撼不可谓不大。既是出于对古人不可小觑的敬畏,更是出于徒景之对自己一两句闲谈竟记在心上的感动。
又一日两人说到万事农为本,林海一时没有收住嘴,胡乱发表了一通所谓“嘉禾”可能是杂交水稻中的良品,倘若加以研究而不是单纯当做祥瑞,兴许会让水稻产量迈上新高之类的言语。那日徒景之的表情实在精彩,开始稍有愤怒,继而深思,末了竟带着些了悟,是林海与他相交之时少有的七情上脸的模样。这种种表情都深刻在少年人的内心深处,许久不曾遗忘。
待到四月末的时候,朱先生返回姑苏,安平侯府也都知道了圣驾即将离开扬州返京的消息,林海听闻此事,便知道自己不必再内心挣扎,无论徒景之是什么人,圣驾既然北返,两人的缘分到此也就尽了。
他虽伤感,但因一早便知是虚妄之想,思恋了几日,表面上也就丢开了。此后林海一面应付母亲非要往他房里塞通房丫头的过剩母爱,一面愈加发奋读书——倘有一日金榜高中,或许就能直面徒兄了吧。
林海这里历经患得患失,定下了自家的前程之路,在徒景之这里,却又是另一番难断。
自圣驾北返天京,一路之上,司徒偃明知该收束心思,不可再去想作为徒景之时的一切,却屡屡放下朱笔,面对奏折而神思万里,往往在贴身内侍的提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