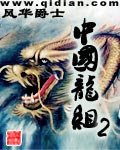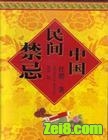中国在梁庄-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开始吐血,在县医院住有快两个月时间,血一直止不住,也始终找不到病因。最后几个月,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停地咯血,最后,鼻子、嘴里也呛血,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家里腥臭难闻。兄弟姊妹们刚开始还积极凑钱,积蓄花得差不多了,眼看也没什么指望了,于是为出钱又生了很多矛盾。没挨到小柱死,大家又都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小柱死之后,他老婆带着女儿再婚了。第二年,小柱妈查出来有胃癌,没钱动手术,很快也死了。
梁庄村出去打工的人,除了少数在校油泵,少数大专毕业生在公司干些技术活,大部分人都是建筑工人、首饰厂工人、三轮车夫、塑料高温车间工人、翻砂厂翻砂工。赵嫂的两个儿子就在塑料高温车间,还带了同村的几个男孩子去。据他姐姐讲,那里环境差得很,他们经常头晕、呕吐。但是,并没有人认为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即使知道有可能会影响身体,只要没出在自己头上,那疾病似乎也很遥远。
我少年的伙伴,清丽、冬香、多子,都到哪儿去了?她们是不是也和春梅一样,在家里苦苦撑着,等着那一年中仅有的幸福的几天,然后又夫妻分离?王家的一个女孩儿,自十几岁出去之后,将近二十年了,就没与家里联系过。她是活着,还是早已葬身于城市的哪一个黑暗角落?
但是,也并非都是绝望或痛心,乡村的痛,乡村的悲,总是包含着温暖与坚韧,因此,也还隐约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希望。就像五奶奶、芝婶、赵嫂和她们的儿女,无论怎样的痛苦、抱怨与争吵,背后还有亲情和谅解。
在路上碰到韩家种菜的老两口。我一直搞不清楚怎么称呼他们。韩家和梁家的辈分到底是怎么排的,父亲说那得从山西洪洞县迁过来那一辈儿说起,太久远了。反正,我和这老两口是同辈,叫韩哥,虽然他们已经七十多岁了。韩哥用扁担挑着两筐菜颤悠悠地往这边走,腰几乎快弯成九十度了。韩嫂拿着一把菜,跟在后面,也是颤巍巍的。但很显然,他们还很健康。还在田里劳作,依靠自己的劳动讨生活。
乡村也还是有生机的。那天一个堂嫂子来看我,她和丈夫两人在北京卖了十年的菜,在家里盖了房,还有一定的存款。在和我的交谈中,她一直说的是普通话,表现欲望很强,凡是谈到大的问题,她都竭力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中对城市人的市民气息严重不屑,因为市民总是为几分钱斤斤计较。说起现在房地产的行情,她也很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喜欢她那股强势及自鸣得意的劲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常年的城市生活及对自己生活的满意使她产生了一种自信。
但是,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却永远是异乡人。回到家乡,堂嫂自信而活泼,然而,在都市里,她只是无数的乡村打工者之一,是菜市场里的一个卖菜人而已。我的表哥,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每次到我家都手足无措,那种沉默、无奈的表情,常常让我震惊。实际上,他高中毕业,灵动,健谈,有头脑,在他们村子里是以聪明而著称的。但来到城市,他只是一个讨生活的打工者而已,他的情感、智力、生命,与城市没有产生任何交叉。
在所谓的现代社会中,农民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他们衣衫破旧,神情怪异,动作拘谨,显得非常愚笨,就好像鱼离开了水,半死不活。谁能想到,在乡村,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他们会是怎样地如鱼得水、生动自然呢?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梁庄的“华丽”转身
在一般的概念中,经济的衰退会造成文化的混乱与衰退。这是因为,文化的传承需要一种稳定因素的支撑,生活安定,经济充裕,才能够使文化的内在与形式得到充分的体现。但在中国当代乡村,结果却似乎恰恰相反。如果从最广义的乡村总体经济,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体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于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人们总是用“转型”这一个词来概括、形容这一断裂,却忽略了这一转型背后所造成的“黑洞”效应。
就梁庄村而言,整体的、以宗族、血缘为中心的“村庄”正在逐渐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虽然,作为村庄中的大姓氏,仍然会有安全感和主人翁感,但这种感觉已经被削弱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与一些发达地区为了经济利益、村庄宗族势力再度抬头相反。北方内陆的村庄,宗族势力很少能带来经济利益,因为本地几乎没有资源可以利用,大部分村民都是出外讨生活。
与此同时,村庄的规划、村庄家庭之间的内在联结,都在发生变化。村庄的最好位置往往是最有钱的住户,并以此形成村庄新的等级与阶层。而宗族家庭之间的感情往往很淡,尤其是新一代家庭,人们各自出门打工,春节回来一聚。对于村庄的政治事务、公共事务,譬如选举、修路、砖厂的去留、学校的建设,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
家庭内部也在发生变化。由父母通过日常生活教育孩子各种行为规范,变为由爷爷奶奶或亲戚代劳,父母和孩子之间似乎只有单纯的金钱关系。而随着学校在村庄的停办——它可以看做是统摄整个村庄向上精神的象征物,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去世——他们往往是村庄的心灵指向和道德约束,村庄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这一溃败意味着中国最小的结构单位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个体失去了大地的稳固支撑。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农村的确有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正成为新的环境、新的血液,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的整体生存状态。所有这些,只用“转型”二字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当以一种“内视角”进入乡村才会发现,在当代改革的过程中,对传统文明与传统生活的否定性思维被无限地扩大化和政治化,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想象也大多与这一思维同质。
当我就这些疑问与穰县县委书记交流时,他也深有同感。在听到我回来住在老家已经一个多月时,他大大地赞叹起来,他给我开了绿灯,指派自己的秘书和我一块儿,在全县范围内走访村庄,扩大眼界,从各个层面了解一下乡村的整体发展。
我们的第一站是一个小镇,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里是全国知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有着成熟的制作、批发、转销一条龙的大型产业链。每年做宣传,镇里就要花费数百万请明星、歌星,办大型文艺演出。由于制作的粗劣与仿制品的泛滥,1995年之后,该镇就慢慢衰落了,到2000年以后,就连镇上的居民都遗忘了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
镇党委书记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转业军人,说话精炼,有条理,正在对服装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期待重新恢复当年的辉煌。我问他,为什么在已经有广泛影响力的情况下,服装市场会败落?他很干脆地说,还是管理者不行,要想成为大型的市场,必须有先进的管理与经营理念。另外,就是商户的素质太低,太不注重产品质量。他的工作重点分为四步,改造街道环境,包括下水道、电力、路面等等;提高政府行政办事效率,抽调各职权部门集中在一起,使商户手续简单化;抓骨干品牌,骨干企业;扩大宣传,吸引外资。
镇党委书记侃侃而谈,俨然是一位实干家。他带我们去一家毛衣加工厂参观,这是香港的一家公司,老板的祖籍在本镇,回家探亲的时候政府鼓励他回来开厂。工厂简陋,一个巨大的开放式的厂房,有电扇吹着。机器在轰鸣,女工们在忙碌,一派繁荣的景象。
我却对车间里的孩子发生了兴趣。在一位妇女的脚下,躺着一个孩子,正在轰鸣声中睡觉,他的脸上落着白色的毛线碎屑,看起来很滑稽;一个孩子还吊在妈妈怀里吃奶,母亲用布兜拴着他,两只手仍然在忙碌;还有几个孩子围着机器,在捉迷藏,做游戏。我想,无论是工厂主,还是书记,都是不会在意这一场景的,因为在乡镇,这样的场景非常普遍。更何况,母亲能够不背井离乡,能够带着孩子,在村镇附近找来活做,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比起在城市里打工而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家,或把孩子拴在出租屋里的那些母亲,她们甚至是幸运的。
我忍不住问起厂长,这样是否有危险?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厂长认为危险不大,但他承认这样不合规矩。但是,如果不让她们带孩子进来,她们很可能无法工作。党委书记敏捷地接过话题,现在这样的儿童很多,他准备在厂里办公立幼儿园,妈妈可以把孩子放在这里,以厂为家。这样,既可以让妈妈放心工作,又解决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书记的思路让我为之一振,但是这也只是一种设想,谁来出这样的一笔经费,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但是,镇党委书记仍然改变了我对基层官员的认识,在乡村,也有这样锐意进取、希望做一番事业的官员,不管他是为了个人升迁、名利,还是其他的什么,在客观上,他在为公众考虑,在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无论如何,对于中国的乡村来说,有这样的官员总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我们又去了村庄整治的几个典型乡镇。这是穰县南面的几个乡,从县城出发,一直是平坦的柏油路,道路两旁是清新秀丽的白杨树,它们只有碗口粗,这是县委书记来之后为发展杨树经济栽种的。再往远处,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玉米、红薯、高粱,青葱翠绿,我恍然好像到了南方。到了模范村才发现,新的乡村规划已经完成。一排排房子,虽然仍是北方普通的屋架房,但是却高低整齐,规格基本一致,房前屋后不再是黄泥土,而是水泥地,有统一的下水道、垃圾池,还有沼气池。沼气池是近几年县里推出的一个节能项目,凡是建造沼气的人家都有一部分政府补贴。
我们进到其中一户人家里。只有老两口在家,儿子长期在外打工,他们在家里养些家畜,为了产生沼气,又专门养了两头猪。我们参观了他们的猪圈、沼气池,里面发出的巨大气味熏得人难以呼吸。问起使用的情况,老两口认为这的确是节省了煤气、煤球钱,但是,夏天气味太大。
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个乡的一个别墅村,那些别墅就盖在公路边。蓝天白云下,红砖白墙、圆顶拱门的别墅很漂亮。中西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