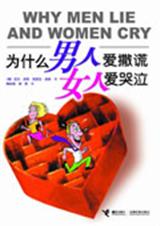官场女人-第5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把大字报跟引资招商联起来看,就会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不是的!完全不是的!”黄福瑞大声地嚷着。
张言堂给栗宝山递眼色,让他结束这次谈话。栗宝山也觉得该结束了,不然,黄福端要再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就不好了。于是,他站起来说:“好了,今天就暂谈到这里吧。
你好好考虑考虑,有时间再谈。“
黄福瑞拉住栗宝山,不肯让他走:“栗书记,你听我再说几句,你听我再说几句好不好?”
“我还有事,以后再说。”栗宝山说着,用力握一下黄福瑞的手,急匆匆离开了黄福瑞的办公室。
黄祸端看着自己的手,回想着栗宝山临走时的那有力的一握,似乎领悟到什么,呆呆地坐着。
当有人把栗宝山离开黄福瑞办公室的信息传到贾大亮耳朵的时候,贾大亮正在财政局找副局长李田个别谈话。他告诉李田说,他打算直布他主持财政局的全面工作。李田一听,心花怒放,恨不得当下给贾大亮磕几个响头,一口气说了许多表忠心的话。贾大亮很高兴。心想,金九龙的眼光还真不错。于是,他召集财政局科以上干部开会,先讲了一通形势什么的,尔后就说,鸟不能一日无头,人不能一日无主,财政局这样重要的单位不能没有主持全面工作的负责人。在路明停职检查期间,就由李田同志主持全面工作。
“栗宝山把路明叫到他办公室去了。”贾大亮又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把路明叫到办公室来谈,是栗宝山、银俊雅和张言堂精心策划安排的。路明显得很紧张,脸色苍白,嘴唇颤动。
“坐吧。”栗宝山打一下手势对路明说。张言堂微笑着向他点点头,指指栗宝山对面的那把椅子。
路明慢慢地坐下来,低着头,等候栗宝山问话。
“你的检讨写出来了吗?”栗宝山问。
“写出来了。”路明说着,从兜里掏出写好的检讨交给栗宝山。
()好看的txt电子书
栗宝山翻了几页,放下问:“你说说,你对自己的这个错误是怎么认识的。”
路明根据金九龙给他划定的框子,只原则地承认自己有错误,给自己戴了几项大帽子,一点实质的错误也不涉及,最后只把责任推到黄福瑞身上。
“黄福瑞具体给你说过些什么没有?”栗宝山十分关切地问。
“他说,引资招商是给你和银助理树碑立传。”
“他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前后还说过一些什么话呢?”
“是在议论引资招商的时候说的,前后还说过些什么……记不得了。”
“在什么地方说的?”
“在……在北京。”
“在北京什么地方?”
“就在住的那个旅馆。”
“在旅馆的什么地方?是在那个房间里?还是在楼道里?
还是在院里?“
“……在……在楼道里。”
“跟前还有别的人吗?”
“没有。”
“就对你一个人说的?”
“……对”“什么时间?”
“就……就去的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的几点几分,还能回忆起来吗?”
“回忆不起来了。”
栗宝山还向黄福瑞说了什么,干了什么,路明虽然牢记着金九龙让他随意乱编的指示,但见栗宝山刨根寻底地追问,不敢轻易地再说什么,只说下去想想再交待。于是,栗宝山给他作了一番开导的训话后,放他回去了。
接着,又把朱丽山和李发奎分别找来谈了。谈的内容都是一样。
贾大亮和金九龙等人,满以为撤销路明的财政局长已成定局,想不到在研究路明等人的处分时,栗宝山说,路明等人的认错态度好,又是初犯,主要责任也不在他们身上,所以提议只给了路明等人一个警告处分。至于黄福瑞,栗宝山说,他是地管干部,把材料上报给地委就行了,让地委结合大字报案件一并去处理。
这一来,李田的财政局长梦就破裂了。从贾大亮宣布他主持全面工作那一刻算起,到路明恢复局长的职权,总共还不到一天的时间。对此,贾大亮感到心里很不是个滋味,说不清这一回是胜了,还是又败了。
二十六、贿赂
这天早晨吃罢早饭不多久,一辆白色伏尔加开出市区,行进到去往太城县的国道上。车里坐着三个人:张少颜、孔发春和明清理。张少颜是地区检察分院检察二处的副处长,四十多岁,秃头善目,未老先衰,名叫少颜,却是不少,看上去颇有些城府的样子。孔发春是地区公安处三科的副科长,三十多岁,肥头大耳,一套崭新的警服紧紧地捆在粗壮的身材上,显出让人看了不很舒服的威武之相。明清理是地区政法委的干部,二十多岁,留着寸头,穿着西装,面露玩世不恭的现代派气质。他们三个人是奉了地委书记辛哲仁之命,要去太城县复查大字报一案的。从上车到现在,车里不曾有人说过话,三个人好像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慈眉善目的张少颜,此时合眼仰在座椅上,形似打盹,实际正在反复盘算着自己究竟该如何运筹为好?对他来说,这回遇上的事,是有生以来的头一次。这次弄好弄不好,是太关键太重要了。从昨天黄昏到现在,他的脑子几乎是没有停顿地在想这个问题。
昨天或许是他人生历史上难忘的重要日子。整个一天他在办公室里整理案卷,平常得几乎和往日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异。就在将要下班的时候,具体讲,是下午五点钟,检察长打电话把他叫去了。检察长说,他刚到辛书记办公室开了一个会,辛书记要抽几个人查一下太城县的大字报案,决定由张少颜带队去。接着,检察长向他简要介绍了一下案情,传达了辛书记的有关指示。他和往常一样,记下来,接受了任务。因为像这样的事,对一个检察干部来说,是很平常的,没有什么感到特别的。
从检察长办公室回来,就到该下班的时候了,他收拾了一下桌子上的东西,提上那个脏兮兮的帆布大提包,到院里推上车子,就往归家的路上骑去。
他家住在郊区。他老婆的户口前不久才从老家农村迁来,因市内没有住处,就在郊区租了间菜农的房子暂住。由于工资低,老婆还没有找上工作,经济比较桔据。所以,为了省钱,每天中午他不能回家,也不到机关食堂就餐,而是早晨上班来的时候,在那帆布提包裹带些菜什么的,中午待人们下班后,插上电炉子,在办公室里做巴做巴,吃口就行了。下班回去时,如沿途遇上什么便宜的东西,就买些装在帆布提包裹带回去。生活相当的俭朴。这天,在归家的路上没有遇上什么便宜东西,因而他很快就骑出了市区。
()好看的txt电子书
太阳快要落山了,下地的菜农已经收工回村,路上也没有别的行人,整个郊外显得空旷而清静。张少颜蹬着车子在田间小道上缓缓地行进着。
忽然,他发现前边的路上扔着一个什么乌黑闪亮的东西。他有些惊喜地用力蹬了几下,就到跟前了,当看清楚是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皮包时,他很快下来拣在手上,朝四下里看。周围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里头什么东西?”他心里这样想着,随即一拉拉锁,把包打开了。这一打不要紧,惊得他吓了一跳,里头竟装着齐茬茬十捆百元面值的人民币!活了四十多年,张少颜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么多的钱。
他又惊又喜,赶快又把皮包拉上。同时再次四下张望,还是一个人影也没有。这时候,贪财之心使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迅速将那皮包藏到了帆布兜子里。而且蹬上车子飞也似地往村里跑去。
不过,跑了一段,他又疑惑地下车了。他想,这么多的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该不是组织上有意在考验他吧?他再朝四下里看,依然一个人影也没有。“组织上为什么要这样考验我呢?有什么必要要这样考验我呢?”他想,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什么人遗失的。如果是遗失的,时间不会很长,因为下田的人刚刚归家,不然,下田的人就会拣到的。
如果是这样,丢失的人就会很快来找。他想到这里,又不由自主地跳上车急蹬。就好像失主就要追来似的。
然而,他又一次下车了。因为他想,让人家追来索要,还不如自己交公,款归原主。这样,自己不但可以上报上电视,还能得一笔奖金。这个想法使他在那里站了足有五分钟。但后来他还是没有去交公。他想,先回去跟老婆合计合计再说。
回到家里,他关上门,把皮包拉开让老婆子一看,惊得老婆失声而叫,被他慌忙捂住了嘴。他把过程向老婆说了一遍,老婆立刻跪到地上向天磕头,说是财神爷见他家穷,特意送来的,坚决反对他交公的想法。并且很麻利地数了一遍,包裹共十捆,每捆一百张,正好是十万元。老婆子数完后,高兴得抱起票子直亲。张少颜想,不交也罢,反正这钱不是他偷的抢的,是在路上拉的,他不交并不犯法。况且也没有人看见。他想,如果这款是个人的,说明那人有钱,或许是个发了横财的大款丢的,给他这个清苦人一部分也是该。如果是公款,更加没有什么问题。公家那么大,不在乎这点钱。而且他想,自己干了这多年,才挣四百多元工资,本来该提他当正处长,也没有提,现在连住的房子都没有,生活这样困难,有谁管他?他为什么非要那么顾国家呢?至此,他打定了吞下十万元巨款的主意。
接着,他便和老婆商量,把这么多的钱藏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不管钱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过后都会很快报案,很快来找,说不定晚上或者明天早晨,就会有人来。要是让人家从自己家里搜出这些钱,可就完了,不但款落不下,还会落下一个贪财的恶名。于是,老婆提出让他带上款连夜回老家去。一提回老家,他才想起了下午接受的任务,脑袋略地一大:“难道这钱跟那案子有关系?!”
“你怎么了?”老婆见他突然脸色变白,不解地问。
“你别问,不要说话!让我好好想一想。”他想,这些年来,为了逃罪、轻判、打赢官司而请吃送礼,是常有的事。
但这么送,送这么多,是太离奇,太不可想象了。他把怀疑说给老婆听。老婆立马否定。老婆说:“既然你有事,不能回去,我回去吧。”张少颜最后想,干就干吧,不能再犹豫,再犯傻。今后有了这十万元,日子就好过了。放着送上门来的福不享,那就太愚蠢了。即使是有人为那案子贿赂他,也无妨,反正他没有把柄落在他手里,就是他达不到目的,他也无法将他怎么样。就这样,当天黑下来之后,他把钱让老婆带好,悄悄送老婆出了村。
这一夜,张少颜根本就没有睡着觉。他总是幻觉有汽车响,有人来敲门,吓得一回一回地出开。实际上,一夜无事。到了第二天早晨,还是无事。到了机关,依然无事。这个平静无事的情况,倒使他越来越感到那十万元好像与那个案子有一种什么关系。他的心因此缩紧了。
检察长打来电话说,地委办公室来电话催了,叫他快过去,等他走呢。他心流意乱地到了地委,见孔发春和明清理早在那里等着他。他们几个人好像都用审视的眼睛看着他,使他感到异常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