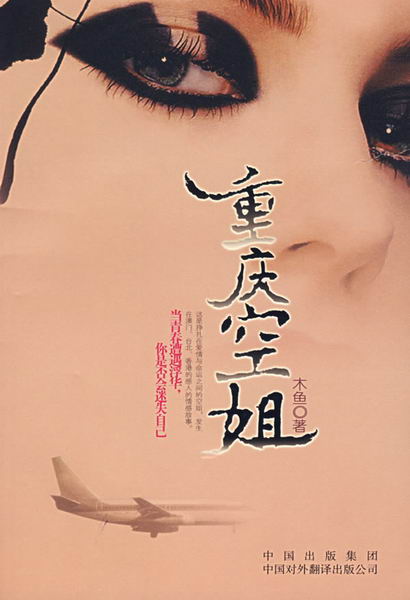重庆噢啊噢-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还是个学生娃呀!我就是说你咱个是这个样子。房子我有,我的街上租了房子,唉,今晚我表妹在,明天晚上我让我表妹回去就行,她说。
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不信我连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都拿不下来。
好吧!明天晚上我就在舞厅门口等你,现在我就先回去了。我说完就走出了舞厅,我心里有点讨厌这个女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重庆噢啊噢 (53)
53
方君在她租住的房子里拿出画板、笔、颜料,准备画画了。他们系里要搞毕业作品展。
方君先画了一个坐在凳子上的女人,她画女人时没有把女人的胸部画出来,画了两天后她拿去让她的老师看,我也跟着她到她们班的教室,教室里有几人学生在画画,四周的墙壁上已挂了很多作品。我不看不知道一看就看出了方君和她的同学们之间的差距。以前美术系搞展览我碰到了都会进去看看。一次看到一幅用白色布条挂在展厅的大梁上的农村使用的架子车的一幅轮子,轮子下面作品的各称叫《农村公社》。我小时候农村的生产模式就是农村公社,村子里面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人们集体劳动,平均分配,那种集体劳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很低,大家一起劳动,一个靠一个,能偷懒就偷懒,能混则混,反正分粮食是按人们的劳动天数计算,大家都吃不饱、穿不暖,后来解散了。那一幅轮子和那些白布条我看了半天也都不解其意。还有一幅墙壁挂着一张白布,白布上溅着蓝色的红色的墨水,白布下面就是几只打碎了的墨水瓶。这幅作品的名字就叫《无名》。我在想,如果这些都有能称为艺术品,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艺术家,我拿两只蓝色的红色墨水瓶对着挂在铁线上的床单闭上眼睛一阵乱甩,睁天眼睛一幅作品就出来了。我感觉一幅作品,最少能打动人,给人在视觉感觉上一种刺激,一种冲击,通过这种视觉和感觉能在人的内心造成一种震动,或者达到一种共鸣。这种作品能让人心理上感到一种美好或者难受,但是你的作品给别人没什么感觉或者百思不解,就是失败,就称不上什么艺术品。
方君的作品就是这样,她画了一个女人,很平常的一个在凳子上坐着的女人,这个女人的感觉,就是很平常的一个女人。
我们到她们教室,教室里有很多人。他们的老师戴着一顶鸭舌帽,嘴里嚼着口香糖。我一眼就认出他是一次一位日本教授在学术厅搞讲座时的翻译,当时我以为他是外语系的,没想到他是美术系的。她的老师嚼着口香糖明确指出,方君画如果不看头饰,根本看不出她画的是女人还是男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我一听到这里马上走开了。
墙上一幅画画着两个年轻人,看这两个人物的面部表情是木的,但是人物面部肌肉光滑饱满,这种只有年轻人才有的脸。如果不看这张画的面部看人物的胸部,两个人物穿着的衣服上铜质的楞角分明钮扣和钮扣中间很粗针线,一看就知道是年轻人穿的牛仔装,老年人哪个穿这种衣服。墙壁上还有一幅蜡染的紫色图案的衣服,上面的花鸟栩栩如生,好象要从衣服上的树枝上飞起来。方君见我看的入迷过来解释说做这件衣服是一个贵州的同学,其实这件衣服也不是她的同学自己做的,而是她从家里带来的。
我的心里一下升出一种厌烦,我说你先不要说别人怎么样,你有作品没有通过,而且里面错误很多。她说是她的画里面的颜料太薄了,没有立体感。我看的那幅画着两个年轻人的画的同学都三十多岁了。
方君决定重新画两幅画,一幅是人物,另一幅也是人物。
她先画一个身穿黑衣服的女人,第一天晚上画到十点多,她画一会站起来看一会,看一会再坐下来画一会。她画的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女人,头发飞舞起来像火在烧。
我感觉她的这幅画的创意还可以,但是她画的是一个热情奔放,头发像火炬一样燃烧的女人。这种女人应该表情丰富,神采飞扬。但是方君画出来的女人两眼无光,表情呆滞。我指出我的这些看法后方君开始烦躁起来,她出去买了一包烟进来点上,她的头发遮住了她的眼睛,她用一根带子扎在头上像一个道士,一会儿带子开了,她气急败坏地用手使劲拔了几下后用一个橡胶圈扎在后面。地上颜料、画笔、烟、打火机乱七八糟地摆的到外都是。
第二天上午我到她住的地方,她已起来了,那幅画整体出来了,但是画上人物眼神和人物头顶的火炬的颜色不相称。
我们又去了她们教室,去的时候我拿着那幅画,她们教室的四面墙壁上又挂了许多画,一些空着的地方已有人写了纸条标明已占,还有两个同学因展位太小和不在显眼的地方和老师争辩。方君看了一会就出来了,我们回到她住的地方,方君就把那幅画扔掉了。
第二天就是截止日期,我建议方君避开动态的东西画一个静态的,比如画一幅风景,我在她们教室里看到有好几幅作品是画风景、物品、机械的,但是她说静态的东西她没画过。
晚上方君拿来一幅画,两个胖嘟嘟的脸红扑扑的戴着帽子的小男孩坐在草地上,一个小孩手里拿着线板,一个小孩望着天空。一看就知道是北方草原的小孩在放风筝,虽然地上的草绿了,但是草原上的风还是很冷,两个小男孩圆圆的头、圆圆的脸、穿着厚厚的衣服坐在草地上就像两个圆圆的球,身后的草地一望无际地绿着,头顶的天空一望无际地蓝着。
这幅画是方君借别人的。
第二天她们年级毕业汇展开始,有几个老师来参观打分,展厅外面站着许多她的同学,一个同学手里拿着一只玩具狗放在脸上做着亲昵的动作。老师们打完分就走了,我又进去看了一会,我注意找赵海萍的名字,四面的墙壁上没有她的作品。我看了一圈走到门口,我看到教室中间的展台上摆了许多手工作品。我走上前去看到上面有手工编的篮子、花鸟、动物,这些作品一个个做工精致,形态逼真,找到作者的名字一看,作者就赵海萍,没想到赵海萍还有这一手。
()好看的txt电子书
重庆噢啊噢 (54)
54
我看到在台阶上站着的几个同学的头发在阳光下像发黄的草一样在风中起伏。当然,他们几个没有注意到我在看他们,看他们黄|色的没有一点光泽的头发。我把阿龙叫到身边,指着那几个同学说,你看,那几个家伙的头发怎么像草一样枯黄!
这几个家伙,肯定是事干多了。他说。
我一想,也真是,那几个家伙都有女朋友,平时在学校里搂肩搭背地公然出入,难保没干事。
我问阿龙,你怎么知道别人事干多了?
肯定是身体里面的东西让女人吸干了,头发不黄才怪,你看我的黄吗?阿龙反过来问我。
我看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又浓又亮。
这是系里第一次把我们四个年级的学生一同集合起来,系主任站在台阶上大声骂几个学校给了处分的同学,他让几个受了处分的同学举起手来,我看了一下,那些同学都是少数民族的,他们平时都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有时花衣花裤,有时一条长长的斗篷。平常吃饭喝酒都在一起。我认识一位叫江布的比我高一级的同学,他可以说是他们年级的重点人物,平常年级有打架斗殴的事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的,他人高马大,面黑眼大,有点侠客的味道,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只要找到他的门上,他一概帮忙。
曾皮留级的事就和他们这些少数民族的同学有关。他们这一级还是按科目记成绩,不像我们施行学分制。曾皮一到学校不好好上课,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搞创作,一天只是在吃中午饭或者晚饭时上骑一辆破自行车飞驰在去饭堂或者到学校外面去的路上。他们这一级一学期成绩有四门课不及格就要开除,一学期下来曾皮有五门课不及格,而那些少数民族的同学也有很多人四五门课不及格。曾皮就和江布几个少数民族的同学商量,少数民族的学生学校本来就收分低,像江布凉山的学生大多都是委培生,到学校时的分数更低,这些同学到学校后因基础差,很多课程学起来本来就很吃力,而这些同学平常又喜欢喝酒,一到周末就凑在一起喝得天昏地暗,平时上课也不是专心听课,考试时就一个个傻了一样。江布他们几个少数民族的同学知道他们自己都有被学校开除的危险,这些地少数民族的学生好不容易从偏远落后的大凉山出来了,回去丢人显眼,哪个也不愿意回去,他们一伙就到系主任家门口静坐请愿,他们的借口是自己是少数民族学生,基础本来就差,是地区教委托培养生,毕业以后也是要回去,要求学校给他们降低分数线。曾皮的理由是他是学校的特招生,文化课基础也差,在学校期间写了不少诗歌,有很多在国家级的刊物上发表和获奖,为系里为学校争了荣誉增了光,也要求学校降分数线。他们一伙先和系主任谈话,没等到系主任的答复就在系主任家的门口静坐到了天亮。
学校对他们都留了情,曾皮被留级,江布他们少数民族的学生学校按45分的及格线而全跟着原来的班继续上。
但是,他们少数民族的同学又出事了。
我们班也有几位少数民族的同学,少数民族的同学又数凉山的同学最喜欢争强好胜。那段时间凉山的“飞鹰组合”风靡一时,其中的《回到大凉山》,《火把节》,《赶集回来啊来来》几首歌天天有人在学校广播里点唱。《火把节》里面有几句是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唱的,一天晚上我去问我们年级的凉山的一位同学阿加那几句少数民族语言是什么意思,阿加一遍一遍地给我唱,但是他一唱到用少数民族语言唱的地方也变成了少数民族语言,我问他如果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他呜嘟了半天只说是在火把节上年轻男女追求爱情的意思,用具体汉语表达,他感觉怎么也说不出那个味道。
那学期阿加在班上选了八个女生给她们教火把节的舞蹈,女生们学会后系里举行元旦晚会时大获成功,后来成了我们系里的保留节目,不管举行什么节目,火把节的舞蹈都会上演。
阿加平时也没有多少话,只是在周末和他的少数民族兄弟们一起玩。他们在一起时主要就是喝酒,只要是周末,阿加都是在半夜回来,有时歪歪倒倒地一个人,有时是他们少数民族的同学们抬他回来。他睡上铺,一次半夜尿急,他竟拿出东西在宿舍里面解决了。同宿舍六人,谁都不好意思说他,由着他的性子,在他酒精麻醉后混乱不清的神智的支配中胡闹。班里汉族学生占多数,但是汉族学生面对他们强悍的体形和性格时个个显得萎萎缩缩,显得小里小气。
我们刚到校报到后年级第一次集中点名,点到一位同学时这位同学用一句少数民族语言回答了,教师当时就说是不是是少数民族的同学,老师一问,同学们都向着那个同学的方向看,这个同学是左林。军训时教官管的很严,一次课间我请了假去邮局时,在街头上一家小卖店前见一位穿着军装看上去很眼熟的同学在喝啤酒,一问是我们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