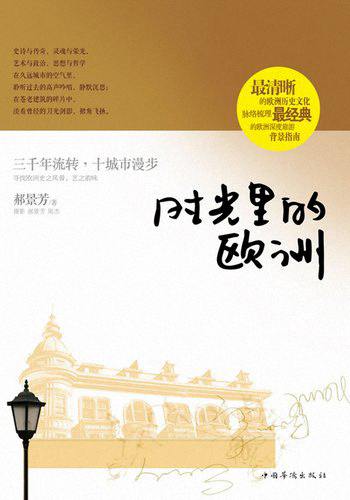b小调旧时光-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讲完之后,我让他在吉他上找出标准音“la”;他顺利弹了出来。我弹出一个“so”,问他:“听得出区别么?”
6约翰…列侬的理想世界(3)
“听不出来。”
我又弹出一个低得多的“do”,问他:“这次呢?”
他茫然地摇着头:“听不出。”
我苦笑一声。看来这部吉他要一直新下去了。我没见过对音高这样不敏感的人,但也不忍心打击他。毕竟从理论上来说,长着此类耳朵却能练出一手好琴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贝多芬中年之后还是个聋子呢。
但以常理判断,他会在最长一个星期后放弃征服六根琴弦的努力。
从当天起,我和动物般的女孩或者在房间里弹琴,或者到街上闲逛,张彻则把自己封闭在地下室,一门心思追随约翰?列侬的伟大足迹。他练一会儿琴,听一会儿音乐,再练一会儿,再听一会儿,周而复始,可以持续十几个小时,直到我们给他带饭过去才告一段落。吃饭的时候也左手拿着汉堡或三明治,右手练习指法。如此努力,成果却基本是零。一个星期下来,他连八度音节都不能弹下来。
张彻不仅听音能力一塌糊涂,而且手指的协调性也有问题。对于他这个身手矫健的人,这倒难以想像。他可以坐在飞驰的自行车上,稳准狠地用链子锁击中某人的头顶,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却死活无法将五根手指合理地运用在琴弦上。不是按错弦,就是按不到弦,情急之下,还会整个手掌在琴上一阵乱抓,好像要碾死一只老鼠。
青蛙用长着肉蹼的手掌弹琴,大概也就这个效果。发出的也不再是吉他的声音,甚至完全就不是弹拨乐器的音色。
对于这种情况,只能理解为上帝不允许他弹琴,或者他上辈子曾以回收销毁破旧吉他为业,所以这辈子吉他与他为敌。
他却不为所动,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下定决心和吉他较上了劲,还预备四处拜师。
“哥们儿以前没理想,现在有了,那就是当一摇滚艺术家。”
一个耳朵和手指对于音乐来说基本是残废的人居然确立这种理想,确实也可歌可泣。
一个星期过去,张彻更加废寝忘食,完全变成了所谓的琴痴,并在意识形态里正式将约翰…列侬推到了神学的高度。徒劳无功的练琴之余,他会背上“蜻蜓”牌吉他,流窜于师范大学西面的平房区。
那片平房里,居住着一些自诩为摇滚艺术家的闲杂人员,靠在酒吧街弹琴唱歌维持生计。此类社会贤达,生活内容倒也简单,白天练琴,晚上到酒吧演出,等待被唱片公司相中:一贫如洗,潦倒不堪。据说也有几个被音乐制作人叫到公司去当过伴奏,甚至还有小小混出点名气来的。但幸运者总是少数,而且一旦有人获得这种机会,马上就会被圈里人鄙斥。
“丫傻×一个,根本不是西方学院派的路子。除了媚俗之外没别的长处,要不怎么能被唱片公司看上?”
()免费电子书下载
盼着被“发掘”,一旦被“发掘”了又立刻变成###,这大概是中国地下摇滚界特有的悖论。
不过这些平房里的社会贤达也不是完全浪费粮食,他们对社会还有一些贡献,就是协助派出所破案。一旦发生丢自行车、家庭主妇钱包被抢、打工妹被强Jian之类的案件,警察就会把他们请过去。熟门熟路的,他们进屋就打招呼:“政府,您好。”
警察也很和颜悦色,对他们说:“来啦?那边儿请吧。”
他们便大模大样地走到墙根,解下裤腰带递给警察,抱头蹲下。双方开始就最近的治安情况进行探讨。警察一般会问:
“某天下午,你在哪儿混着呢?”
“不要说混,”摇滚艺术家说,“我当然在搞艺术。”
“时间地点。”
“一点到五点,在屋里练琴。”
“真的假的?那包子铺的小姑娘让谁×啦?那你们对门老太太的三轮车让谁撬啦?”
“政府,我真练琴呢。”
“口说无凭,你们先在这儿交流交流,一会儿人到齐了就知道啦。”
于是蹲在墙根的艺术家就叽叽喳喳地讨论艺术,搞金属的骂搞朋克的是傻×,搞朋克的骂搞金属的是傻×,大家一起骂和唱片公司签了约的是傻×。骂了一会儿,全体平房里的艺术家陆陆续续地到齐,几乎占了北京摇滚界的半壁江山。蹲得长了,未免有人提出要求:
6约翰…列侬的理想世界(4)
“政府,我想拉屎。”
警察说:“你瞧,心虚了吧。”
“不是,纯粹是蹲的,蹲久了肚子里的东西往下坠,绷不住劲儿。”
“那快去。”
去之前,还要把鞋带解下来。摇滚艺术家提着裤子、趿拉着鞋去拉屎,拉完了未免又动了点儿心思,妄图像鸭子一样一摇一摇地溜掉。谁想到警察早料到这一招,守在厕所拐角:“想跑?自绝于人民。”
“不是,”艺术家解释说,“我拉完才发现没带手纸,想回去拿。”
“不用擦了,反正裤子都穿上了,回去接着蹲着吧。”
蹲得差不多每个人都拉了一泡,事主才被警察带过来指认,这确实是一个类似于摸彩票的过程。摇滚艺术家清一色是脏兮兮的长头发,两三个月没洗过,如同脑袋上顶了一团墩布;浑身又瘦又臭,好像一条癞狗。事主往往看了几遍,也看不出,摇滚艺术家则在乱叫:
“大姐,强Jian您的真不是我。”
“大姐,您要真想指认我,就把我算成偷自行车的算了,我赔您一辆自行车。指认我强Jian我能赔您什么?贞操能赔么?”
“大姐,您好歹也算当上回原告了,够牛×了,牛×牛×算了,别连条生路也不给兄弟们留啊。”
事主被搅得晕头转向,只好随便指出一两个完事。被指出来的大叫冤枉,但也无法,跟着警察上分局。没被指出来的胡乱领条裤腰带,被打发回家,临走警察还说:
“谢谢合作破案啊。”
摇滚艺术家边走边说:“见天的把我们叫来开会,干脆把这里改成文联下属机关算了。”
张彻背着“蜻蜓”牌吉他到平房区拜师学艺,如果直奔派出所等着,绝对可以把吉他高手一网打尽。无奈他不知道这个窍门,而且万一进了派出所,也会被警察扣下。他只好顺着胡同,一间一间地找过去。
只要一听到琴声,他就凑过去敲门,门一开。也不搭话,直接鞠躬:“大师,您教教我!”
()好看的txt电子书
一般百无聊赖,都会好为人师,何况人家开口就叫“大师”,可摇滚艺术家偏不如此,他们无聊的时候喜欢搞党派斗争。张彻还没抬起头来目睹尊荣,就被劈头一句问道:
“你是搞金属的,还是搞朋克的?”
这个二选一,很难作答,不知道怎么才能投其所好。刚开始,张彻实话实说:“不知道啥叫金属啥叫朋克,我是搞甲壳虫的。”
“也就是beatles对吧?香港那边翻译成披头士对吧?”对方立刻显得很懂的样子。
“对对,听您一说真长见识。”张彻拍马屁。
孰料对方却道:“滚吧。”
“为啥滚?”
“都他妈什么年头的玩意了,别出来丢人现眼。你丫,太年轻,太简单,太幼稚!”
听到人家这样说约翰…列侬,张彻自然有点不乐意,但对大师也不好说什么,他只好说:“那您教我点儿深的。”
对方又绕回问题的出发点:“那你先说,金属和朋克,你支持哪个?”
事到如今,张彻只好蒙一个:“金属万岁!”或者“朋克万岁!”既然是蒙的,总不免有错的时候。假如他说金属,不幸对方又是搞朋克的,或者他说朋克,不幸对方又是搞金属的,立刻会被一通大骂:
“你丫这傻×,懂他妈什么叫摇滚乐么?屎壳郎上马路——假装小吉普,屎壳郎坐飞机——臭气熏天,摇滚乐就毁在你们丫这帮狗×的手里啦!”
不仅要骂,还要动手,很多大师看到张彻是个并不凶悍的小年轻,都情不自禁地抄起酒瓶子、折叠椅、半块砖头向他乱打一气:“为了中国摇滚,我跟你拼啦!”
刚开始,张彻还看在艺术的面子上,也不还手,一边躲闪一边说:“大师,您息怒!”后来那帮孙子给脸不要脸,越打越凶,他只好翻脸,从自行车筐里抄起链子锁,一个旱地拔葱,跳起两尺多高,一家伙敲在对方天灵盖上,致使其口吐白沫,歪在门框上两脚抽搐。
6约翰…列侬的理想世界(5)
打完以后,张彻推车就跑,再去寻找下一个大师。但下一个大师也逼他回答“金属还是朋克”这个二选一的问题。
后来张彻发现,即使答对了,他蒙的答案和大师所属的流派一致,也于事无补。比如说他回答“金属万岁”,正好大师也是搞金属的,本以为可以拜师了,大师却会进一步细化问题:“你也是搞金属的?那咱们也未见得是同志。你是搞重金属、速度金属,还是死亡金属的?”
如果答错了,还是连骂带打,为了中国摇滚拼了,最后张彻只好再把这位也打得口吐白沫。这样看来,他的师是拜不成了。不过也是天作巧合,他歪打误撞,把精神病患者黑哥领了回来。
当时他已经快要转完那片平房,打了接近二十个摇滚艺术家,正要心灰意冷,打道回府,却听到胡同口还有一个弹琴的。反正已经转到这儿了,就算不成,无非也是一链子锁的事儿。于是他跑过去拍开那扇呲牙咧嘴的木门:
“大师,您问吧!”
里面走出一个黑得像非洲人、头发脏得像涂了猪油、白眼球占据眼眶十分之九的家伙。那家伙看看张彻,迷惘地说:“你让我问?问什么?”
张彻没想到这位没有问题,反而不知如何是好了,他顺嘴说:“您想问什么就问呗。”
那家伙便问:“安眠药、刀片还是麻绳儿?”
安眠药、刀片还是麻绳儿?这就是黑哥向张彻提出的问题。问得没有来由,自然也就无从答起。后来黑哥和我们混在一起,经常会问出此类选项组,比如说:电门、氰化钠还是钻头?京广大厦、昆明湖还是永定河?生鸦片、金镏子还是五四手枪?无论他怎么问,都是没法回答的问题。
当时张彻找不着北,问黑哥:“问这些干吗?”
黑哥高深地说:“我自有用处。”
张彻想了想,黑哥所说的那三样东西,其共同作用大概只有两个:杀人或自杀。而无论是哪种用途,都不大好乱出主意。他问黑哥:
“你要干吗?”
黑哥郑重地说:“要自杀。自杀嘛,就是自己把自己弄死。”
()免费TXT小说下载
张彻说:“这个我知道。但你为什么自杀呢?”
黑哥说:“多简单,活腻歪了呗。”
张彻说:“那你为什么活腻歪了呢?”
黑哥说:“更简单,活着活着就腻歪了呗,活了这么多年,当然有可能活腻歪了。”
张彻说:“这个问题还是很复杂,怎么就活腻歪了呢?”
黑哥回头望望,如同望着往日时光:“大概过去的每一秒钟都在酝酿这个结果,而究竟怎么酝酿的大概很难说清楚,我只能牢牢记住结果而已。”
张彻说:“那你是从什么时候有了这种想法的呢?”
黑哥说:“不知道。总有几年了吧。”
张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