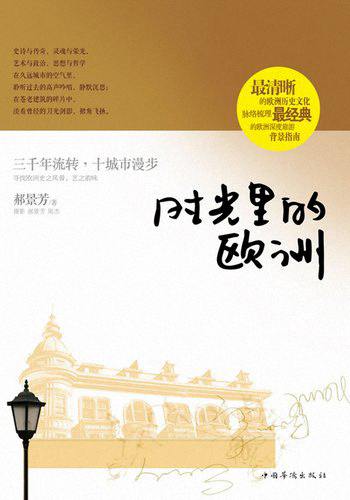b小调旧时光-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在都挂牛脖子上了。
张彻和络腮胡子的男人满牧场地追着牛,逮谁给谁发bp机:“戴上吧哥们儿还是大汉显呢,过去三千多还不一定买得着呢。”牛们表情傲慢,无可无不可地挂着那玩意埋头吃草。
一直挂到中午,才挂了两百多个。张彻已经累得不行了,浑身牛屎味,还被一头母牛踢中了肚子,吐了半升白沫。看看天色不早,他不得不停下工作,急着开车进城去买呼叫台的必要设备:发报机、天线和功率放大器。
“你自己开车去好了,我又不懂,免得给你添麻烦。”我把车钥匙给他。开车进城需要往返近两百公里,回来时天肯定黑了,我不想误了给拉赫玛尼诺夫送行。
张彻自己开着车出了牧场,我无所事事地站在院子门口看着秋草。草场犹如一夜愁白的鬓发,已经在绿色之上覆盖了枯黄,平原上的风吹过,方圆十里内似乎回荡着悲鸣。
晚上那顿饭,大家照例喝高了。虽然张彻不在,可老流氓兴致不减,一个劲地灌黑哥喝酒。黑哥闷声闷气地像个无底洞一样,喝了三四瓶三十八度的白酒也不动声色,黑脸上一丝酒红也没泛上来。
“牛逼,哥们儿你太牛逼了,”老流氓语无伦次地说,“是个司局级干部的料。”
黑哥已经喝得机械了,都不用别人劝,咕咚又是一杯进肚。
我和动物般的女孩随便吃了几口羊肉,小杯沾唇地抿着酒,坐等夜色全部降临。老流氓还想灌我,被我像豹子一样暴声喝开:
“滚蛋啊,别招我,否则灌你老丫的。”
他佯装无事地躲开,小声取笑:“你是不是到经期了,这两天脾气那么大?”
我扭过头去不理他,看着窗外泼了蓝墨水一般的天色。
络腮胡子的男人彬彬有礼地举杯和我碰了一下,但我感到他神色古怪。看什么都不对劲,大概我也有点精神紧张了。我和他对笑了一下,一口把酒干了,反扣杯子,不再喝了。
一直到窗外完全漆黑一片,草场的风吹进寒意,黑哥还是一杯接一杯地喝。我按住他的杯子说:“黑哥,没人劝你就别喝了。”
他忽然奇怪地说:“你闻闻,这酒怎么没酒味儿啊?”
我接过杯子闻了闻,呛得抽了抽鼻子:“怎么会,曲酒,味儿挺冲的。”
“不会吧,”他摇着头说,“我喝着明明就像白水一样,白水一样,白水一样嘛——”
()
说着又喝了两杯,就像喝水一样,品都没品就吞下去。我想坏了,喝不出酒味,大概就是喝得太多了,所以鼻子和舌头都麻木了。他的面前已经或立或倒地放了好几个空酒瓶子,用筷子一敲,叮咚作响。
我说:“黑哥,真别喝了,就是水也犯不着这么喝吧。”
黑哥饱含热泪地大叫一声:“让我喝,我心里苦!”
刚说完,他忽然轰隆一声,仰面就倒。我低头一看,何止是脸,他就连脖子都通红了起来。他仿佛醒悟一般说道:“原来真是酒,有酒味了!我的妈呀,怎么灌进去那么多酒啊!”
20魔手终结与动物般女孩的消失(2)
然后黑哥便满地打起滚来,一边滚,一边哭诉自己想自杀,但又不知道怎么自杀。每打一个滚,他就举例一种死法,问我好不好:“上吊好不好跳河好不好吞金好不好喝农药好不好跳楼好不好——”
我只能说:“都挺好都挺好都挺好。”
这么闹腾了半个钟头,人类的死法大约被穷尽了,黑哥忽然坐起来,像鹅一样伸着脖子干嚎两声,对我说:“我想吐。”
“那我躲开点。”我后退一米,“就这儿吐吧,这儿不是咱们家,吐完咱还不用收拾。”
“可我吐不出来,噎住了。”
“噎住了那是咽不下去,不是吐不出来。”
“反着噎住了,总之是堵着了憋着了管道不通了。”黑哥吼叫着,脸越涨越红,而且向吹了气一样越涨越大,抓胸捶背,弯腰顿足,看起来十分痛苦。
我看到他无比躁狂,眼见发疯,也手足无措。老流氓还在扯淡,问络腮胡子的男人要洗衣机水管“给丫灌肠”。
我正想给他找点水喝,黑哥忽然暴吼一声,拔地而起,破门而出,冲了出去,他一边在原野上奔跑,一边遥遥地喊道:“我要吐我要吐我要吐——”
远方传来的回声说道:“噎住了噎住了噎住了——”
我拉上动物般的女孩,说去追黑哥。但来到门外,黑漆漆的夜里已经空无人影。我们肩并肩地向昨天下午遇到拉赫玛尼诺夫的方向走去。
夜风有如海浪,在耳边呼啸不停。我和她踏着齐膝的杂草,连星星都看不到,只得凭着感觉寻找方向。那么大的风竟然不能遮盖住她的呼吸和我的心跳,并且每走一步,脚下草茎的呻吟声都清晰入耳。
如果不开车的话,这段路真是遥远。我们失去了车厢的保护,仿佛赤身裸体地暴露在苍穹之下,去迎接世上最奇异的变化,每走一步都危机四伏。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我才看到几百米外似乎有人影。逐渐走进,拉赫玛尼诺夫的身影显现出来,他孑然一人,好像无所事事一般插着兜,站在原野之上。
我们加快脚步,几乎是小跑着奔了过去。他看到我们,并没有打招呼,只是转了半个身,面向我们。
“魔手就在这里,一共九只。”他从兜里掏出一只厚厚的金属杯子说,“不要看它小,其实魔手是无形无状之物,不管多少只,都可以装进去的。”
我看着那杯子,它在深夜里连一丝光芒也没发出。我忽然想起,这就是我们偷窥他的那天晚上,他使用的杯子。当时他从杯子里拿出几个金属块,喂给神情迷乱的呆傻青年吃。呆傻青年和魔手又有什么关系?
“那您将怎么离开这里呢?”我撇开自己的想法,问他眼下的问题。
“用这些魔手的力量,完成一次时空穿行,就像我来的时候一样。在魔手成熟以前,跨度超大的时空穿行是不可能的,但好在终于到了它们瓜熟蒂落的时候。”
“就这么简单?”
“说得简单而已。时空穿行哪有那么容易,需要将魔手的力量恰当地集中在一个点上,确定好目的地,确定好到达的时间和位置,假如出了一点差错,那么很有可能会被抛到黑暗的未知空间里去,再也回不来。而且时空穿行是有一定原则的,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影响所去时代的历史。所谓的蝴蝶效应一定要注意,比如我到达18世纪的俄国,可能降落的时候碰碎了一个花瓶,花瓶的碎片扎伤了一个小孩的脚,导致化脓腐烂,必须截肢,而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却是一个出色的情报员。这事情的后果就是俄国军队在滑铁卢战役中失去了重要情报,因此败给了拿破仑。这就是影响到了历史。所以在穿行之前,必须计算清楚,千丝万缕都要估量好,一丝一毫也不能出差错,正如同在历史的夹缝中穿行。”
我说:“那么您这次去,要去什么地方?”
“还说不好。魔手的力量终归是要用于音乐,所以我的时空旅行也就是在各个时代之间穿行,假如某个时代缺少一双魔手,我会把魔手留在那里,造就一个音乐天才,使人类的历史不再贫乏。就像播种机一样,我将走过九个时代,进入九种不同的人类文明,将魔手赠与他们。我曾经说过,这才是魔手的真正用途。魔手将永存于人类的音乐中,而不应该用于其它任何目的。”
()
20魔手终结与动物般女孩的消失(3)
“那么您将魔手放出去以后,如果异乡人再去抢夺怎么办?不知道别的时代有没有异乡人?”
“异乡人这种角色,据我所知在别的时代没有,只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我在远古留下的魔手流传到现代,当然有可能被异乡人抢走,但我还会将它们夺回来。这是我的工作,可能就在夺走与抢回的周而复始之中,我维持了人类历史的平衡,也就是音乐和暴力的平衡。”
我说:“那您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培养艺术家这事儿好像归文联管。”
“我当然自有我的目的,”他说,“只不过现在告诉你还是为时过早。尽管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但依然是为时过早。仅从人类的角度看来,让历史有声有响,不也是一件好事么?”
“这个当然。”我想了想说。没有音乐,地球大概照转无误,不过每个零件——人类、动物、植物甚至山川河流——都会转得异常乏味。
“所以嘛,新的魔手之旅总要出发,把音乐带到蛮荒之地,终归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拉赫玛尼诺夫说着托起手中的金属杯,像鉴赏古玩一样长久凝视。那杯子一尺多高,是个规则的圆柱体,看起来重量非常大,杯壁异常厚实,任凭什么力量也别想穿透。他看着杯子的时候,身体被蓝光笼罩,眉头紧锁,嘴唇轻轻闭上,仿佛正在思考一项复杂的问题。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运算。拉赫玛尼诺夫和魔手即将离开这个时代。
但就在这时,动物般的女孩忽然攥紧了我的手。她手心发亮,胳膊不停颤抖。我听到大地深处传来一声唿哨,悠长而又遥远,不紧不慢地掠过杂草。我们身边的草丛里站起几个人来,他们不像是躲在草里的,而像是直接从地底长出来的,就如同传说中的龙牙武士一般。
而站起来的人正是棕色皮肤的姑娘。异乡人再次造访。
她和那个小伙子站在草丛里,眼睛闪闪发亮,看来伤势已经痊愈。我正诧异于只有他们两个人来,却感到不远处有什么东西正在随着风上升。动物般的女孩叫声不好,我仰头环顾,看到空中漂浮着八个人的身体。他们和那天的秃顶老头一样,身体急剧膨胀,就像一战时期欧陆上空的齐柏林飞艇,君临天空,威慑地面。
“钢琴师,”棕色皮肤的姑娘道,“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魔手不要带走。”
拉赫玛尼诺夫闭着眼睛,没有说话,但身体依然被蓝光覆盖。
“否则的话,你将永远留在这片牧场上,哪儿也去不了。”棕色皮肤的姑娘继续说道,她停了一停,等着拉赫玛尼诺夫开口。
“据我所知,”拉赫玛尼诺夫睁开眼睛说道,“异乡人在地球上为数不多,而每用一次血咒,都会有一个牺牲生命。”
“即便只剩下一个,也必须和魔手融为一体。”棕色皮肤的姑娘道。
拉赫玛尼诺夫不动声色地说:“那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不要再和我讨价还价。”
“也好。”棕色皮肤的姑娘说着向天空挥了挥手。血液从四面八方喷涌下来,而且如同高压水枪一般,速度极快,力道极大。
动物般的女孩立刻拉上我,跳到拉赫玛尼诺夫身边,他用蓝光将我们一齐笼罩起来。血液射到蓝光上立刻弹回,在我们脚下汇成河流。被血溅上的草立刻枯萎,变成了一团黑灰。随着血液的冲刷,蓝光越变越弱,但拉赫玛尼诺夫睁大眼睛,振奋起来,又将血液挡了回去。
“这就是魔手的力量。”棕色皮肤的姑娘赞叹道,“异乡人的血流得值得。”
天空中涌下来的血越来越多,似乎又有不少异乡人变成飞艇,飘了上去。
“异乡人这次是要倾巢而出了。”拉赫玛尼诺夫道。
棕色的皮肤的姑娘忽然又打了个唿哨,空中的异乡人忽然暂时停止了喷血。他们调整了一下队形,陡然间将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