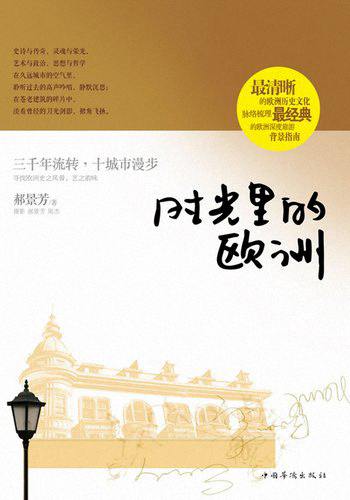b小调旧时光-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拉赫玛尼诺夫轻轻耸着肩膀,无声地打开钢琴盖,手指轻轻弹出《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中的舒缓段落,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正是被段音乐贯穿始终。“那么你相信不相信音乐能穿越时空?”他边弹问我说。
“这个我自然相信,因为有唱片存在么。在您的晚年,录音技术已经很发达了,因此在您死后,美国留下了大量您亲手弹奏的珍版。比如说一套名为《拉赫玛尼诺夫弹奏拉赫马尼诺夫》的唱片,《第二钢琴协奏曲》就是我在那里面听到的,虽然是单声道录音,但是原汁原味。”我说。在说后半截话的时候,荒诞感越来越强烈。
“这不就结了么。”拉赫玛尼诺夫潇洒地弹出一组高音,“所以穿越时空也不是不可能么。”
“就像常说的‘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音乐虽然能穿越时空,但音乐家毕竟还是人,人都是要死的,您怎么能在此时此地冒出来吓唬我呢?”
“这也不能怪我嘛。”拉赫玛尼诺夫带着讽刺的歉意说道。
“那是,确实也不能怪您。”除了说这个,我无话可说了。
“我何以能在此处出现,何以偏偏出现在你的面前,个中原因实际上很复杂,以后我再慢慢给你解释吧。”拉赫玛尼诺夫停止弹奏,在似有似无的余音中说道。
“这么说我还得在荒诞的感觉里生活一段时间。”
“习惯了就不觉得荒诞了。”他说的这句话倒是真理,因为近期的生活就是如此。但他接着又说道:“还有更多的荒诞等着你去习惯呢。”
“我穿越时空的‘荒诞’旅行,说得简单些,实际上就是以音乐作为向导的。”夜色完全深沉下来,对面楼里的灯光已经近乎完全熄灭,从窗户里往下看去,路灯也一盏不剩,大地如同无底深渊般漆黑。此时已经换作了我坐在钢琴前,伴奏般地弹着拉赫玛尼诺夫的即兴小品,而拉赫玛尼诺夫本人则坐在床上与我交谈,间歇性地就琴技指导我两句。
9魔手(2)
他说道:“我只能出现在某些能弹奏我作品的人身边,或者不弹我的,能弹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高沙科夫等人的也行,总之必须得是俄罗斯音乐。”
由于乐曲早已烂熟于心,我得以像他一样一边弹琴一边说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十月革命后,您虽去国离乡,但仍无法忘却俄罗斯情结,所以即使穿越时空也会追寻着俄罗斯音乐而行?这个思路是不是太像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了?”
“很多问题都是这样:随你怎么理解都可以,否则你就无法理解。如果我告诉你,实际原因是一种心灵感应,你岂不又该觉得荒诞了么?”他说。
我叹口气:“那也没关系,眼下的事情难道不就是荒诞么?再多点也无所谓了。”
“实际上,在时空之旅的路程上,我并不仅仅在你这里停留。你这里不是目的地,你也不是我惟一要找的人。大约在你们意义上的‘四十多年以前’,我还在北京停留过一次,但那一次过于投入,造成的后果差点儿把我给毁了,所以这次要格外谨慎。”
“什么意思?过于投入是指什么?差点儿毁了是指是什么?大概您就是在那时候学会北京话的吧?”
“北京话当然是那时学会的,因为那次停留的时间格外长,就连身份都改变了。至于‘投入’和‘毁了’指的是什么,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也就是说,我注定在荒诞的处境里浸泡一段时间,连层层揭开面纱的权利也没有。我岔开话题道:“那时的北京是什么样的?”
“冬天吃大白菜,夏天吃小豆冰棍。据我所知,你倒觉得那时的生活更具有美感?”
“大概是这样,不过真的活在那时,也许美感就会消失了。”
“确实是有美感。”拉赫玛尼诺夫微微抬起头看着房间半空,做出追忆年华的神态。一个随意穿梭时空的人也会追忆年华,他所追忆的感受是否和我们一样?
“对了。”经过长时间相处,我些许轻松了,恢复了开玩笑的能力:“那么你也还会说俄语吧?说一段儿我听听——说不出来我可认为你是假的哟。”
“说什么?”
拉赫玛尼诺夫眨巴眨巴眼睛,布噜布噜地说了一段,结尾处还加上一句“乌拉”,说完以后道:“在我观察过的人里,还没人像你这么无聊。”
()好看的txt电子书
我感到些许愉快,轻快地弹完了一段乐曲,问他:“我弹得怎么样,大师评价评价。”
他随意指出了几处力道不对和节奏上的纰漏,然后说:“实际上也没什么可以指点的。每个音都很准确,每个小节都很清楚。”说着让我把手拿开,他自己弹了一段我刚才弹过的乐曲。这时我明白,所谓“没什么可以指点”也就是“差距太大,无法指点了”。我的每个音都是照着乐谱一丝不苟弹的,接近于分毫不差,但弹出的每个音在拉赫玛尼诺夫都是错的。在“准确弹出乐谱”与“弹出拉赫玛尼诺夫的神髓”之间存在着天渊之别的鸿沟,而那却不是可以依靠人力跨越的。一瞬之间我想起黑哥,甚至嫉妒起来,他在吉他上做到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我弹的只是乐谱而不是音乐。”我说。
“能看到这一点,已经远远高于一般人了。”
“那么如何才能弹出您这样的美感呢?就拿您的作品为例而言。”
“前提只有一个,忘掉那是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
“对于您来说,也就是忘掉自己就是拉赫玛尼诺夫本人?”
“可以这样理解,对于一般人来说,也就是忘掉生命本身。但说谁都能说出来,真正做到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想到自己曾经将钢琴确立为理想,不免悲伤起来,同时于心不甘:“假如说我一定要做到,那么如何才能呢?”
“需要一样东西,也就是魔手。”
“什么是魔手?”我问他。
“所谓魔手,并不是再往身体上安两只手——”他慢悠悠地说。
9魔手(3)
“我也没那么理解,手太多了那是哪吒。您别卖关子了行么?”我打断他道。
“魔手实际上是一种不具有具体形态的存在物,但又不是纯粹抽象的理念。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气质或者一种感觉,也就是使人和音乐融为一体的能力。”
“那么说来,您、鲁宾斯坦、帕格尼尼这些人都是拥有魔手的了?”
“不能说‘拥有魔手’,而是魔手附身。魔手不是人通过刻苦练习形成的,而是外在于人体,客观存在于世界之上。如果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成立的话,魔手也许是一种能量场。”
我想像着空气中漂浮着被称为“魔手”的无色、无形、无声的物质,当某位幸运儿被它附身,即可变成拉赫玛尼诺夫、鲁宾斯坦和帕格尼尼这样的天才。如果这话是真的,那么整部音乐史都将被改写,而变成《对魔手无规则运动的研究》。在所有音乐家中,也许莫扎特是最早被魔手青睐的,可以推测,他还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魔手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入他母亲的身体找上门来。
“然而魔手并不是无限多的。魔手有着具体数量,而且相当少。否则的话,伟大的音乐家就将满地都是了。”拉赫玛尼诺夫继续说道,“有限的魔手在不同人之间转移,在有的人身上停留得短,在有的人身上停留得长,在有的人身上毕生停留,可以说与附主融为一体,直到附主死去,才另找归宿。仅在某些人身上停留一时半刻,这也就是许多天才的艺术寿命难以为继的原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被称为‘俄罗斯音乐之父’的格林卡。”
格林卡比柴可夫斯基时代略早,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他拥有可以与普希金相提并论的地位,是俄罗斯音乐崛起的先锋军。但他还停留在贵族的玩票阶段,作品也大多良莠不齐,有些令人惊叹,有些则让人大倒胃口,“我很难相信,这些东西居然是格林卡这个天才写出来的。”柴可夫斯基也曾皱着眉头评论道。
我问拉赫玛尼诺夫:“那么如何才能使魔手附着在身上呢?”
“魔手作为外来的寄生体,势必与人内部原有的‘自我’排斥,所以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彻底忘掉一切私心杂念。”他说。
“说来说去,还是没有别的办法。”我说,
“我没说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只不过将其中的机理解释清楚。所以在神学的范畴里来讲,音乐家都是浮士德,用自我灵魂去换取天才。”
面前的拉赫玛尼诺夫一直沉默、冷静,说话滔滔不绝,语音不高不低,语速不缓不快,使人感到他所说的完全是客观叙述,不含有恐吓人心的成分。我却因此感到困倦,有些敷衍地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说了这么半天魔手,我还是不知道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魔手是从哪儿来,如何形成的呢?是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就有还是在某一个地方产生的?”
“这个现在也不能告诉你。能告诉你的只是,目前有一些魔手飘散出来,流落在世界之上。我此行的一个目的就是探访这些魔手的流向。魔手数量有限,必须善加利用。但这只是目的之一。”拉赫玛尼诺夫不动声色地说道,然后心照不宣地点了一下头。
我像接到许可一样,睡意铺天盖地涌来,转瞬趴倒在琴键上睡着了。睡之前,几个念头滑过脑海:假如说魔手“流落在世界之上”,那么它们在此之前应该处于某些人的控制之下,眼前的拉赫玛尼诺夫也许就是控制魔手的人;今天造访的拉赫玛尼诺夫绝对不是通常意义所谓的拉赫玛尼诺夫,但也不应该因此否定他的身份,也许拉赫玛尼诺夫确实具有世人所不知晓的另一面也未可知;以我的经验,黑哥应该是魔手附身的人,但拉赫玛尼诺夫为什么要找到我呢?难道仅仅以我奏出的东欧音乐作为时空穿行的着陆点么?还有,他说寻找魔手只是目的之一,那么我是否与他的其他目的有关?
最主要的是,我依然心存狐疑,对今天看到听到的一切都心存狐疑。没有人会轻易相信这些东西,不过这个时代的人除了一般等价物以外也不会再相信什么了。我是否真的见到了拉赫玛尼诺夫,真的与他边弹钢琴边谈话来着?或者说我一直就在屋里睡着,方才所见只是梦境?
9魔手(4)
随后我意识到,真正的梦境开始了,或云我从一个梦境进入了另一个梦境:动物般的女孩走近我屋里,我已然记不清她的面容,但确信是她。动物般的眼睛、表情和姿态毕现无遗,我们一面默默接吻一面四手联弹。我把脸埋在她的胸前,清晰地吻着她Ru房上的每一道褶子。
书包 网 想看书来
10网(1)
次日清晨,阳光明媚得嗡嗡有声,窗外的灰砖楼、白杨树和自行车棚的绿帽子被照得纤毫毕现。我趴在钢琴上睁眼醒来,刚一欠起身,钢琴键盘便杂乱无章地想了一通。昨晚我不知不觉就趴在琴键上睡着了,但却不记得趴倒时听到震耳欲聋的巨大和弦。我活动活动上肢,找出一颗烟点上,环顾房间。
钢琴、桌子、木椅、木床、两个暖壶。除了毛巾和散落在墙角的啤酒瓶子以外,全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产物。木椅上漆着“师范大学教”的字样,木床床头早已被摸得像瓷器一样光滑。就连楼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