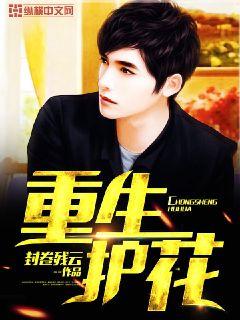重生之媚授魂与-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午,三夫人娘家人便过来了,与太夫人赔不是。
而下午,三夫人拖着虚弱不堪的身子,由她母亲陪着回来了,向太夫人下跪认错,哭了半晌才回了房里。
这一次,三夫人把自己和娘家都害得不轻。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叶昔昭去太夫人房里的中途,分析着三夫人的性情,再想到吴妈妈的提醒,猜测三夫人极可能会将自身遭遇的罪责推到她身上,心怀怨恨。
有时候,有些人无法面对、承认的就是自作孽自讨苦吃,会下意识的把责任推给别人,却不肯反思追究自己有无过错。三夫人是这种人,往昔她与父兄亦是。
思及此,叶昔昭吩咐了新竹一番:“让房里的都记住,日后何事都要与三夫人撇清关系。”沉吟片刻,又补充道,“相安无事即可,若是有人找茬,不予理会,及时知会我。”
太夫人信奉家和万事兴的道理,若是正房总与三夫人那边摩擦不断,时日久了,两房的人都会惹得太夫人嫌弃。
“奴婢谨记。”新竹应下后又道,“芷兰去命人照方抓药了,回去后奴婢便跟她细说。”
叶昔昭笑了,“对,芷兰高兴的时候是伶牙俐齿,不高兴的时候是牙尖嘴利,闲时多劝她改改这性子。”
新竹噗嗤一声笑,“那是自然,奴婢少不得劝她。”
到了太夫人房里,恰逢虞绍桓出门。他神色很是落寞,勉强扯出一抹笑,寒暄几句离开。
整件事,受伤最重的就是他了。前一日兴许还在憧憬孩子出生后的情形,今日就变成了这般情形,换了谁也承受不了这种落差。
太夫人坐在大炕上,神色难掩疲倦,见到叶昔昭,强打起精神问道:“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宾客众多,午间晚间都要设宴款待,你们该帮忙待客才是。”
叶昔昭恭声道:“侯爷本该在家静养,不宜整日忙碌,况且府中又有事。”随即谈及贺礼之事,不安地道,“儿媳事先也不知贺礼如此贵重,便带了去……”
太夫人摆手笑道:“这是绍衡的主意,那是他与友人打赌赢来的,赠予相爷再合适不过。你也不是不知道,他们兄弟三个对风雅之物不看重,不定哪日便会随手丢给谁,绍筠就更别提了……”说到女儿,她便是头疼不已,不自觉地岔开了话题,“我总疑心她投错了胎,竟比男孩子还顽劣。”
虞绍筠是虞绍衡四妹,自幼跟着三个兄长习文练武,聪慧狡黠。一年前,这大小姐在及笄之后,反倒越发的顽劣,不时溜出府去,屡次与人比试,被她打的起不得身的名门子弟就有好几个。
眼看着虞绍筠就要变成祸根,且很有惹下一堆恶名嫁不出去的危险,再加上虞绍衡又因政务繁忙无暇管教,太夫人狠了狠心,让虞绍衡寻了个身在外地的严师,把虞绍筠送出了京城。
叶昔昭心知太夫人就是再头疼,也是百般思念女儿,笑道,“绍筠去外面也有一年了,太夫人命人去把她接回京城吧?”
“嗯,倒是听说如今文静了几分。”太夫人笑眯眯的,“等端午前后就让她回来。绍衡不似往日那般没日没夜的忙了,也有时间帮我管教她了。”
“这再好不过。”
继而,太夫人言简意赅地说了三夫人的事,“好生将养几日再回府也不迟,却这么急切地回来认错,哭哭啼啼半晌,若是落下了病根儿,算是谁的不是?”
叶昔昭说什么都不大妥当,便没接话。
末了,太夫人道:“今日都不得清闲,丫鬟之事,明日给你指派。晚间你们就别过来了,我着实乏了,稍后歇下,不知何时才会醒。”
“是。太夫人好生歇息。”叶昔昭告退。
回到房里,叶昔昭取出从相府带回的诗集,送到虞绍衡面前,“从相府带回的,侯爷看看?”
这诗集里面,有些字眼在别有用心之人看来是犯上之意。在前世,这是叶舒玄罪名之一。
虞绍衡倚着床头,微眯了眸子,翻阅时,指关节一直揉着眉心额头。
“头疼?”
“嗯。”虞绍衡看着书页上的字迹。
叶昔昭去搬了把椅子到床前,又让虞绍衡横躺在床上。
虞绍衡会意一笑,“别累着。”
“举手之劳罢了。”叶昔昭手指按揉着他头部一些穴位,“小时候每次头疼,父亲总是如此照顾,久而久之,也就记住了。”
虞绍衡到何时也承认,叶舒玄很疼爱儿女,只是在有些事情上方式欠妥,笑了笑,道:“是叶相笔迹,字里行间却不似他性情,是抄录还是旧作?”
叶昔昭没说实话,“就是不知道这一点,又没问出结果,才让侯爷过目。”
“我好好看看。”
“不急,不舒服就先歇息。”他愿意看就好。叶昔昭将诗集放到一旁,问出心中疑惑,“今日那名女郎中,侯爷是从哪里寻到的?是天生口不能言么?”
作者有话要说:
☆、原来如此
虞绍衡告诉她女郎中的底细:“那是我友人亲眷,医术不错,却不常为人医治,你也就无从听说。是否天生不能言语,倒是没问过。”
叶昔昭听得女郎中的由来,猜想“民女”二字是否只是谦辞。因着他道出的友人二字,念及兰竹图由来,不经意岔开话题:“听太夫人说了贺礼从何而得,真是想不出侯爷与友人的赌约是什么。”
“……”虞绍衡不接话,呼吸转为匀净。
须臾间就能入梦?叶昔昭才不相信。这厮就是喝成醉猫,也不可能如此。“侯爷。”她手上加了点力道。
“……”虞绍衡继续装睡。
原本叶昔昭不过随口一说,可他这样子反倒引得她有了强烈的好奇心,又抬手推他肩头,“侯爷说说又怎么了?”
虞绍衡装不下去了,勾唇轻笑,却道:“冷了。”
叶昔昭明知他这是缓兵之计,还是脱掉绣鞋上了床,去给他拉开一条锦被盖上。
虞绍衡顺势把她勾倒在身侧,“头不疼了,跟我躺会儿。抓药的人得过些时候才能回来。”
“……”叶昔昭被强行安置在他怀里,不满地看住他。
虞绍衡忙着将她头饰去掉,末了又吻了吻她眼睑,“快睡会儿,脸色真差。”
叶昔昭被这种逃避问话的方式引得笑了,“心存疑惑,怎能入睡。”
虞绍衡只好道出实情:“你不会愿意知道,不说是不想骗你。”
叶昔昭揶揄道:“便是有心骗,一时间也编不出合情合理的理由,不能自圆其说,对么?”
虞绍衡理亏地笑笑,“这么说也可。”
叶昔昭扯扯嘴角,“但这让人愈发好奇了,怎么办?”
虞绍衡想了想,告诉了她事情梗概:“我与友人赌的是一件事,历时几年方能分出胜负,是以,那幅画只是赌注之一。那时候少不更事,否则怎会有这等行径。”
叶昔昭听这话,想着应是关乎他几年前程,也就没再细究,目光微闪,笑了起来,“真担心侯爷的友人已倾家荡产。”
虞绍衡逸出清朗笑声,“不至于。”
又说笑了一阵,两个人睡了一觉。芷兰轻声询问叶昔昭要不要用饭的时候,夫妻两个醒来,方觉天色已晚。
唤人摆饭前,芷兰先端给叶昔昭一碗颜色深浓的药,“方子上写着,要在饭前服用,已经晾了些时候。”
叶昔昭接过,一口气喝完。
芷兰又奉上一杯水。
虞绍衡看着妻子服药的情形,想起了妹妹虞绍筠,“绍筠每次生病服药前,丫鬟都要给她摆上一堆糖果甜食。便是如此,还要磨蹭半晌。平日里无法无天,其实没出息得很。”
叶昔昭轻笑,“因人而异。”叶昔寒一个大男人,生平最怕的事,也是服药。这完全就是没道理可讲的事情。
饭前服药的一个弊端,是无法如常用饭。胃里有一碗药打底,哪里还能吃多少东西。这引得虞绍衡有点头疼,“左右都不是好,总这样,你不是更虚弱了?”
叶昔昭倒是不在意,“午间不需服药,多吃些就是了。”
“你总有话说。”虞绍衡打趣一句,又吩咐下去,命小厨房里的人每日精心准备些养胃的饭菜。是药三分毒,药材性子就是再柔和,也会伤胃。
晚间,叶昔昭早早睡下了。虞绍衡则借着床头灯光翻阅诗集,与叶舒玄有关的一切,是他必须去了解的。
有些诗与唐鸿笑风格相仿,辞藻华丽,却非伤春悲秋,看了赏心悦目。有些则是为了铭记一些际遇而作。细细回忆了解到的叶舒玄生平诸事,有不少能与他年轻时遭遇对上。
由此,虞绍衡确信这本诗集是出自叶舒玄之手。沉思片刻,准备把诗集放到书房,沉下心来看上几遍。
一夜无话。
翌日早间,叶昔昭与二夫人去请安的时候,太夫人把夏荷和两名小丫鬟唤进房里,问道:“将这三人派去正房如何?”
叶昔昭与二夫人皆是一愣。
任谁也不会想到,太夫人会将她最看重的夏荷指派给叶昔昭。
夏荷笑盈盈到了叶昔昭面前,屈膝行礼,“夫人不会嫌弃奴婢粗手笨脚吧?”
“怎么会。”叶昔昭不安笑道:“你是服侍太夫人已久的大丫鬟,若能到我房里,自然是我的福气。”随即看向太夫人,如实道,“儿媳实在是受宠若惊,可是……实在是不知说什么才好了。”
太夫人呵呵地笑起来,“我明白,明白。这是我思量几日才选出来的人,你只管安心收下。”她明白的是叶昔昭的喜悦和顾虑,喜在她的看重,顾虑的是她少了夏荷会不会不习惯——这一点又不能说出,说了怕被误解是不想要夏荷。
“多谢太夫人。”叶昔昭恭敬施礼道谢。
二夫人则笑道:“早知人手不够,便能换得太夫人房里的大丫鬟,儿媳早就将院子里的下人全部打发走了。”又对叶昔昭说道,“大嫂,我可是自心底眼红你的好福气。”
这话引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太夫人应道:“哪日你人手不够了,我房里的人由着你挑。”
二夫人笑着道谢,随即还是开玩笑,“那儿媳回去就开始盘查下人有无过失。”
叶昔昭笑望向二夫人,目光流露着欣赏。这女子甚是聪慧,若是换了三夫人,今日势必会闹得不欢而散。
之后,叶昔昭要回去给夏荷安排住处。夏荷与两名小丫鬟要着手收拾随身之物,第二日去往正房。
叶昔昭与二夫人同时告退出门,之后笑道:“二弟妹去看过三弟妹了么?”
“没有,正要问大嫂是什么意思呢。不同午后我们同去?”
叶昔昭本就是这心思,愉快应道:“好啊。”有些场面功夫,还是要做的。她们两个若是对三夫人不闻不问,总不是那么回事。
而此时的夏荷则被太夫人唤到近前,叮嘱道:“要你过去,一来是把你看到学到的持家之道慢慢教给昔昭,也不要做得太明显;二来呢,夫妻两个若是有了什么嫌隙,你从中周旋着,多劝着她一些。”
“奴婢谨记。”夏荷的声音有些哽咽,“奴婢真是舍不得太夫人。”
“这是什么话,又不是不再见面了。”太夫人笑道,“你们这些孩子,只要是我看重的、知错就改的,我就会给她一份好前程。我毕竟已上了年岁,日后当家做主的,是绍衡的发妻。你还年轻,在正房尽心尽力,才有希望一生无忧。”
感动之下,夏荷落了泪,“奴婢知道太夫人的苦心。”
“你也不必担心别的。退一万步讲,昔昭若是又变回往日的样子,我再把你唤回来就是。”太夫人抬手,帮夏荷拭去泪水,“高高兴兴地去。若无大事,不需知会我,你从今日开始就是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