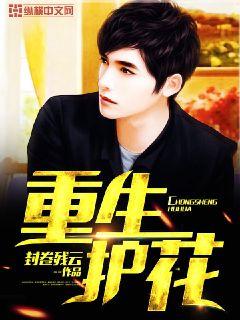重生之庶女归来-第18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柏炀柏研究了一下何当归的表情,突然抬手挖鼻孔说:“俺不信你有这么狠心,方才你还为俺掉眼泪呢,你放心,你们俩的机密谈话贫道真的没听见几句,这里的河水哗啦啦的响,毛也听不清楚。贫道只听见你又拿问过段小子的问题去问他,你们还讨论了一下生孩子的问题,旁的真没听到多少,不信你运功听听那边的竹林,你能听到那边的人说话吗?”柏炀柏指了指被钱牡丹吓进竹林的一群人。
何当归侧耳倾听,果然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字句传进耳朵里,得不到什么连贯的信息,所以姑且相信了柏炀柏的说辞。孟瑄的耳力那样好,连几百丈外的脚步和喘气声都能分出来,他自然能听出近前几十丈有无他人的呼吸声。再说了,带着上一世的记忆在自己多年以前的身体中苏醒过来,这种事情除非亲身经历上一次,否则就是说破天也不会有人相信的。
柏炀柏小心地捅一捅何当归,分辩道:“女大王,我没说错吧,我只是想趴在这里看看你们究竟进展到哪种程度了,让那个孟小子那么自信满满的送一本‘孟家刑罚大典’给你当聘礼,结果等到最后也没看到什么好料。啧,这个孟小子真是个大爷们,给咱们所有男人长脸了,段小子对你的无礼要求起码还考虑一下,再跟你好声好气的商量,讨价还价一番;人家孟小子却张口就回绝了你,人家的意思很清楚,他再喜欢你也白搭,你的要求根本不现实。这回你该醒悟了吧,丫头,就算你是个天仙,也不可能有哪个贵公子只娶你一个,天上的仙女下了凡,找的也是孝子董永而不是豪门公子!喂,你的针上没有毒吧?”
何当归嗤了一声:“当然有毒了,没毒我扎你干嘛。”
“有毒!呀,那你快把上次你打晕钱牡丹给她吃的那种药丸给我吃两丸!”柏炀柏摇晃着她的胳膊,恳求道,“好师父,快救我!我不要变成钱牡丹那个样,她是没死透啊还是诈尸啊,吓得贫道小心肝都僵住了,都记不清段小子哪一天来扬州参加武林大会了。”
☆、第173章 五花马千金裘
何当归一脚踢在柏炀柏的小腿上,将之踢得鬼哭狼嚎,她咬牙切齿地说:“好你个柏炀柏,亏我将你当成个数三数四的好朋友,平时想找你帮忙时见不着你尊面,在我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你不光不施以援手,还在一旁冷嘲热讽。最最可恨的是,你已得知了段公子最近的种种不如意,又成日在我周围晃荡,你居然不告诉我这一切,让我从头至尾都被蒙在鼓里,还傻傻跑去问段公子的同僚他的近况,平白挨了一顿排头。你就等着毒发身亡吧,潜君兄,等你亡故之后,我会在你的遗物里好好翻一翻的。”
柏炀柏连连作揖告饶:“师父容禀,我只是两三个月前去过一回京城,顺便逛了逛段府,见那死心眼儿的段小子还惦记着你,我就去规劝了他一番,那时候他老父尚健在,还冲我点头一笑呢,我也不知后来段府发生了那么多人间悲剧,又如何讲给你听呢?”
“真的?”何当归将信将疑。
“比真金还真!”柏炀柏用力点头说,“至于说到在你的危急时刻,我却作壁上观,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让那个中年美妇孙氏给欺负了,贫道不是帮你去偷看她洗澡,破坏她的名节了吗,对一名女子而言,还有什么比名节更珍贵的东西呢?比如孟小子仗着亲过你,语气里俨然以你的丈夫自居,不就是吃定了你清白已失,好了歹了都是只能嫁他一个人,对你提出的要求完全不予以考虑呀,人家!后悔了吧你,自己先跌了份儿,说什么都迟了,这一回你也欠考虑,这些无理要求应该在你们共赴巫山之前谈判才有用。”
何当归举起梅花小针想治一治他嘴贱的毛病,柏炀柏又是一阵连连作揖,双手奉上孟瑄的匕首说:“女师父息怒,那个毒针岂是能拿来乱玩的,还是用刀吧,我刚才试过了这柄匕首,切地上的青石板跟切豆腐差不多。”
何当归从善如流的收起了小针,接过匕首举到柏炀柏眼前,冷笑道:“既然你见识了这把刀的威力,旁的废言我亦不愿多讲,为了你的耳朵鼻子和手指头着想,你速速道来段公子赴扬一事的始末,他来参加武林大会做什么,他又不是江湖中人,难道是带着官兵来搅局的?他哪一天到扬州,在何处下榻?你的消息从何而来?”
柏炀柏神气地叉腰一笑:“吼吼,就是因为此刀威力无穷,所以我笃定师父你这样菩萨心肠的人连近都不敢近我,更不用说削我耳朵了,是不是师父?其实贫道开价也不高,掰着手指头算,从现在开始贫道每说一句话一两银子,五十两银子付账一回,如何?”
何当归掂一下自己的荷包,只有不到二十两碎银,也就是说只能买他的二十句话,顿时满心不悦道:“你在京城不是有皇帝赐你的大宅子吗?听说里面奇珍异宝无数,五花马,千金裘,香车宝马加美人,你简直是富豪中的败类,败类中的富豪,还好意思跟我一个小女孩伸手要钱,你羞愧不羞愧!”
毫不羞愧的柏炀柏吹着口哨,哼着小曲,眼睛直瞄着何当归的荷包。何当归冷着脸摘下递给他,还价说:“这些钱买你一晚上的话,不够下次添上,从现在开始你要对我百依百顺,问一答十,举一反三,听见了没有?”
“得,没想到贫道竟如此廉价,”柏炀柏把荷包里的碎银一股脑儿倒走,把荷包和扇坠完璧归赵,不情愿地嘟着嘴巴说,“贫道去中书省门口摆摊要上几个时辰的饭,赚的也不止这个数。下次去你闺房的暗格里把段小子的十几封情书偷走,卖给你‘未婚夫君’孟小子,至少能弄个一千两银子花花。”
何当归气急败坏地将匕首重新换成了小针,遥指着他的鼻子,寒声喝道:“你竟然敢偷看我的私人信件,柏炀柏你这个老无赖,这些年来你竟然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你就等着毒发身亡——”
话至中半的时候,柏炀柏忽而将她扑倒,百十斤大山一样的压过来。她正要张口斥骂,他的唇居然直压了下来,触上了她的唇瓣,虽然只有电闪一瞬就飞速挪开了,还是把何当归唬得不轻。下一刻,一个黑衣老妇从远处蒿草丛的方向奔过来,途径他们身边时瞧也未多瞧上一眼,就径直往场地上糟乱的人群里奔去了。
待黑衣老妇跑远之后,柏炀柏立刻翻身落在一旁的草地上,不等何当归开口说话,他先自辩清白道:“我不是故意的真不是故意的,扑倒你的时候你的针扎了我的胳膊了,而且我的嘴巴上带着一层假皮,所以你只是亲到我的皮,这个什么都不算,行不行?”说着真从自己嘴唇上揭下两层皮来,他的唇色立刻就由暗红色变成了樱红色,因为揭得太急,所以连下巴的部分也被揭掉一些,夜风一吹,他下巴上的一片异物随风上下摆动,看起来比钱牡丹的诈尸一幕更加诡异。
柏炀柏见何当归一直盯着自己的下巴看,索性就从下巴处开始连揭带撕,将自己的一张艺术品一般仿真的“李郎中的脸”给撕坏了。
柏炀柏笑嘻嘻地说:“明天还是去你院子里给你洗衣服吧,这书院门口卖药糖的活计太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一个月下来才赚五两银子不包吃喝。而且把钱牡丹医成了那副鬼样子,我也不好意思待在澄煦门口了,她爹爹悲愤之下,找不到元凶,又惹不起刚才给治病的孟瑄公子,肯定先拿我这个草民开刀。”
他说着这番话时,已经从一个白胡须老头,渐渐变成一个看上去跟孟瑄和彭渐年龄差相仿佛的少年郎,虽然容貌不及孟瑄的俊美无俦,也没有彭渐的英姿勃发,却是说不出的让人感觉亲切,仿佛春风拂面一般的惬意。因为常年照不见阳光,他的面色有一种病态的白,可一双清亮而灵活的眼睛却是生机勃勃,与他的白肤病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远山眉,丹凤目,挺鼻樱唇,好一个亦庄亦谐,如风如露的道圣柏炀柏,谁能想到他如今已经三十有五,谁又能不对他的驻颜之法产生强烈的探索欲望,何当归前世足足探了他五六年,今世又缠了他将近一年,可如今仍对那个传说中的“驻颜汤浴秘方”一头雾水,甚至开始怀疑,他究竟有没有这种秘方。
何当归习医二十余载,前一世她幼年师从神针传人窦海溱,后回到罗家之后,也暗暗温习从前所学的医术,并且一边努力识字,一边想尽办法获得进入罗府藏书阁习读医书的机会,只因为她在自己的金锁中发现了外祖父罗杜仲的一封留书。
由于离开亲娘时只有四岁,所以她一开始不知道金锁中藏有机关,只要用针尖触动就可以开启。后来,跟着窦海溱老先生学针灸,她天天摆弄着几根针,看见什么东西都想上去扎两下练习手指的灵活性,有一天她就扎上了自己的长命金锁,只听“啪嗒”一声,金锁像开花一样分成了四小瓣。一瓣盛着小半匣研磨得极细的香料,一瓣盛着一捧银针,另外两瓣则是两大叠光滑鲜亮的白绸,极轻极薄,这就是她外祖父留给她的东西。
她虽是大户小姐,可眼界极窄,连棉布都甚少见到,更遑论这样漂亮的绸子。用纤细的手指揪出来之后,一张一张打开对着天上的太阳瞧了半晌,都是清一色的白绸,无花无字,只是每片绸的角落处都有外祖父的闲章——东郭山人,这是外祖父的自号,她还是有印象的。
她只道这是外祖父给自己的几块手帕,舍不得轻动就塞了回去,直到出了农庄跟母亲住一处的时候,享受上锦衣玉食的她才发现,原来大户人家小姐的手帕是一种很讲究的东西,有题花、纹饰、绣边和主人的小字,比如她的帕子通常会绣上“清逸”或“清绣”。不管手帕上的绣花出自哪一位绣娘的手艺,都可以署上她的名字,当成是她的作品,这是大家闺秀中不成文的规定,也是个小范围公开的秘密。
这些精美艺术品作用很大,除了宴会上许多的游戏场合,比如击鼓传花、接龙对诗和才艺表演等,可以拿着帕子向所有宾客展示自己的女红,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议亲时挑上一两幅最好的作品,用于给男方的母亲祖母等人观赏,作为评判这位小姐优劣的一项重要指标。毕竟公子们可以请画师多多给自己作画,再每个媒人处送上几张,把自己的音容笑貌传达到更多适婚小姐的眼前,而女子就不能这么开放大胆,除非是亲事已经敲定,才能赠自己的画像或小像给对方,因此小姐们手帕上那朵花儿的绣工和暗含的才情,就成了她们议亲时交出的一份重要答卷。
总而言之,见识浅薄的农家女何当归长到九岁时,才知道自己金锁中那几块漂亮的白绸布,跟传说中的“小姐的手帕”相差甚远,虽然没想明白外祖父去世前为何背着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母亲和外祖母,在自己的锁里塞了这么几块质地中下等的绸布——此时眼界大为开阔的何当归已得知,绸布色泽太亮就俗气了,只能作下品料子视之——不过,有意要完成自己人生第一幅绣品的她,拿了这些绸布浸在水中除尘,五六年不曾见过水的布料就显出了行行字迹来。原来,这是外祖父留给她的一封遗书。
绸布一共有九张,遇水显出字来的一共有六张,另外三张却是怎么泡都泡不出字来的空白绸子。
透过这一封“绸布遗书”,对外祖父的长相毫无印象的何当归却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