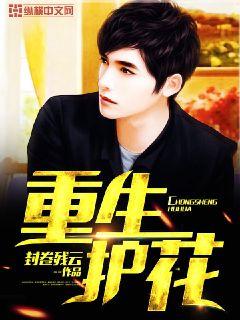重生之庶女归来-第17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年周菁兰对自己用逍遥蛊,除了想让自己体验极致的痛楚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死后不留伤痕和毒素,看起来就是自然死亡的样子。书上说,逍遥蛊顾名思义,中蛊活活痛死之后,死者的面容依然栩栩如生,和乐安详,让人根本想不到那人是刮骨剜心,活活痛死的,尸身还可以保持七七四十九天不坏,可是其人的魂魄俱销,连孤魂野鬼都做不成。
总的来讲,中逍遥蛊而死,是所有中蛊者中最“体面”的死法——这也是那本书上的一句话,直到今天晚上之前,她都是断断不肯相信的。不过,今夜看了钱牡丹的那种怖人惨状,她是不是应该感激周菁兰给了自己那种“体面”呢?不知道那一位高贵而重情义的夫君大人,有没有去瞻仰他昔日宠姬“栩栩如生,和乐安详”的遗容呢?有没有让人去井底,将他那个裹着襁褓、缠绕着长命锁的女儿的小小尸身打捞出来呢?
呵呵,“蛊”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呀,难怪世人都是谈蛊色变,不过再可怕的东西也只是一个东西,一件工具而已。最可怕的还是人心,东西可以在书本上一条一绺的描述得清楚详细,可是人心难测,再高明的相面识人的相士,最高不过国师齐经和其子齐玄余,他们也只能掐指算算人的前世今生,算算人这一生的坎坷,也不可能剖开人的心看看里面长了些什么样的毒草。
那些恶毒、傲慢、嫉恨、愤世嫉俗和一切负面情绪的毒草在心中攀爬,造就了耿炳秀、曹鸿瑞、何敬先、孙湄娘那种人,并把他们的毒草种子向世间播撒,让更多的人像他们一样长草……现在,她自己的心上有多少草了呢?步步为营的算计罗府二房之人也就罢了,眼前坐在她身边的那个少年,是她传道授业的小师父呀,她怎么可以为了让自己脱困,就用色相诱惑于他,骗着他救自己脱离苦海呢?
不行,不能再这样错下去了,否则就算有朝一日报了仇,她也会变成第二个孙湄娘,一生利用着她的丈夫罗川谷,一个她完全不爱的男人。
在水牢相会的那次,孙湄娘得意的向自己透露说,她年轻时也曾怀过一个罗川谷的儿子,不过因为何敬先的一封信,她就很激动地打掉了那个孩子,等着跟何敬先幽会,直到一个月之后才发现上当受骗了,那何敬先根本就没打算来见她……不过她也没有太多懊悔,反正她也是不太喜欢儿子的,长大也是跟罗川谷一样的窝囊废……
何当归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跟孟瑄说清楚,自己原本想利用他避开仇人,后来自己突然良心发现了,悬崖勒马了,不想去抓他的救生圈了。若是他肯原谅她,那他和她还可以继续做师徒做朋友;若是他无法原谅,从此不再理她,那她也认了,少背两三个心上的包袱,至少她的日子可以过得坦然一点。能及时幡然悔悟,不利用善良之人的善心,不牵累无辜之人,这才是自己跟孙湄娘最大的区别。
“柏炀柏,”孟瑄冷冷开口道,“以后盼你不要再开这等玩笑,也不要做春梦的时候,梦到一些不该梦见的人,否则我会让你以后都不能再继续开玩笑和做梦,现在,我跟小逸有一些两个人的‘夜半私语’要讲,你真的想听吗?”
柏炀柏激动地点点头,问何当归:“我能听吗?我嘴巴很严的!”
何当归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无所谓,事无不可对人言,她已经决定向孟瑄坦白了,既然要坦坦荡荡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就算有个把旁听者也无所谓。
孟瑄望着何当归那绝美的侧颜,将心头的话一股脑倾倒给她:“小逸,刚才就在这片林子里,你那么温顺的靠在我怀里,安安静静的让我搂着你,让我脱你的鞋袜,让我温暖你冰冷的身子,”柏炀柏之处响起了响亮的抽气声,孟瑄继续陈述事实,“你让我吻你的眼睛,让我吻你的唇,让我吻你的身子,”柏炀柏之处响起了被口水呛到的咳嗽声,孟瑄无视他之后,紧声质问道,“而你却说,你对我无一丝男女之情?那你对我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被我吻过了,你还想嫁给谁?我们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要说你跟我‘相交不深’,那你觉得怎样‘相交’才够深入呢?我不懂,小逸你教我。”
柏炀柏的双眸晶亮,咳嗽声震天响,又是甩手又是捶大腿,似乎孟瑄话语中暗藏的那些消息已经让他兴奋得手舞足蹈,忘乎所以了。而何当归咬着牙,反复地宽慰自己“事无不可对人言”,才能止住将柏炀柏一掌打到竹林深处的冲动,这家伙真是有够无聊。
柏炀柏席地而坐,从他的药箱中摸出一小盒瓜子,一边嗑一边冲孟瑄挤眼:“小子你厉害,我连做梦都还没梦到那个环节,而你竟然已经可以实实在在做到了,真是给我们男人争光呀,书院中的那群小子知道后还不气疯了。”
何当归将手中的匕首递还孟瑄,可他的双手都背在身后,于是她转而将匕首递给柏炀柏,说:“你先拿着点,等孟瑄走的时候还给他。”然后她面朝着竹林外的众人,在地上铺了一块手帕,刚要学柏炀柏那样席地而坐,孟瑄已在她的手帕上又加了一件他的叠整齐的外袍,口中道:“地上凉,仔细着了凉,回头还要吵着让我半夜去你房里给你驱寒。”柏炀柏玩着匕首,吹了一个响亮的口哨。
何当归当下也不客气地坐在上面,冷晒道:“孟瑄你不必刻意在柏炀柏的面前提这些,他的见证不会左右我的选择,就算再多十个旁观者,今日我也不能再将谎言继续下去。”
孟瑄也席地而坐,微微颔首道:“说吧,你骗了我什么了?我洗耳恭听。”
何当归侧耳倾听着远处河岸边众人的谈话,刚才有一段略去没听到,仿佛是钱牡丹的父亲钱袭也同意了砍手,可她的妹妹钱水仙仍然苦苦阻拦。
钱水仙泪流满面地说:“先生和各位有所不知,姐姐天性要强,追求完美,平时上学若是衣饰搭配不好,她怎么也要弄满意了才肯出门,以致我二人常常迟到。有一次京城传过来一种血玉制成的玉簪,听说是临安公主府上最先流行起来的,但因为血玉珍贵难得,在京城的玉石场切了一块三丈高的原石,统共就只得了几十斤血玉,被众玉石店掌柜哄抢一空。当时父亲也从京城高价购得一血玉玉簪,回家后给了姐姐,当时她戴上之后很开心,戴了一整夜,可第二天去书院时,她发现伍小姐竟然戴了一整套的血玉首饰,而且每一件成色都好于她的玉簪,于是她……”
她在拖延时间,何当归在心中这样默默道。伍毓莹也发现这一点:“都火烧眉毛的关键时刻了,你还扯那些闲篇作甚,我看你分明是想拖延时间,拖延到钱牡丹断气了你就开心了,钱水仙,你是何居心!”
看着嗫嚅答不上话的钱水仙,何当归却在心中想,下蛊之人至少不会是钱水仙,因为只要对蛊毒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钱牡丹中的蛊已然化开了,是覆水难收了。假如钱水仙想让她姐姐死,那么她现在已经达到目的了,何必弄这一套拙劣的拖延伎俩呢,如今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呀,还有衙门的捕快在场,如此做法不嫌太扎眼了么?咦,钱水仙的一双眼睛在斜斜地看着什么地方?
“喂,你们两个,”当然,何当归主要喊的是孟瑄,“有没有听见河岸对面的蒿草丛中有什么动静,有没有人的呼吸声?”蒿草丛距离此处有四五百丈,中间又隔着湍急奔腾的河流,想听到那里传来人的呼吸声,连何当归也是绝难办到的,更不要说柏炀柏了,所以实际上她问的就是孟瑄。
“似乎是有一个呼吸声和四五个脚步声,”孟瑄凝听了一下,而后深深注视何当归,“还是说说我们的事吧,你对我的心……”
“一个呼吸声和四五个脚步声?”何当归不可思议道,“你傻了,还是耳朵出毛病了?”
孟瑄不耐烦道:“我怎知道,可能就是耳朵出毛病了吧,反正自从遇见你,我身上的毛病也不差这一桩了,我对你的心意你应该已经很了解了,而你对我的态度真是让我迷惑到了极点。今日初见时,你那般温顺乖巧,任我予取予求,让我以为你对我也有情,为何后来说掰脸就掰了脸,还拉着柏炀柏与我不辞而别?”
何当归回思前事,答道:“当时不是你我吵架了么,不辞而别有什么奇怪的,况且那是你先找茬吵架,我不过是还击几句而已,算了,反正已吵完了,再回想吵架的过程,真真愚不可及。”
“愚不可及?”孟瑄凝望少女貌似冷漠无情的容颜,在柏炀柏有节奏的嗑瓜子的声音中悲伤一笑,“为什么你总是这样理智而冷静,难道你生平从来都不做任何一件明知愚蠢,还忍不住想去做的事情么?你当真不知我为何那般气你吗,归根到底,就是你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
何当归从地上揪了几根草,编着草戒指说:“愚蠢的事恐怕人人都做过,我从前做的多了,下场不是太好,所以现在养成了做事时瞻前顾后的习惯,轻易改不掉了,少不得请你担待些。其实事情是这样,我这三年在罗府过的不太如意,老太太让我认三舅母为干娘,每日晨昏定省,母慈子孝,皆大欢喜。可后来我发现,这位干娘常在我的请安茶中下一种药,然后劝我全部喝掉。”
“是什么药?”孟瑄作势要扑上来帮她驱毒,何当归摆摆手说:“你稍安勿躁,那都是三年之前的事了,如今我尚健在。当年,老太太将竹哥儿放在我院里养病,竹哥儿吃了他娘给他下的蒙汗药,中了曼陀罗、川乌和草乌之毒,我暗中换掉或倒掉吴大夫给他开的药,因为我觉得他的脏腑已经虚弱得不能进药,只是用温补针法为他每日扎上几针。可竹哥儿中毒太深,本来当初那些毒马上就要侵入脑中,令他变成一个痴傻儿,所以我用银针封穴令他昏睡,想让那些毒慢慢地自行散去。后来,罗家主母孙氏去跟老太太说,我正在谋害竹哥儿,还拿出了我偷换竹哥儿汤药的证据,一通‘官司审问’和‘当堂对质’下来,虽然我没受什么大的处罚,但在老太太处已经失宠不少,之所以还能住桃夭院和享受小姐待遇,不过因为几颗枣和一幅画。”
“枣和画?”沉默地听着故事的两个男人齐声重复,柏炀柏不知不觉已停止嗑瓜子了,托着下巴问,“可是,我几次潜进罗府,没见你有什么枣和画呀,你的闺房我也去过不少次呢,你的那个圆脸小丫头经常把你的肚兜叠成一摞放在你的床头上,上面绣的都是海棠和梅花,对不对?呵呵你们俩别瞪我呀,我很君子的,只看不拿。”
何当归冷冷逼视柏炀柏:“你真够无聊的,这两年西北大旱,你不是龙王吗,怎么不去普降甘霖,救济众生?”
柏炀柏挖着鼻孔望天:“从你们两个小辈对我老人家的不敬态度就可以看出,你们根本不信我老人家是那种通天彻地之人,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那我也不方便泄露给你们。不过,既然罗家人觉得你害了那个奶娃娃,为何奶娃娃如今还在你院子里又吃又睡呀,还动不动半夜摸进你的房间,钻进你的被窝里睡,有一次还把你的床给尿湿了。”
何当归扬眉说:“你不是亲眼撞见过竹哥儿的母亲去我那里闹么,那竹哥儿就是不肯跟她走,我也没办法。我虽不讨厌小孩子,可我一个表姑姑也不便长期养着他,他一个小娃儿什么东西都要交由我保管,动辄就让孙氏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