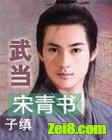赵航的南宋-第8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严霜兴致勃勃:“大哥,你看,阿福这样子,是不是就跟我们大宋的小娘子没什么区别?”她说完,看看其木格,有有些不好意思了:“啊,对了,你是不是不懂汉语,别急,我慢慢教你。”
赵航眉头一皱,觉得事情不太对,转头看其木格,其木格脸上已经露出一丝笑容来:“我懂汉语的,谢谢您。”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你,所以才不愿意开口。
严霜再迟钝,也觉出不对劲儿了,她今天一大早就让人把其木格请过来,高高兴兴地给她挑衣服,梳头发,化妆。从头到尾其木格都没说什么,她本以为其木格是汉语不好才不吭声的,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啊。严霜有些局促,虽然她比其木格大了四五岁,可对于这么一个身世可怜,跟她的成长环境又完全不一样的女孩子,严霜其实是不太懂怎么跟她相处的。她小心翼翼地看看其木格,轻声问:“阿福,你是不是不喜欢这身衣服啊?”
其木格摇摇头:“不,我很喜欢。”她低下头,轻声说:“我从来没穿过这样柔软的衣料,没有带过这样精致的首饰。我只是觉得,这样的我,有些不像我了。”
严霜看看其木格,又看看赵航,赵航隐隐有些猜测:“其木格,你是不是不喜欢阿福这个名字啊?”
其木格咬咬嘴唇,没说话。
严霜转转眼睛,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啊,怪不得呢!这名字确实起的不太好听呀!白叔叔起名字可真是…………”严霜说半截,迅速转换话题:“你叫其木格?其木格在汉语里是什么意思呢?”
“是花蕊的意思……”其木格的声音很轻,可她的话,却像锤子一样狠狠地敲在赵航与严霜的心上。
无论有多少憎恨与仇怨,她的阿妈的眼里,女儿依然是最娇嫩的花蕊。
严霜愣了一会儿,轻声说:“花蕊啊,听着就很美。我给你办户籍的时候,就用蕊这个名字好么?”
作者有话要说:似乎有亲觉得卢瑟的性格写的有些怪?
实际上,这个人物是我认真揣摩过的,他的种种行为都是基于他的性格跟他的经历而写出来的……
前几天群里可爱的软妹子花花说她越来越不喜欢卢瑟了,她提到“宋朝看不起蛮夷但是主宰的不都是满口礼仪之邦对待别人的吗”,关于这个问题,潇湘碧影对卢瑟这种态度的比喻很精辟:
我对路过的一只狗狗不发脾气
证明我修养好
但我不会把狗狗当做我同阶级的人
这话说得很残酷,但却正是我想表达的。
不同民族之间的杀戮,很多时候不就是基于不把对方当做同类的基础上的么?当日本人那中国人做细菌实验的时候,当德国人把犹太人的尸体提炼出油脂来做肥皂的时候,他们是根本不把对方当做同类的。
卢瑟是个有教养的人,也是个有着相当高的道德底线的人,即使他的一家都死在蒙古人手里,他依然不会像白林喜那样迁怒所有的蒙古人………但同时,他也不会把蒙古人当做平等的人来看,这是那个时代的许多宋人固有的观念,并非他一个人的问题。而其木格诡异的身世让卢瑟本就比较矛盾的态度在她身上体现的越发明显,一方面不会眼见她死在白林喜手里,但另一方面又对她又不能像对大宋的姑娘那样尊重。而且,他生长在一个男权,父权的社会,所以他还要维护父权的尊严,可同时他又觉得其木格毕竟是白林喜唯一的女儿,他希望这个女孩子最好能跟她父亲和解…………
卢瑟的对其木格的态度很矛盾,但这种矛盾正好就是我要写的。(百度搜或;;更新更快)所以,这个人物并非是我玩脱了,而是着意刻画成这样的,他态度上的矛盾恰恰就是因为他本身的矛盾。解释完毕,摸摸每一只:如此苦逼的话题难为大家一直看到底,辛苦了一
第九十三章
回到开封;走亲访友是少不了的;不过赵航首先还是要参见一下官家。
官家给赵植的旨意是让他三月之前回来;他二月二十日便进了京;虽然还没到期限,但是去报备一下还是没错的。
颠颠地跑去吏部复命;他这几年没少跟大宋属国的官僚机构打交道,在四川等地也没少出来办事儿;所以现在在官面上的行为还是蛮过得去的。顺利的把报道事宜办了,顺便认识了吏部大大小小好几个官员,回到家便跟严霜巴拉了起来。
“大娘;好像今年的春闱推迟了?听那些官员的意思;推迟这个考试似乎是个很重要的举措;许多人不同意。”
严霜点头道:“是啊,往年都在二月,每年考试,都病倒一批考生,有时候还会闹出人命来。春寒料峭,连夹衣都不让穿,病了也是难免的,官家几次说要改时间都被朝臣们找了一堆理由搪塞过去。这次官家在大朝会上动了怒,直说他们是自己糟过这个罪,觉得后来的年轻人居然不用遭这份罪,心里不平衡……”
赵航囧了:“这一棍子打翻多少条船啊!”
严霜也哭笑不得:“可不是么?岳相公当场就暴走了,说有个屁的不平衡,这也算遭罪?虽然不让穿夹衣,可又不是不能多穿几层,而且还有毛衣可以穿啊?有条件考上举人的,再穷也穷不到买不起一身毛衣的地步……官家这话太伤人,他要考虑一下辞职的问题。何相公也生气了,拿着拐杖敲案几,直说官家道理讲不过便大帽子压人,非明君所为,应该回去反省一下。”
赵航擦汗道:“闹成这样还没让官家改了主意?”
严霜的神色越发纠结:“咳,官家也当场发火了。说你们几十个人对付我一个,我哪里扯得过你们这么多张嘴说出来的这么多歪理——”
赵航脸上继续保持“囧”状,严霜也觉得哭笑不得,忍了笑继续描述那天的乱象:“到最后就是官家认为大家一起欺负他,岳相公说官家是胡搅蛮缠,何相公说官家正在向昏君发展很危险……最后汤思退出来和稀泥,说这种事儿应该问问司天监——”
“等等,司天监该不就是那个不干正事儿,专门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的研究与推广的机构吧?”
严霜怒道:“你把这话跟我二舅舅说说去!”
赵航这才隐约想起严霜的二舅柳芳去年才平调到司天监做监丞,他这话简直是当着和尚骂秃驴,忙缩了脖子干笑道:“啊,我不多嘴了,你继续,继续……”
严霜瞪了他一眼,这才继续说下来。
司天监这个机构很坑爹,级别很高,但是能干的正经事儿很少。所以虽然设置了许多官位,但是在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官位的大部分都是空缺的——尤其是司天监一把手的位置,建国二百年也就有那么三二三年有人干。为毛呢?还是那句话,这个机构级别太高但是要做的事情太少,司天监一把手司天监监,从三品。这绝对是高官的品级,可是干的事儿的重要性哪里能比得上别的平级官员呢?所以这个位置常年空缺,司天监的工作由司天监少监负责。司天监少监从四品,坑爹的依然是同级官员里重要性最低的那种了,所以依然很少有人干,都是让低级别官员顺便管管这事儿……
好了这里有点跑题,基本上呢,就是大宋的皇帝也是很聪明的。发那么高的俸禄让你们看星星?别开玩笑了,皇帝家里就算余粮很多,也不能这么乱花啊!所以偌大的监天钦,行政级别高的吓人,但目前需要发的最高的一份工资,是给一个区区七品的司天监监丞的。这个倒霉的司天监监丞,需要把司天监的工作整个都负责起来,而他只是个区区七品,上头没上司,部下则是看天象的技术人员们和神棍们的以及同时具备技术人员跟神棍两种身份的人员组合,简直苦逼死了。
柳芳就是这个倒霉鬼了,领着七品的俸禄,操着一群三品四品官儿该操的心,正房放在那里只能当摆设,他领着几个办事人员极为苦逼的缩在司天监的小厢房里处理整个部门的事务,每一天都有在他爹之前打报告乞骸骨辞职回家的冲动。
然后,柳芳知道了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的感觉了……官家跟一群朝中大员两眼冒火地看着他,让他说说这春闱到底在什么时间举行最科学,哦,错了,最吉利。
我勒个去,二月春闱是几百年的传统,要按历法算那肯定是二月啊!可大家伙儿都问这个问题,那显然是对二月不太满意。柳芳心道:擦,我也不满意,我考的那年倒春寒,下雪,冻透了!隔壁的考生还带了路子,你带炉子就带呗,还不会生炉子,弄得到处都是烟,呛死我了。连着好几天不能洗澡,再被烟熏熏,天气再冷些。难怪年年都有人病倒!
我们必须知道一点,柳芳的性格是很像他的父亲,这种性格特点说好听点呢,是诚实而富有正义感,说难听点,就是二缺……关键时刻,他的正义感发作,为了以后的考生们不用像他一样遭罪,柳芳当即表示二月的日子虽好,但是三月末跟四月初其实也分别都有很不错的时间。
等柳芳意识到他的老师岳相公正一脸不善地看着他的时候,大局已定。官家得意洋洋地表示既然时间都很吉利,那放在三月考试不是很好么?
赵航嘴角抽搐:“怪不得你对这事儿这么清楚,闹半天是二舅干的……”
严霜咳了一声:“二舅也算是给大家个台阶下了。其实换个时间没什么不好,几位相公也没有非要不改时间的意思。主要是官家说话太气人,这才呛起来……这事儿若真的改的不合适,便是有一百个二舅舅,也休想让朝臣们让步。”
赵航虽然当了几年官,但一直在外,对政府机构的许多事情都不了解,这会儿见严霜似乎对这些很了解,便问起了另一件事儿:
“我今天去吏部,大家的办事效率很高,跟我在西夏,吐蕃,看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听几个过来办事的年纪大一些的官员说,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似乎是在其位不谋其政,乱的很,我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大娘给我讲讲?”
严霜微微一笑:“大哥也听说这件事儿了?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太祖登基之后,为了遏制各部官员的权力,把前朝的差遣制度用了个淋漓尽致。比如科举,明明考核,提拔官员,本该是吏部南曹的职责,该由吏部员外郎主管,可实际上呢,官家却要派个刑部员外郎来主事,这样子外派过来的官员,事情要做,去没法在吏部扎下根基。当然了,刑部员外郎被‘差遣’到吏部,他在刑部的工作自然也不是他自己干,于是便又要弄个兵部官员过去主事……”
严霜说到这里,神色逐渐严肃起来:“‘属师旅之后,庶政从权,会府旧章多所旷废,惟礼部、兵部、度支职务尚存,颇同往昔;余曹空闲,案牍全稀,一饭而归,竟日无事。’这样的情况在前朝便很严重了,到了本朝更是愈演愈烈。官家需要官员做事儿,又生怕分了自己的权利去,于是便弄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来。工部,礼部的差事最辛苦,又没什么大的权利,所以到很少‘差遣’别部官员过来管事,兵部户部刑部的工作经常被‘差遣’来的外部官员干扰,最惨的是吏部,跟摆设差不多!”
赵航听着听着某头就皱了起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