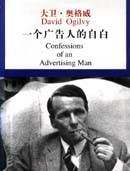展大人的衣服-第4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展大人您不要紧吧,我可是费了极大的劲,才让自己忍住没插手您和他的对战的。还有,肯定是他手臂内的狗头的古怪,你和他对战的时候,那里就散发出一股令人不舒服的气息。”兰竹拍着展大人的肩膀如是道。
虽然兰竹没说一句劝他的话,但展昭还是知道她为了不让自己难过,想着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摇了摇头,展昭温言道:“无事。”说着他拂开尚义的衣袖,可那里的刺青已经悄然无痕。
“怪不得。”展昭明悟的低语道:“这狼头刺青,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
“哦。”兰竹听了展大人的话回应着,当她看到远处溜达着的清风的时候,她立即道:“展大人,清风找回来了!咱们快点回去,办完事好吃饭啊!”
清风驮着王春香,展大人扛着尚义的尸体,两盏茶的时间,这个奇怪的组合就出现在了中牟县县衙门前。而这时府衙内出来一帮衙役,紧接着王春香的小叔杨谢祖、婆婆杨李氏和中牟县的县令师爷也一同出府。
杨李氏看到自己的儿媳,她激动的跑上前去,接下马上的王春香,杨李氏拉着她的手道:“春香,你终于回来了,谢祖说你被歹人劫走,娘立即来报官,找人去救你,你没伤着吧!来让娘看看。”
杨李氏说着也顾不得擦眼角的泪水,上上下下将王春香打量了好几遍。
当兰竹看到和杨谢祖有几分相像的县令时,她终于想通了这个案子,这应该就是《寸草心》那一个单元的了,只不过电视里展大人救出这个春香的时候,她已经中毒很深了,展大人还替她运功疗伤来着。
兰竹感觉到那个县令看杨谢祖时充满仇恨的眼神,她小声的在衣服里提醒道:“展大人,这一家子好像没那么简单。我记得这个叫春香的小叔,他不是这个老妇人的亲生儿子,他应该是县令的亲弟弟才对,但是县令和他们家有仇,现在县令想害死他们家儿子,也就是他弟。”
兰竹捂脸,这纠结的人生呐,当初看剧的时候她肿么没觉得,果然是她太不适合讲故事了……
展昭知道兰竹是来自千年之后的时空,所以对他们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的了解。他听了兰竹一段不清不楚的话,抓住了几个重点,一个是现场的这两人是亲兄弟,县令与老妇家有仇,县令想杀老妇的儿子报仇。的确刚刚他也觉察到那县令一闪而逝的目光……
可要想阻止这场人伦悲剧的发生,切入点又是什么?
兰竹看着齐聚在县衙门外的人,想着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于是她立即向展大人提出了她宝贵的建议:“展大人,其中的细节我也记不清楚了,不过这件事说开了应该就没问题了,要不然我们赌一把?您现在就把他们是亲兄弟的事情说出来,反正那个老妇人知道所有的事情,抖抖估计能抖开。”
展昭听了兰竹的话,想着这未必不是一个办法,于是他看着询问王春香腹中胎儿怎么样了的杨李氏道:“杨老妇人,您身边的这个年轻人不是您的亲生儿子吧?”
杨李氏听了展昭的话,她眉头一皱,摸着王春香肚子的手一顿,她头也不抬的道:“壮士说笑了,谢祖可是老身十月怀胎诞下的骨肉,怎么会不是我亲身儿子呢。”
王春香感觉到婆婆的手一顿,想到为了谢祖征兵西夏的相公,她哂笑道:“是啊,我婆婆平日里对小叔百般疼爱,试问若不是亲生母亲,又怎会如此?”
展昭听到杨李氏矢口否认,他没有继续询问,而是看向中牟县的县令道:“县令家中有一名失散的幼弟,而我没猜错的话,就是他。”说完之后,展昭便将手指向了杨谢祖。
段清河听了这个陌生男子的话,他眼神一厉看向杨谢祖,那个陌生男子说得对,他的确有一个弟弟,可他已经在十年前被母亲带到河中淹死了,要不是他半途挣脱,他恐怕也葬身河中,莫不是杨家怕他们杀他父亲的事情败露,怕他找他们寻仇,故意编排的吧!可这件事他们怎么会知晓……
杨李氏听了展昭的话,却惊得抬起头来,她看看杨谢祖,再看看县太爷。县太爷姓段,当年老爷误斩的那个哑巴也姓段,怪不得她在大堂前就觉得谢祖与县太爷有些相似。
如此想着杨李氏看杨谢祖二人的神情,便多了几分愧疚。当年老爷误判,赶到段宗和家中,他的妻子已经不堪打击带着两个儿子投河自尽。幸得老天有眼,段宗和的小儿子大难不死,这是上天给他们杨家一个赎罪的机会。而现在段宗和的大儿子也活着,真是老天有眼呐!
展昭看到杨李氏的神情,他温润一笑道:“相信杨老妇人也不希望,他们兄弟二人相见而不能相认吧?展某也相信,中牟县内的旧档案能说明一切。”这后一句展昭却是对段清河说的。
段清河本就是身修行洁、正直无私的好官,只是仇人突然出现在眼前,十年来压抑在心中的仇恨让他突然爆发,现在他听到这个陌生男子的话更是急于知晓答案,于是在众人还未有反映之前,便直接冲回府衙,前去调阅档案。
何康十年来对清河悉心教导,他何尝不知清河心中的苦楚,可当年杨仲康误斩恩人,责任也不在他,可他依然引咎辞官,从此不知去向。如今他自是期望杨谢祖是清河的亲弟弟,看之前杨李氏在大堂上如此维护杨谢祖,也许他的出现能够平息两家恩怨,抚平清河内心的伤痛。
何康看了一眼杨谢祖,挥手示意让这一干人等跟他回衙。
段清河看着手中的档案,他失力靠在椅背上。
档案中记载:中牟县令杨仲康,生有一子……
天禧五年,如今粗粗算来以二十七岁,而杨谢祖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难道他真的是他弟弟!
段清河抬眼看着被何大叔带进来的杨谢祖,在公堂上,他第一眼也觉得他长得与娘有些相似,如今看来他真的是他弟弟。
段清河霍的一声自椅子上站了起来,他边往杨谢祖身边走,边指责道:“你,怎么可以认仇人做父母,他们不配,他们是害的我们家破人亡的仇人啊!”段清河用力的摇着段谢祖的胳膊质问他。
杨谢祖被段清河抓的生疼,他求救的目光看向杨李氏道:“娘……”
杨李氏听到段清河愤怒的质问,她便知道他对他们杨家是有多么的愤恨,可即便这样她仍没想着逃避,这是他们杨家欠段家的。杨李氏对着段谢祖安慰道:“谢祖不要怕,他不会伤害你的,他是你哥哥,亲哥哥……”
杨李氏说着说着便哽咽起来,她当作亲自抚养的孩子,以后便再与她没有任何瓜葛了。可是看到仍是抓着谢祖不放,她立即上前解释道:“你不要怪他,他当年溺水,受到了惊吓,有很多事情他都记不起来了。”
段清河听到杨李氏的话,他充血的眼睛瞪向杨李氏:“不怪他,那就是怪你了!怪你的丈夫屈斩了我爹!只因我爹相貌与水盗相似,可怜他哑不能言,如此老实的一个人,却因为捕鱼的行当葬送了性命!我娘悲愤莫名,带着我与幼弟投水自尽,若不是我中途挣脱,想要找何大叔前来救人,恐怕我早随爹娘去了。”
杨谢祖听了段清河的话,他向后踉跄一步,闭上眼睛却全是这十年来,娘和哥哥对他的爱护,杨谢祖上前挡在他娘面前道:“不!不管怎样,娘她十年如一日待我比亲子还亲,家中清贫,全家人吃糠咽菜,却只有我顿顿有肉,哥哥他更是一早设摊为代书,中午替人抬脚,夜晚还要打更守夜,赚得的前全都花在了我身上。征兵西夏九死一生,我娘更是强迫自己的亲生儿子,代我出征、可怜我哥,一介书生,至今仍是生死未卜。”
杨谢祖看着沧桑的母亲,继续道:“杨家欠我家两条人命,我杨谢祖欠杨家的十世也还不完呐!”
杨谢祖说完跪在了杨李氏面前,虔诚的一拜后,杨谢祖闭上眼痛苦的道:“可是父母之仇谢祖不能视为无物,至此三拜后,以往恩怨一笔勾销……”说着杨谢祖又是两叩首。
段清河没想到杨李氏竟会如此厚待他弟弟,他怔愣的站在当场。在仇恨与恩情中挣扎许久,段清河长叹一口气,胸中积累了十年的仇恨随之吐了出来。
段清河对着一直静立在一旁的陌生男子鞠躬道:“不知尊驾何人,请受清河一拜。”若不是这个人,他恐怕要害了自己的亲弟弟,到时他还有何颜面再见地下的父母。
展昭见段清河眼中再无怨怼,深知段清河拜他何意,展昭跟着抱拳一礼道:“段县令太客气了,在下展昭,展昭在开封府中常听大人说,段县令公正无私,政简刑轻,最是令大人得意的门生,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其余只字不提……
在借中牟县的马快衙差向开封府送了一封信之后,展大人终于带着兰竹去吃那顿久违的午饭了,吃完饭之后,展大人在兰竹的要求下休息够了半个小时,才驱马上路。
因为师兄的事情绕道中牟,又耽误了半晌的时间,为了赶上进度,展昭出了中牟先便一路扬鞭绝尘,在中牟通往许通的林中小道上留下一道道残影。
兰竹盘坐在展大人的肩头,看着展大人策马扬鞭的潇洒英姿,帅得她一塌糊涂。兰竹三令五申的告诫自己,最多只能再看两眼,就必须去修炼了……
然后瞪着眼睛仔细的瞧着温文尔雅、举世无双的展大人,就是不眨!
这个时候,作为一只鬼的优势便大大的体现出来了,不眨眼也不会有肿胀酸痛的感觉。兰竹正自鸣得意的时候,一阵熟悉的眩晕便传了过来……
兰竹莫名其妙的摇了摇有些眩晕的脑袋,耳朵里听到一声清风响亮的嘶鸣,她瞪着眼睛向前方看去,模糊的画面一帧一帧的变得极为清晰:两只马蹄!
“!”
骑在马上展昭感觉到兰竹强烈的目光,他强迫自己不要去想,让自己的心思全都放在赶路上,可对于兰竹的目光他根本无法忽视。梗着脖子在林间赶路,展昭只觉得被兰竹注视的那一侧脸灼热无比,手中的马鞭没有控制好力道,身下的清风一阵吃痛,速度又提升了几分。疾驰的劲风灌在与目光焦灼脸上,带来几分凉意。
偷偷地舒了口气,展昭眼角的余光中却突然闪出了一个白影,他惊得立即勒住缰绳,使了十分的力气才将马头磨开。
待清风的两只前踢着地,展昭正想要与来人道歉,却在看到对方的衣着的时候,心下一跳,他立即将脸转向右侧。
脸上红的滴血,展昭心虚的瞟向他的右肩,口中结结巴巴的道:“兰兰……我,我不是故意的,我……”
前方那位姑娘的妆扮沾满了他的脑子,那是一位长相秀丽的姑娘,有着一双含着雾气的动人眼眸。可是……可是这样一位姑娘,她却头发凌乱的一条白色的布条系在脑后,她穿着一件单薄的“衣裙”,“衣裙”下膝盖若隐若现,“衣裙”是没有袖子的,甚至,竟然露出了一抹酥胸,而且她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赤着脚,不,确切的说她只穿了一只不知什么材料的红色的“屐”。
她衣裙上似乎印着一个猪的头?还有那位姑娘也许只有这一条“衣裙”。她的衣裙被斩断之后,她竟然用牙将那变成两段的衣裙咬出洞来,再将衣裙的下摆扯破,用扯下来的布条穿过衣洞,把两半的衣裙又系成一条,想来她头上的“发带”也来自衣裙的下摆。
该死!只一眼他却连最细微的地方都印在了脑子里!口中的解释在他想对面那位姑娘的装扮时便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