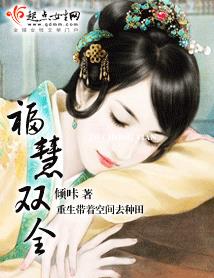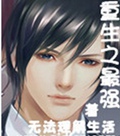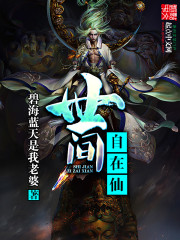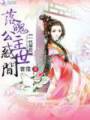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⑼未胗凶约旱挠攀啤K母盖滓丫怂裘山逃馐顾芸炀褪视α搜暗姆瘴АK拇匣郏诤⒆又蟹浅4蜓邸�
寺院确实如父亲所说的那样,里面藏着无尽的知识。如今,一个从未接触过的世界,为阿旺嘉措开了一道门。那些经师们,是真正学问渊博的人,他曾经疑惑的问题,总能在他们那里得到满意的解答。他们为他打开了一道可以满足他全部好奇的门。
看着这些经师,阿旺嘉措会想起父亲。父亲虽然没有这些经师们博学,但亦是一个满腹经纶的人,这让父亲在家乡受到了尊敬。他想要成为父亲一样的人,他想像这些经师们一样博学。他收起了放野山林的心,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经师们的教学上。
阿旺嘉措学得很认真,也学得很快。那些复杂的藏文,他不久就能识读。经师们教的经文,他只听一遍就能背诵。他记下了经文的解释,还能提出自己的问题。所有成绩好的孩子,都会受到老师更多的青睐,阿旺嘉措也成了学经孩子中最受经师们喜爱的。他们乐意为他解答疑问,有时还会多点拨他一二。这让他在孩子们中更加出众。
用现在的话来说,阿旺嘉措算是天才儿童了,他一早就表现出了独特的天赋。如果他的这种天赋,是源于他是达赖转世,那么汉地的诸多天才儿童,当也是学富五车之人的转世。
看那仲永,才5岁,就能在未见过纸笔的情况下,要求写诗。不仅写了,还写得极有文采。此后只要指定事物让他写诗,他都能立即完成。这份天赋,即便在一个成年儒生那里,也不是件易事。可仲永就可以未学而成诗,即便七步成诗的天才曹植,也是十多岁才以诗文闻名。如果我们不以转世来作注解,很难解释这份天赋的异禀。
借着藏文化的浪漫,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们,或许真继承了前世的学识。但此生是否能将此继续,却是未知。王安石在《伤仲永》中讲到,天才的父亲把孩子当了摇钱树,每天带着仲永四处拜访,给有钱人有偿作诗,而不是给他教育。等仲永长到20岁时,他就和平常人没两样了。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在三四十年前,中国曾是神童满天飞的国度,神童画家、神童音乐家、神童诗人,成为令我们羡慕的神奇人物。这些神童们四处应酬,和当年仲永的遭遇一样。可今日,我们几乎没再听到他们的名字,他们消失在人海之中,甚至比一般人还普通。
当年,王安石就已经对此作了总结,他说:“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与人者不至也。”仲永之所以聪慧,是因为天赋的异禀,使他拥有了比常人更高的智慧。他之所以成为了普通人,是他没有受到后天应有的教育。
即便是天才,没有后天的教育,仍可变为庸才。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至少让一部分先天聪颖的孩子,拥有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阿旺嘉措是这些幸运孩子中的一位,他的聪颖,让他有机会得到最好的教育。虽然不知道这样的机会,对他是幸,还是不幸。
桑结嘉措虽然有政治野心,但对转世灵童的教育,却没有马虎。他为阿旺嘉措准备的经师,不仅学识渊博,更兼有各个派别。这给了阿旺嘉措一个机会,去全面了解藏传佛教,这是他成为全藏宗教首领的第一步。
这样的教育,应该是成功的。他们在他的头脑中建立起了牢固的信仰,他后来曾写诗赞颂佛法:
十地庄严住法王,
誓言诃护有金刚。
神通大力知无敌,
尽逐魔军去八荒。(曾缄译)
此时的阿旺嘉措,是虔诚而好学的信徒。与佛经、灯盏相伴的日子,他不感到厌倦,至少此时还没有厌倦。他用繁琐的经文,为自己构筑起一座堡垒;他用其中的智慧,充实自己的内心。他知道,他正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去观望无限的知识,他正在逐步成为一个有学问的学者。他的神经兴奋着,他为他能处身于这样的佛界,自豪。
阿旺嘉措此时还不知道,他将有一天会为身处佛界而愤慨,恨不得远离佛界。但此时的阿旺嘉措,还没有发展出灵异的未知能力。他不知未来的世界,他只为渐入佳境而兴奋。他做着一个少年对未知渴求的梦,他愿意在这里,倾尽他所有的心智。
黑暗的殿堂中,那个小小的身影,独自摇晃出一朵红云。他轻拿出一页佛经,放在一侧,继而接着诵读。清朗的声音,在凝重的佛殿中回响。酥油灯的光,没有摇动。神佛们,也出奇地静穆。它们都在注视这少年的成长,都想要注视他将要经历的,不凡一生。
第5章 山有木兮木有枝
梵音,是寺院唱诵的声响。它从一个个躯体飘出,汇合成唱诵的河流。梵音唱响的,是佛的谆谆教导,佛祖的慈心穿透岁月,在这唱响中得以重现,仿佛佛陀一直在这世间,慈爱世人。
事实上,佛祖已经涅槃了若干世纪。他用遗留于世间的智慧,教导世人。这个世间一切都在缘起缘灭之中,没有什么可以不朽。但人类的智慧,却可在这尘世存留更长久的时间。即便创造它的人和学习它的人都已从这世间消失,智慧依然在尘世的某处发光。
在佛灯的摇晃中,我们听到了他的吟唱。声音从轻启的唇舌中溢满而出,汇成音乐般的音响,将他包围。那梵唱,钻进了他的耳,钻进了他的心,钻进了他的前尘往事。它带着前尘往事的智识和慧根回来,让那颗希望在虔诚中有所收获的心,感悟到了智慧的源泉。可他不知,从这前尘往事中翻出来的,不仅是智慧的金子,可能还有世俗的尘埃。
生物从一颗单细胞开始进化,繁衍生息成一个世间的繁华。繁衍的需要,渐渐被赋予了情感,人类成为了有情的生物。情之为物,纠葛人的一生一世。从初出世间的亲情,到青梅竹马的友情,再到此生不渝的爱情。情之于人,有割不断的联系。它深深地扎在人的心里,哪是一两句梵唱就能将其割舍的?
于是,当梵唱要去割这牵连,这牵连反而牢固地扎在心底。令人迷茫,令人难舍。
阿旺嘉措在孩子们中,有着出类拔萃的学识,对于经文的理解,他常常一点即通。但他心中一直迷茫的是,为何佛总说世间苦,总说世间的情谊是虚妄的。他心里不信这个。他相信的,是父亲对他的谆谆教导,是母亲对他的爱护有加。他爱他的父母,即便见不着他们,他仍是想念。
尤其当看到佛经中提到要割断世间情谊时,他便会想起父母,思念就从心底汩汩地流出。刚到寺院时的兴奋,已经渐渐消退,对母亲的想念却在与日俱增。毕竟,他还是个孩子。
在梦里,他会听到那首歌,母亲送他时唱的那首歌,歌声从远方飘摇着过来,搂过他的头,就仿佛是母亲搂着他一般。
多久没有这样的温暖了?即便寺院的喇嘛们再喜欢他,他们也不如母亲的爱来得浓烈。那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能暖到他的心底。他想念老屋的味道,想念母亲的味道,他想念和她在一起的任何瞬间。
他知道,他是母亲唯一的倚靠。虽然他还没有强壮到可以保护母亲,但没有他的陪伴,母亲定会感到孤独。他常在梦醒后想,没了父亲的支撑和他的陪伴,母亲一个人过得可好?她一个人在家劳碌,劳累会不会在她的脸上留下苍老?她会不会像他梦里一样,在村口送他离开的那块大石头上,远目眺望等待着他?她会不会一个人唱着父亲的歌,被思念折磨得日渐消瘦?
可自从来了寺庙之后,和母亲相关的消息,就像是早晨的薄霜,还没有感知就已经化为冰水,浸入泥土。几次三番,他想回家去看看,可都被老师们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阿旺嘉措也没多想什么,正如老师们说的,他还未到学业有成之时,此刻回家,只会平添母亲的烦恼。
但他还是盼着母亲的音讯。他开始在念经的时间开小差,有烧香的人走过,他都会去辨一辨他们的眉目,看是不是村子里的人。寺里的喇嘛都知道他有这心病。有一两次他们知道是他村里的人来,便去通知他。他急急地跑去,可村里人已经下山了。他只有望着寺门外的空旷,发呆。
偶尔,他会溜出寺门,向着村子的方向遥望。仿佛他的目光能穿透云层,看到阿妈的身影。他有时也会唱起父母教给他的歌,让歌声飘得很远。他知道,歌声不可能飘到母亲的身边,但他希望,这风、这云,能把他的思念送给母亲。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母亲的消息,竟然是她的死讯!他已经不记得是如何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只是浑浑噩噩地知道了一件事:他善良慈爱的阿妈去世了。
在模糊的泪水中,阿旺嘉措看到阿妈唱着好听的歌谣,在烹饪美味的饭食;他看到阿妈穿着盛装,在热闹的节日里,像一朵绽放的格桑花,美丽迷人;他看到阿妈在家门口呼唤顽皮的自己;他看到阿妈在昏黄的灯火下,做衣服、讲故事……可现在,这一切都不在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母亲可以依偎,可如今母亲也去了,他还有谁可倚靠?命运,就如此决绝地割断了,他与世间的亲情。可他为何没有觉得这是解脱?他只感觉,心被活生生地挖去一大块,空空的,没着没落。
哭了千百遍,泪水早已经干了。可阿旺嘉措的眼睛,仍久久地望着寺外。他看不见这经堂中的烟雾缭绕,他只看得见一片遗落的世界。愣愣地,时间流逝,世间却仿佛与他无关。当经师们唤他时,他转头而来的眼神中,有着丝丝的恨意。
是的,他恨,他恨这寺院,恨这带他离开母亲的寺院。从此,他和母亲天人相隔,他再多的思念,母亲也感应不到,他再多的呼唤,母亲也无法回应。他甚至恨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隔绝他和母亲的世界!
看着阿旺嘉措散着狂野的眼神,经师们有些怕了。他们占卜的结果,是阿旺嘉措着了魔,如果不让他离开这寺院,他将被自己毁掉。于是经师们决定将他送到一个离家乡更远的寺院去。
跋涉。从一个处所,到另一个处所。对于心灰意冷的人来说,跋涉是没有实意的。但对于孩子来说,跋涉过程中带来的一路新奇,却可以唤醒他内心的好奇。
那年,阿旺嘉措14岁。一个喇嘛带着他,走上了去错那宗的路。他们一路往东北前行,路程虽然不远,却让阿旺嘉措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有几十上百间房屋并排在一起,中间的街道上有几家商铺,门口摆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和阿旺嘉措出生的小村庄比起来,这里繁华得多。
这在阿旺嘉措的眼中,俨然就是一座繁华的大城市了。他的脑袋瓜,被看到的新奇事物占据着,一刻不停地去琢磨:这些奇怪的物件,究竟是用来做什么?心底的某些东西就此被激活了,它跃跃然地跳动着,要去感受这世界。
喇嘛看到阿旺嘉措眼神的变换,不由点了点头。他知道,阿旺嘉措来对了地方。他只知道阿旺嘉措的神智在恢复,他不知道的是,阿旺嘉措将在这里,惹起新的尘埃。
喇嘛带阿旺嘉措去的,是比巴桑寺更大的寺院——贡巴寺。这里的藏书,比巴桑寺多,这让阿旺嘉措重拾了学习的兴奋劲儿。他看了很多经书,但其中最让他感兴趣的,不是那些高深的佛理,而是夹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