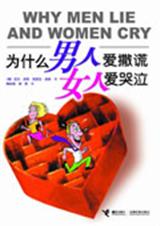男人的另一面-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二天上午,他一到办公室,立即打开电脑。果然,初雪一早就回复了,她说他是无赖,但是同意见面,最后一次,并一再吩咐今后不许用电子邮件与她联系,她丈夫会接收的。
白佐很亢奋,心想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他怎么可能去做那无赖的事。他立即回复:无赖谢谢,不见不散。
“女人毕竟好欺负。”白佐又得意又恻隐。
第三章 男人的另面
第三章 男人的另面(1)
6
天津车站上车的人不多;列车停靠十五分钟后就离站了。有人敲了一下门,女列车员出现在车门口,身后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头发涂油抹蜡,西装笔挺,红皮鞋,拎着一个贼亮贼亮的皮箱。他皱着眉头,打量了一下包厢,用浓重的广东腔朝列车员说:“搞错了吧!”
“没错,你看。”列车员指了指包厢号。
他朝我努了努嘴。
“啊,这是列车长一个亲戚,暂时在这儿坐一会儿,等下再安排。”
“不行,你把列车长叫来!”
这回他不是广东腔了,而是我十分熟悉的南海省口音。
列车长闻声赶来说:“老板,请原谅,一会儿济南站有人下车,小妹就调过去,今天旅客太多了。再说,你也只有一个人。”
“我一个人?这四张车票我全买了,是北京站就买起,我到天津看一个朋友,我就要一个人坐!”
“列车长,那我走,我去外面坐。”我拎起旅行包,真后悔没买票。
“别价,人家老板大量好商量。”列车长殷勤地把男旅客的皮箱拎进门摆在铺上,又拂拂床、掸掸窗,让男旅客坐下,然后附在他耳边说,“这是我们局长的亲戚,一会儿我就安排她到其他房间。”
“局长,哪位局长?你们北方局几位局长我都熟悉。朱副?马副?牛副?”
“哎呀,让你猜着了,就是马副呗。”列车长顺水推舟。
“马副够哥们的,基建工程的木材全是用我们的。”
“这么说是自家人喽!”
“那可不,以后碰见马副代我问好。”
“一定一定。小妹,这是马副局长的朋友,我们不打扰了……”列车长朝我使眼色。
“别价!既然是马副的亲戚,那也是我的亲戚,小妹坐下。到哪里呀?”
“到江城。”
“啊哟,江城,‘契弟’江城。”
“契弟”是江城的一句方言,我听宝说过,是一句骂人的话,意思是淫乱不堪。
“小妹,算你运气好,大哥高兴,你就陪大哥坐这一趟车,你这张票我出了。”
“老板真大方,肯定是发大财的。”
“哪里哪里,大财没发,小财发点,够吃够喝的……”男旅客趾高气扬,大声讲话。
隔壁车厢有人探头喊:“声音轻点好不好,赚几个小钱在这里‘腔宽’!”
“腔宽”也是江城的一句骂人话,宝也曾对我说过,意思是说大话,不实际。
“轻个鸟!你们江城人都是‘契弟’知道不知道?”男旅客朝隔壁车厢骂过去。看来他不是江城人,听口音是卜城人。
隔壁包厢有两个男人冲出来喊:“有种的出来,别躲在房间里骂,你奶我操,卜城人。”
原来男旅客是卜城人,宝也给我讲过,南海省的卜城人在全国经商,精明绝顶,被称为“中国犹太人”。
男旅客一步跨出包厢,捋袖拂脸,准备打架,那架式与他那一身笔挺的西装实在不相称。好在列车长身高马大,女列车员咧咧嚷嚷,才把三人劝进包厢。
男旅客气鼓鼓地说:“我最讨厌这些江城人,最势利的小市民!”
“老板,你跟他们计较什么,他们是看见你这一身派头嫉的。”列车长假意奉迎说。
“我不与这些小人计较!”男旅客掏出一包中华烟,抽了一支递给列车长。列车长连说不会抽,婉拒了。
列车长转向我说还不谢谢大哥?
我说谢谢大哥,男旅客说别客气小事一桩。列车长再次谢过男旅客就关门出去了。
包厢平静了下来,男旅客开始炫耀地整理行李物品。他从皮箱中拿出便携电脑、茶叶、口杯、书籍、零食,顺手扔给我一包南海省出产的大橄榄,头也不抬,似乎是上帝的恩赐一样。我不好意思地接住,说了声谢谢。
他打开电脑,我看出他是不熟悉装熟悉。他用右手中指敲键盘,那中指又粗又大,他仿佛生怕键盘不听话,一边骂“操”,一边用力敲,我担心他要把键盘戳穿。
“你别使那么大劲。”我边吃橄榄边说。
“嘻嘻,这玩意儿我刚学。”他倒是很坦白。
“你玩什么游戏?”
“什么都玩。”
“你要学会用双手敲键盘。”
“那玩意儿太累。”
“我教你好不好?”
“好……”
我坐到他旁边,手把手教他。他笨拙地跟着学。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出身的?”
“你不是老板吗?”
“我是打石头出身的。”
“嗬,还真看不出来。”
“包装的。”他指着自己一身西装革履,“现在做木材生意,过去看过性病。”
“你是南海省的卜城人。”
“嗯。”
“‘中国犹太人’。”
“嗬,你也知道?”
“我朋友说的。”
“过去我们以为犹太人很坏,出卖耶稣,其实耶稣也是犹太人,一说我们是‘中国犹太人’我们很反感。现在知道犹太人很精、很富、很厉害,说我们是‘中国犹太人’我们很高兴。小妹,你是哪里人?”
“我是江西人。”
“江西老俵。去江城做什么?”
“朋友出了点事,去看看。”
“什么事,大哥能不能帮你?”
我警惕地看着他:“你我萍水相逢,才认识不过几分钟,你怎么想帮我?”
“嘿,什么叫江湖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反应比电脑还快,凭感觉嘛。我看你小妹很顺眼,绝不是坏女人,不就给了你一张票吗?”
“说的也是。喂,我正想问你,你一个人干吗把整个车厢的票全买下来,多浪费呀!”
“嘿,我是想体验一下坐专列是什么滋味。你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出差都是坐专列,我当然不能包整列,包一个厢总可以。飞机坐腻了,换换口味,体会体会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怎么排场的。车厢包了,就缺个张玉凤,你来当张玉凤得了。”
“哎呀,你可不能祸害我呀!”
“你,就你这样子,还达不到我祸害的水平。”
“为什么?”
“你这相貌不入流。我玩的都是模特、歌手,至于明星吧,一时还攀不上。不过我师傅那糟老头,要的都是明星。”
“别吹!看你那熊样,”他真有点像狗熊,个子又高又大又胖,样子又笨,加上大背头,“真有模特、歌手看上你?”
“她们不看我看钱呀!这年头有钱什么办不成?我们省那个走私头,不是把全国最出名的明星都搞上了?”
“真的?”
“别看我这熊样,北京部长家,总后首长家,我可以随便进出。”
“哎哟,那我朋友的事,说不定你也能帮上忙。”
“什么事,尽管说。”
“什么事我现在说不清楚,反正被‘双规’了,要到江城问问才说得清楚。”
“贪官,肯定是贪官。拿了多少?”
“别说那么严重。我那朋友确确实实是个好人,好干部。”
“他做什么?”
“是一个集团董事长。”
“那肯定的,不是贪污就是受贿。喂,你朋友多大年纪了?”
“他……”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五十八这个岁数,刚才要是说是我亲戚就主动了。
“嘿,别不好意思,朋友归朋友,老公归老公,他要出事你就跟他拜,这有什么关系!”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会跟他拜,我要去看看能不能帮助他。”
“看来你对他感情蛮深。”
“是很深。我不知道自己是犯傻还是在受骗。”
“女人之美在于蠢得无怨无悔,男人之美在于说谎说得白日出鬼。喜新厌旧、喜欢撒谎是男人的特点,知道吗?”
“知道,手机短信说的。”
“知道就好,你要提防。”
我犹豫了,宝会不会撒谎,会不会骗我?他说过除了他妻,他此生没有过别的女人。但他为什么又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另面,人也有另面,他也不例外呢?人会变,他会不会变?我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
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很古怪,很狡黠,叫人难以捉摸,但被后来的紧张、激动所淹没,我就没有多想。他不直接通知我住哪家宾馆,他指定我在广场上见面,他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好像地下党接头。等在广场见了面,他环视我周围没人跟踪,才带我去宾馆,他住的景元大饭店是北京出名的饭店。后来他解释说,前几天他刚看到一份资料,说有人利用色相设圈套让男人上当,进而敲诈钱财,因此他要警惕。天啊,我和他电话恋、网络恋恋了整整一年才见面,他难道还不相信我?但是第一眼他给我的印象太好了,比相片上的年轻、精神、健硕,虽然五十八岁了,却跟四十多岁的年富力强的中年人一样,那成熟老到的魅力,那像父亲一样的亲切慈祥,把我的疑虑一下子赶得烟消云散。
他带我穿过广场走进饭店大堂,顺手拍了拍我的头,像我爸经常拍打我的头一样。
“怎么像个高中生?”
这是他跟我见面后说的第一句话。
“我有那么年轻?”
“不是说年轻,而是说不成熟,像个小姑娘。”
我不知道这是褒还是贬。后来他才给我描述,那天我穿着短T恤、牛仔裤,背个包,像个高中生,顶多是个大一女生。不成熟是指我脸色灰黄、不红润,没有妇人的韵味,看得出他十分喜欢成熟的、有风韵的女人。
他带我进了房间,这是一个巨大豪华的房间。落地大玻璃窗下,烟雾迷漫的北京城像个水泥森林公园。车人如蝼蚁,在纵横交错的街道上移动。我从来没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俯瞰北京城。他从我背后轻轻地拥住我,我一转身像见到亲爸似的一把抱住他。我哭了,我不知为什么哭,也许是因为自己身世孤独,缺少家庭父母的关爱,今天突然见到一个像父亲似的亲人,幸福和快乐突然降临而流泪。我的眼泪像断线的珍珠簌簌滑落,我不擦眼泪,不觉羞耻,不怕见笑,伏在他的胸前痛痛快快地哭着,我从来没有哭得这样酣畅淋漓爽快过。后来我想,我这样一见面就扑在他怀里哭,是注定要掉入他这口深井的。
他并没有擦我的眼泪,也没有说不要哭、别伤心之类的话,而是看着我,微笑着,一任我泪水滂沱。后来我问过他,为什么看见我哭不安慰我?他说你需要的是宣泄,人一宣泄,心情就会好。他小时候在教堂唱过歌,有一首
歌词是“母亲啊,我喜欢你流泪,热泪充满了我的心,我的心啊,变成地上的天堂”,这几句歌词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不过,他母亲死得早,他从小失去母爱,十分怀念母亲的爱。这就是后来我为什么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叫他“宝”的缘故。他有恋母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