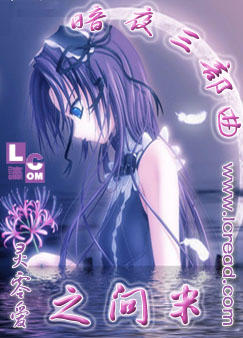老鼠爱大米-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嫘Ч阎豢伤家椋梢猿晌澜绱呙呤飞霞宕呙叩牡浞吨弧N矣肓礁雠笥训蹦暝诒本┛垂槐竟赜诖呙叩氖椋獠涣松倌昶ⅲ槁鄢说际Χ媸至煨渫乘В耆桓裨偌痈龃呙呤Α!敝钡浇裉欤褂胁簧俚笔氯巳匀淮τ诘蹦甑谋淮呙咦刺缧啤扒啻何藁凇钡牧合⒏吆簟霸傥煳辣藕啊钡恼懦兄竞图岢帧啊堆扪籼臁肥亲钫媸档淖髌贰钡暮迫坏热恕�
知青一代,回顾青春岁月的时候,多放在人生得失之上,阿城却敏锐地指出:知青都参与了疯狂的对环境的破坏。如果说打过或者没有打过人的事实,还需要进行调查和取证;那么开荒、砍树,谁没有做过?“三十年了,知青不再年轻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承认自己是破坏者的知音。近年来回去插队地点看看的知青们,意识到破坏的后果了吗?黑土地,北大荒,处女地,意思应该是原始生态,破坏它为什么成了‘人生得到锻炼’这种只对一代人生效的欣慰呢?”写到这里,阿城的语调,是在平淡背后隐藏着沉重。可惜的是,在他的同代人当中,这种清晰的自责异乎寻常的少。“在常识面前,不要欺骗孩子。在丧失常识的时代,救救孩子就是教给他们什么是常识。”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可贵的常识,它伸展和发扬了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呼喊,而赋予其更为严峻的内涵。
阿城的文字轻巧而锋利,却常常能够一招制敌。不似杨过的重剑,粗大朴拙,气势逼人;而像李寻欢的飞刀,凌空一闪,直入虎口。他的文字不夸张、不雕饰,如流水、如行云,有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洒脱和悠闲。他的谈饮食、谈爱情的文字,有当年林语堂和梁实秋的风韵。这也许跟阿城身处国外有关,在国内每天耳闻目睹一桩接一桩背离常识的事情,心情自然会峻急起来。心情一旦峻急,文字也会跟着峻急起来。我很羡慕阿城的这种心态,不过各自的生存环境和性情不同,模仿是模仿不来的。阿城行文的时候,似乎从不谋篇布局,像是聊天一样,茶浓的时候,侃侃而谈;待到茶喝淡了,点到为止。例如,他对国内的足球狂热很不以为然,就随手敷衍成了一篇《足球与世界大战》。中国足协的官员曾经说:“与其窝窝囊囊地输,不如悲悲壮壮地死。”阿城反问:这是何苦来?“让足球只是一种游戏好了,就好像让文学只是文学就好了,不要给它加码。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按常识去做,常常在于智慧和决心吧。”足球的胜败与国家的兴衰无关,这同样是一种被遮蔽的常识。中国人太缺乏游戏的心态,仿佛一球可以兴邦、一球亦可以丧国。在神采张扬的背后,其实是骨子里透彻的自卑。从某种意义上说,足球与伟大领袖一样,也在充当着催眠大师的角色。让足球回到足球,让文学回到文学,让日常生活回到日常生活,阿城想说的不过是这样一些常识而已。
阿城喜欢说“鬼故事”,这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兴趣。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意识、缺乏彼岸关怀,“鬼故事”也就成了中国文人发挥想象力和好奇心的最好场所。《聊斋志异》中所谓的“花妖狐媚,多具人情”,阿城想必是深有体味的。“我读中国小说,很久读不到一种有趣的东西,就是鬼。这大概是要求文学现实主义的结果吧。”这里所说的“中国小说”,大概是指当代的中国小说。比起汲汲于“有用”来,阿城对“有趣”的看重,更上了一个境界。我又想起贾平凹的新作《怀念狼》,小说中有不少狼精幻化为人,与猎人斗智斗勇的故事。这本来是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却被某些人批评为“颓废情调、封建迷信”,这种巴尔扎克式的文学观,一旦定于一尊,不就要了文学的命吗?与贾平凹一样,在讲述鬼故事的时候,阿城的文字达到了从容的极致。有“闲话说玄宗”的沧桑感,却没有“白头宫女”的情不自禁。
阿城的博学通览与绝顶聪明,都与王小波相似,他的许多篇什让人读后立刻联想到王小波,顿有“何曾相识燕归来”之感。阿城与王小波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特质,都是当代文学最缺乏的,也是令当代文学感到隔膜的。所以,他们的文字能够赢得普通读者的喜爱,因为普通读者是凭借自己的直觉去喜爱的;同时又遭到文学评论家们的冷淡,评论家们无法使用已有的概念进行分析和研究,所以只好保持尴尬的沉默。而评论界怎么说,已经跟他们本人无关了。
阿城开着自己组装的跑车上路了,走到哪里天黑,就在哪里停下来。
也许,他会遇到一个异国的可爱的女鬼。
暧昧的日本,锐利的大江
1994年12月7日,当大江健三郎荣获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日本时,读者们发现书店中大江的作品少得可怜。与福克纳一样,大江在国外的名气远远超过了国内。我在大江获奖前一年就已经注意到他的作品。记得那是1993年秋天,我在北京大学台港文献中心,惊奇地发现了那本台湾版、金色封面的《个人的体验》。然后,一口气就读完了它。
2000年9月,大江健三郎应邀访华。自20年代印度大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访华以后,又一颗闪亮的文学之星掠过中国文学的天幕。如果说当年白须飘飘的泰戈尔让中国人感到遥不可及,那么今天大江的来访则让中国的作家和读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日本是中国的宿敌,大江却对中国一直抱友好态度,迥异于一般的日本人;中国的文学工作者有着难以言说的诺贝尔情结,诺贝尔奖偏偏光顾狭小的日本岛而不降临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对于作品以晦涩著称的大江健三郎,我们既尊重、羡慕,又带着些许的疑惑和嫉妒。
大江究竟比我们多出些什么呢?或者换一种提问法:我们究竟比大江少些什么呢?远远地阅读在海的另一边的大江,答案也许还有点朦胧。现在,我们有了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比较和思考的机会。
母亲与儿子
出现在中国社科院研讨会会场时,大江身穿一身黑色的中式服装,里面是雪白的衬衣,显得朴素而凝重。用王蒙的话来说,“大江先生一看就像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而且是津贴在每年6万元以下的教授。”大江说,这是他领取诺贝尔奖时穿的、最好的一身衣服。作为一个小山沟里长大的孩子,尽管功成名就,他依旧保持着清水出芙蓉般的朴实。大江安静地坐在主席台上,英华内敛。而他周围的中国作家们却有些躁动不安。
与那些崇尚现代都市生活的日本新生代作家不同,大江身在东京,心却还在故乡那个小小的山村。那里有童年涉足的山山水水,那里有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母亲不习惯东京,坚持住在青山绿水的村庄里。大江是个孝子,获奖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故乡向母亲报告好消息。他开玩笑地对母亲说:“现在健三郎排在了泰戈尔和鲁迅的后面。”而母亲用两只手分别做了一高一低的手势,对他说:“泰戈尔和鲁迅这么高,健三郎这么低。”在母亲的眼里,儿子永远是儿子,是稚嫩的、调皮的儿子,尽管那一年大江已经快满60岁了。
在谈起母亲和儿子的时候,大江最动感情。大江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是智障儿童。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大江夫妇终于将儿子培养成一名优秀的音乐家。如今,儿子创作的歌曲,比父亲的著作还要深入千家万户。《个人的体验》是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写的就是一位获知妻子产下残疾婴儿的父亲,由沮丧、绝望、逃避到清醒、自信、进而勇敢地承担命运所赋予的责任的精神历程。今天,当大江谈到儿子的时候,脸上堆满了温馨的微笑。但是,谁知道这微笑背后的辛劳呢?
大江是个性情中人,他的“性情”正是中国作家们竭力要泯灭的。中国作家讲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重视技巧而忽视心灵。近20年以来,流派纷呈,你方唱罢我登场,却罕有震憾人心的作品问世。在研讨会上,中国作家们也多是斟词酌句,挑选恭维话来说,而回避心灵和思想的交锋。面对“文如其人”的大江,有多少人在反观自我呢?那么,“见”与“不见”又有什么区别呢?
大江最崇敬鲁迅先生,他说,在20世纪亚洲所有的作家中,如果要他推举出一位最杰出者,他一定会推举鲁迅先生。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大江也是如此,在谈到对母亲和儿子的爱时,他那黑镜片后面泪光闪闪。大作品缘于大智慧,大智慧缘于大慈悲。这一点,那些痴迷于在作品中耍小聪明的文化人是无法理解的。“爱”在中国的文化圈子中,居然已经成了一个让人感到羞怯的词语。
文学与政治
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直就是“剪不断、理还乱”。大江健三郎是一位政治色彩很浓的作家,不同于年轻的“飘”一代喜欢阅读的村上春树。他对村上这一代青年作家的“非知识分子化”持批评态度,而认为“一个好作家,应该强烈意识到文学家是士大夫,是知识分子”。
在大江看来,文学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的作家不是一个好作家。1999年,他的柏林的一次演讲中,引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当年使用过的“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概念,来呼唤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干预。“我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在家里写写小说、做做实验就行了的,他必须主张通过自己的学问获得对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为此需要战斗。”反战与环保是大江作品的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对今天的中国也极具针对性。
在日本这个民主制度尚不稳固,皇道主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大江倍感为民主、为自由、为和平而战斗的必要性与艰巨性。他在演讲中曾经说:“以自己羸弱之身,在20世纪,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的苦难……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大江的这一姿态使我联想到拉美的文豪略萨。略萨面对的是更为严峻的军人独裁政权,“1953年我进入大学学习之时,跟别的拉美国家一样,我国正处于军事独裁之中。我入学时,很多老师被流放或监禁,不能开展政治活动,所有政党被都查禁了。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进行审查,压制了一切批判。在那样的环境下,你又正好是个年轻人,你如果不关心政治那才叫怪事。即使你希望成为作家,只想当个作家,政治也会找上门,在你的职业训练过程中,你会遇到种种来自政治的麻烦、障碍和挑战。”作家可以选择自己作品的主题,但他本人无法选择生活的时代和国度。在专制与民主的对决之中,知识分子不可能抱着一种暧昧的态度。因此,略萨认为,一个作家如果不参与政治活动,则“不足以捍卫我们的社会赖以进步、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价值和观念。”也正像罗曼?罗兰所说:“我不关心政治,但政治要来关心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张扬“为文学而文学”无异于掩耳盗铃。
在60年代的动荡中念大学的大江,是在研读萨特、加缪等法国作家的作品之后,带着敬畏之情,投身于充满激情与梦想的文学事业的。文学既是一次梦幻之旅,也是对现实执着的关注和批判。大江选择的一般都是新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