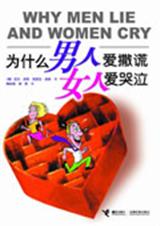请对我撒谎-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来,郝乐意才明白,那些自鸣得意的想法很阿Q,像一片麻醉药,只能在很短的一刹那,让她有点儿快意恩仇的胜利感。而大多数的时间,她的心都是灰扑扑的,像一间陈年老屋,久无人居,地上落满了灰尘,人一走动,就灰尘飞扬,呛得她泪流满面。
第十二章 那些如履薄冰的日子
01
刚回来的那几天,马跃忙着走亲访友,把带回国的礼物送出去。
这天,他从外面回来,陈安娜说问过伊朵了,她没告诉妈妈爸爸那儿有个阿姨,她怕妈妈会哭。陈安娜很震惊,以为伊朵已经懂了大人之间的事,就问她妈妈为什么会哭。伊朵说因为我喜欢“皮蛋”呀。陈安娜就更纳闷了,说这都哪儿跟哪儿了,皮蛋和妈妈有啥关系。伊朵就笑得很诡秘,说“皮蛋”是他们班里的一个帅男生,她很喜欢他,如果他和别的小女孩玩,她就会难过得大哭。爸爸说过他只喜欢妈妈的,可如果妈妈知道他又和别的阿姨玩,妈妈也会难过,她可不想让妈妈大哭,要好多好多糖才能哄好的。
陈安娜边说边抹眼泪说多懂事的孩子,你要再给我闹妖,看我怎么收拾你!
马跃坐那儿不吭声。
陈安娜有些紧张,“马跃!”
马跃嗯了一声。
“你该不会和乐意说了吧?”
马跃摇摇头说:“可我觉得她好像知道什么了。”
陈安娜却认为他是做贼心虚,因为她旁敲侧击地过问伊朵,盘问得也很仔细,像伊朵这么小的孩子,根本就没撒谎骗人的心计。说着瞪马跃,问他该不会蠢到每次和小玫瑰约会都开着摄像头吧。马跃说没有,小玫瑰一般都是晚上去找他,那会儿正好是青岛的上午,郝乐意正忙着上班呢。后来小玫瑰把丈夫送到医院去了,白天才有时间找他。
娘俩分析来分析去,就是分析不出郝乐意为什么会这样,难不成她外面有人了,陈安娜想来想去,觉得不可能,楼上楼下地住着,郝乐意的一举一动她都收在眼里。除了上下班和周末出去买东西,她很少出门。虽然马跃搞不明白郝乐意到底是因为什么不理他,可陈安娜分析郝乐意是不是有了外遇,这让马跃很不高兴,其一,他不相信郝乐意会出轨;其二,他接受不了郝乐意出轨。
自己刚刚出轨完毕,却有这样的心态,他也觉得很荒诞。可出轨就是这样,向来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因为人在出轨的时候,都不觉得自己对不起配偶,也并没因出轨而减少对配偶的爱。而发现对方出轨就不一样了,那感觉,就如同配偶伙同一个混账东西盗走了自己含辛茹苦积累的家产。
在爱情上,无论男女老少,个个都是独裁犯,马跃也不例外。
马跃沉着脸不说话,陈安娜生气了,“你甩脸色给谁看呢?我替你操心还操出罪来了?”
马跃也不示弱,气哼哼地说:“出轨的是我,不是乐意,您能不能别瞎联想?”
陈安娜看着愤愤的马跃,觉得好气又好笑,啧啧道:“儿子,你的意思是我这当妈的愿意你戴几顶绿帽子?你戴了绿帽子,是有我好处还是能光宗耀祖?”
马跃一梗脖子,没吭声。
“我奇怪她不知道你那边作的祸,你拿着研究生文凭回来,按说她应该高兴才对,干吗不理你?”
娘俩正各占了沙发的一头生气呢,马光明两手拎了菜回来了。他说马光远要摆一桌给马跃洗尘。
陈安娜瞥了他一眼,没吭声。
“没意见我就让我哥安排了啊。”
陈安娜没好气地说:“马跃是我儿子,要摆洗尘宴也用不着他们!不就有俩臭钱想显摆显摆吗。”
“不要说李嘉诚,就咱青岛市,比我哥有钱的人,多的是吧?我哥才算个老几。”
陈安娜悻悻地说:“你才知道啊。”
马光明在鼻腔深处嗯了一声:“他们比我哥有钱,可怎么不显摆显摆给咱马跃摆洗尘宴?”说着,拿食指尖敲着饭桌,“说到家!跟谁有没有钱、显摆不显摆没关系,是血缘,是感情!是我哥亲咱马跃!”
“要亲他亲他自己儿子去,我马跃有的是人亲有的是人疼!不就想跟我摆个高高在上的谱儿吗?”说着陈安娜比画了一下,“马光明,这么大钻石值俩钱吧?”
马光明啊了一声:“值几个亿吧。”然后张嘴等她下文。
“你哥就是吊这么大个一钻石在我跟前晃悠,我都不正眼瞧的。”说着,不屑地哼哼了两声,“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似的,一月发三千块钱就把骨气卖了。”
这几天马跃又累又乏,烦得要命,本想回来清静一会儿,可父母又掐上了,就起身说你俩慢慢吵着,我上楼了。
马光明话还没说完,就追到了门口,刚喊了一嗓子,就被陈安娜拽了回来。马光明本以为她这是故意和自己作对呢,就见陈安娜嘘了一声关上门,说儿子烦着呢,别招惹他了。
马光明愤愤地说:“有个你这样的妈,还烦呢,他没疯就不错了。”
“跟你说正经事!”陈安娜压低了嗓子,把郝乐意这几天一直不答理马跃的事说了。马光明有点纳闷,问为什么。
陈安娜就气,说还能因为什么?定定地看着他。
马光明挠头,就手捞了根牙签塞里嚼着。
陈安娜一把把牙签从他嘴里抽出来,扔烟灰缸里。她简直要气急败坏了,真搞不明白男人是种什么动物,脑子就跟不分岔的隧道似的,一条道钻到黑。
马光明却被她愤得不耐烦,让她有话直接点儿,他累得慌,不愿意费脑子。说着,不经意似的,又拿了根牙签,一下一下地剔着门牙缝,好像那儿塞了多少东西似的,其实什么也没有。
陈安娜嘟囔着,你也得有脑子可费的,又把猜测郝乐意出轨了的事说了一遍,叹气说:“虽然我没看中郝乐意,可孩子都这么大了,真不愿意他们两口子再闹腾。”
马光明瞪着她,像瞪外星生物似的,冲着地板狠狠呸了一声,牙签就落到了地上,“死驴不倒架子!你没看中郝乐意,咱儿子有那么牛啊?”
陈安娜有些自得,“以前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可现在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现在他还是一个脑袋两条胳膊两条腿!”马光明恼怒地道,“我说不让他去不让他去!只要他脚踏实地,不拿英国研究生文凭照样有工作干有工资发!你非让去,这下可好!他去了一趟英国,人本事没长一点,花花肠子倒长了不少!”
陈安娜的眼泪又刷地下来了,“都怪我!你怎么什么都怪我?”
马光明气得在家兜兜转,瞥着泪眼婆娑的陈安娜,猛地扇了自己一耳光,“都怪我大老粗,没本事!”
02
在陈安娜办理正式退休的前一天晚上,马光明宣布,为了响应陈安娜自尊自爱自力更生的伟大号召,他要亲自操办一桌宴席,第一是欢迎陈安娜卸下校长职务,正式回归家庭。从此以后,她的头衔只有马光明的老婆、郝乐意的婆婆、马跃的亲妈、伊朵的奶奶;这第二呢,是给马跃洗尘,所以呢,要邀请马光远和郝多钱全家。
马跃有点意外,说伯父不是要给摆酒吗?
“要是单纯因为你,我就让他摆了,可你妈是我老婆,自己老婆的事哪儿能交给别人办?”马光明看看陈安娜,“陈校长,这下你满意了吧?”
陈安娜挺开心的,但她想最后端一次陈校长的架子,就抿着嘴,微微一笑。
这几天,郝乐意能感觉到家里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好像谁都知道马跃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似的,就更觉得苍凉了。但,当着公婆的面,为了不让他们难受,她尽量自然地跟马跃说说笑笑。上了楼,基本不说话。马跃走到身边,她装看不见,只要不喊着她名字说话她就当他是在自言自语。必须回应的,能用一个字回答完的她绝不用两个字。虽然马跃像只丧家犬似的跟在她身后转来转去显得很可怜,她却非常烦,甚至觉得马跃赖皮。哦,在外面偷了腥,还想在老婆跟前扮演温暖的情圣!当她是傻子啊?
有时候,伊朵会跑上来,也没什么事,喊声爸爸妈妈就跑回楼下。郝乐意就知道她是陈安娜派上来当侦察兵的,看看他们两口子在家干吗,是不是各忙各的谁都不答理谁。所以,只要伊朵上来,她就会拿个水果,让伊朵下楼之前给爸爸送过去,小孩子天真,口袋里有糖一定只给自己最好的朋友,所以郝乐意让她给马跃送水果,她就会觉得妈妈好爱爸爸呀。
其实郝乐意想的是,关于马跃出轨,没必要质问了,所谓质问不过是希望他把谎撒得圆一些,帮着她自欺欺人。现在,她需要耐心,他拿到硕士证书了,相对以前工作应该好找,等他找到工作,她就心平气和地和他说:马跃咱俩离婚吧。如果马跃问为什么,她就说:所有能说给别人听的离婚理由,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我不爱你了。
为什么不现在和他离?因为马跃刚回国,气还没喘匀一口,现在就说离婚,她怕受了打击的马跃会破罐子破摔,连工作都不正经找了。虽然离婚之后他们就是不相干的两个人了,可再不相干他也是伊朵的爸爸,在他准备上坡的时候兜头来一棍子,她做不到。
03
因为要请客,马光明提前好几天就张罗着准备东西,让陈安娜帮他收拾客厅,怕人多了坐不开。虽说马光明要办酒席庆祝她解甲归田是件挺让人感动的事,可一想到还要请郝多钱和田桂花这两个冤家对头到家里来,陈安娜就无比的不痛快,遂耷拉着脸说就:“咱家这小破客厅,光一个田桂花就够撂的了,其他人怎么办?你打算墙上砸钉,挂墙上?”
马光明说:“咱把田桂花垫底下当垫子,多好,纯天然的,还是人体恒温的。”
陈安娜扑哧一声就笑了。马光明知道,只要他肯糟践田桂花,陈安娜就会把他划拉成同盟军。这两天,马光明一直在想,现在不比以前,以前大家都上班,吵完了架,还能上班避一避,一天下来,气也就消了。可退休了就不行了,生了气也没地方避去,在家大眼瞪小眼地互瞅着,这气猴年马月才能消啊?气这东西,憋多了就成糟蹋健康的祸害了,大家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不容易,可不能刚要享受享受了就着急忙慌地去阎王爷那儿报到。马光明这么想着,就叫了一声安娜,用从未有过的温情,把陈安娜叫愣了。
“以后啊,咱俩不打了。你呢,退了也别在家闲着,去上上老年大学。我呢,继续在咱哥酒店上班,省得你看着我烦。”马光明伸了个懒腰,笑着说,“你这辈子啊挺亏的,跟了我你算是和称心如意彻底断了关系。”
“接着说!”陈安娜吭哧吭哧地擦地板,她已经习惯了,马光明从来不说人话也不说软和话,前面说了一句软和话,后面肯定有比磨盘还硬的石头等着往下砸。
“没了。”马光明顿了一会儿,“你真应该嫁个文化人,也甭太大的文化,跟我哥似的就行。”
“你哥娶了杀猪的。”陈安娜没好气地说。
马光明就张着大嘴就笑了,“可不,真**的……怎么会这样,我是大老粗我娶了个校长,我哥是文化人却娶了个杀猪的。”然后一阵哈哈狂笑说,“要不,我和你一块儿上老年大学,也变个文化人?”
陈安娜哼了一声,继续吭哧吭哧地擦地板,擦着擦着,她就觉得胸口一阵阵地疼,不是病理性的疼,而是那种明知被命运调戏了,还要强颜欢笑的苍凉之疼。这一切,不是因为她做错了什么,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