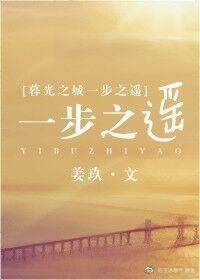焚心之城-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刚刚被剥去外皮的水果的肉。看得出,芬很年轻。
我将她孩子一样柔软的身体轻轻抱起,放回床上。芬被惊醒,恍惚地看着我,目光里有被吓到的恐惧。我向她笑一下,让她似乎想起了昨夜的经过,慢慢坦然,重新闭上眼睛。
穿好衣服,想下楼去买些吃的,但有些担心芬,站在房门口看着伸展手脚睡着的她犹豫不决。
芬的乳还小,应该只在我的手掌里那么大,但很耸,显得挺立。两根细细的锁骨叉向她的脖颈,连着瘦长的胳膊。小腹还没有一点多余的赘肉,是少女的平坦。从光滑的后背弯曲而下的线条勾勒出圆润的臀和美丽的腿,腿间黝黑的毛丛里那一点粉红色微微地张开,显得更加诱人。芬的皮肤是年轻的紧致,反映着照在上面的阳光,像绷在骨骼上的白色缎子,柔滑的光芒刺目,衬得乳上的晕异常的粉嫩,腹下的毛尤其的黑。
我突然感觉似乎头一次看出女人的美,并被惊讶得目瞪口呆。心里也越来越紧张,好像要控制不住。我咽下口唾沫,急忙出门。
赶回来时芬已经不在,床上是叠得整齐的被褥。除了桌上喝剩一半的啤酒,好像没有其他证明她来过的痕迹可寻。我感觉有些空落,拿起啤酒继续喝,一边在房间、客厅、卫生间里转进转出,直到一滴不剩。
第七章 寻找爱
…………………………………………………………………………………………………………………………………………
芬曾一直为自己的不幸而心酸,从父母离婚那年她六岁开始。
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发呆,空洞的眼睛里是失去色彩的光。芬从那时起变得不爱讲话,也不再因为父亲或母亲来接自己而高兴,也不因为他们或她们给自己买什么而笑逐颜开。这样的表现曾让幼稚园的阿姨很惊讶,搞不懂如此小的一个女孩子为何如此地高深莫测。
芬很高兴自己能长大,进入都是小朋友的学校就读。但她看不惯那些小朋友和来送的大人那么黏黏唧唧的没完没了,觉得他们不会有什么出息。老师对拼命要求独立的芬很赞赏,鼓励她继续下去。她却不知其实在芬幼小的心里埋藏着多少无奈的委屈。芬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向亲人以外的人那里去寻找从亲人身上得不到的温暖和关爱,芬从小学就开始轰轰烈烈地恋爱。
她的第一个男朋友是她的同桌,一个戴着难看的矫治眼镜,从正面看来除了硕大的镜架以外别的都不甚分明的呆傻男孩。芬常常将好吃的零食分给他,偶尔给他买他买不起的电脑游戏光盘和漫画书,所换回的是他帮忙背着她的书包,陪她一起走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直至毕业。
进入住校的私立高级中学的第二天,那个男孩除了那副硕大难看的眼镜以外就没有别的残留在芬的记忆里。芬也常常奇怪怎么会将他忘得如此干净,并暗暗责备自己的无情。后来她慢慢明白,其实不是她已经忘记,而是因为他和自己心中被深埋的那段关于寒冷孤独无助的痛苦记忆联系得太过紧密而不愿意被自己想起罢了。
芬的第二个男朋友是个高大的阳光男孩,但他粗线条的生活作风和极端自私的个性却让芬大吃苦头。
走到最后,在芬心里只剩下他光鲜外表带给自己少女虚荣心那点可怜的满足。所以在一起的三年时间里芬除了让他拉着自己的手,间或偶尔让他亲吻自己的脸颊以外,没有给予他任何她认为多余的东西。所以当毕业分手时,芬不但不觉得痛苦,反倒因为解脱开这种没有意义的束缚而觉得轻松和高兴。
现在回想起来,在大学里遇到的勇是她真正感情生活的开始,也是她付出所有一切去爱过的全部。
其实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勇实在算不得出众,只是个不论各个方面都稀松平常的男孩子。想当初当芬和他表白时,勇好长时间都以为有那么多人追求的芬是在戏耍自己,和自己开玩笑。直到芬将自己的身体交与他,他才半信半疑地接受这个如此不真实的事实,并开始了对芬肆无忌惮的占有和玩弄。
芬知道自己又犯了和中学一样的、过于追求两极化的错误。勇其实是个非常自卑的男人,尤其在各个方面都很出众的芬的面前,就像一只丑恶的公老鼠看见拜倒在自己面前的漂亮母猫一样,永远都觉得不放心和不适应。
但从根本上来讲,芬的内心是软弱和孤独的。
童年时因为父母的离异而留下的那一大片黯淡的阴影并不因为她的不肯面对而有所缩减,反倒因为和勇越来越强烈的对立导致的失望而变得越来越突兀易见。芬知道自己和勇之间的问题有一部分是因为自己刻意要求他和躲避自己内心压抑的结果,所以在心里她常常对勇怀着不便言明的歉意,并一味地姑息迁就着他。
芬却不知她这只漂亮的母猫越是向后退缩,勇这只猥琐的公老鼠越要向前逼迫,以满足他心里龌龊的安全感的欠缺。两个人之间就这样纠缠不清地相互怨恨着、厌烦着,消耗着旺盛的精力,并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消耗中完成了生命里最原始的平衡过程,直到两败俱伤。
大学毕业后,芬为了更加彻底地控制勇,将他弄到了自己父亲开设的公司里上班。
芬的父亲目光毒辣,第一眼便看穿勇低俗又无能的本质,不肯将重要的工作交与他,并一再劝芬和他分手。芬对父亲本存着对立的敌视,自然不肯听从,反倒更加放纵勇。
就着这股力量的维系,两个人又坚持了一年多些。直到数天前芬发现勇和公司的一个女孩子拉着手亲热地从宾馆里出来,才如梦初醒。
昨天芬偷偷跟踪勇,发现他和那个女孩子进了这座楼的某个房间。从外面望过去,可见两个印在窗帘上的人影亲密地依靠在一起没完没了。
芬忍不住泪如雨下。她知道一切都完结了,只剩下对伤心的清算。
开车离去,回到家里躺一会儿,不甘心,又起来到那座楼下张望,却见窗上的灯光已经熄灭,而勇的摩托车还停在那里不曾动过。
有好一会儿,芬的精神恍惚到几近昏迷的地步。
她靠在楼对面的路灯杆上才勉力支持自己不倒下,并在心里慢慢地清理着自己曾经那么珍视的、今后却不再需要的记忆垃圾。她为自己曾经的付出而痛苦不堪,同时也认清一直以为的所谓爱情其实不过是自己吹给自己来哄慰自己高兴的一个五彩斑斓的肥皂泡罢了。
如今破灭后,除了包裹在里面的、已经被腐臭污染得令人窒息的空气以外,再无其他。
从车子里拿出烟,点燃一根,靠在路灯杆上不自然地吸。
芬看到那个穿着拖鞋、扛着啤酒走过的男人时,竟突然觉得他很好笑,并奇怪,一个肯在半夜出来买啤酒喝的男人该是个什么样的呢?会不会比勇强一些?或者不如勇?就在那一刻,芬在心里突然有要报复的强烈欲望。
报复谁呢?不知道,但她仍旧向他喊一声。
喊过之后自己又怕得不行,以为要惹祸上身。但伴随恐惧同在的还有放纵自己的快慰,并借此舒缓了压抑在心头的憋闷。
她喜欢坐在啤酒上喝啤酒,在这样凉爽的夏夜里。她从来不曾如此过,不在意他看向自己的眼神,也不在意半裸在他面前的乳和露出的粉色内裤。并觉得自己若是当个妓女说不定也不错,→文·冇·人·冇·书·冇·屋←至少这一夜就这个样子吧。
所以当君来脱芬的衣服时芬觉得很自然,心里一点别扭的感觉也没有。她甚至开玩笑地碰他的下体,那个一直软塌塌的东西,并暗自奇怪它为何不像勇那样有所反应。
芬也曾为自己的主动而暗暗地担心。但想着既已经如此,何不索性一直到底多么地痛快?却不想最后失望的是自己。
芬蜷在君的怀里,感觉着和勇毫不相同的、其实没有任何区别的肌肤的温暖,心里觉得不是滋味。难道自己连做妓女的魅力都没有吗?难怪勇要离开自己而去。芬就在这样的纠结中恍惚入梦。
直到第二天早晨君来抱自己到床上。
在那一刻芬在心里突然涌起从不曾有过的依赖感,虽然她解释不清这种感觉所为何来,但却那么清晰地浮现在那里,任她反复审视,就像自己此时赤裸着躺在这里任他反复地看一样不加掩饰。
不知为什么,芬在心里那么希望他扑上来抱住自己,进入自己,完全占有自己,把自己彻底地从灰暗失败的过去中解放出来。但这次她又失望,他匆匆地走掉。她咬着牙在心里骂他“废物”。
离开之前,芬仔细打量这间屋子的每个细节,窗上挂的白纱窗帘已经肮脏得看不出本来颜色;桌子上的垃圾堆叠得不成样子;地上的灰尘多得有些粘脚;墙角堆着脏衣服。
钻进汽车里,芬突然无法抑止地大笑起来,直到眼泪流出,却仍停不住。后来慢慢变成呜咽,芬趴在方向盘上哭了好一会。
第八章 对自我的复印
…………………………………………………………………………………………………………………………………………
上午英打电话过来说晚上在起子的酒吧里将举行一个小型的文学青年聚会,让我一定不见不散。我知道不过又是个醉的借口罢了,随意答应,并不当真。
然后就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我们嘴里说的所谓‘文学’到底是什么。
从前这个字眼对我来说有着和‘生命’、‘和平’、‘成功’、‘事业’等等这些字眼一样伟大和庄严的沉重颜色,但如今却被酒精冲洗得日渐苍白粗糙,就像被风化的雕像,当平整了原有的凹凸之后就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而已,仅代表那个年龄的天真和幼稚,别无其他。
但我仍旧尊重这两个字,就像尊重我的父母一样,因为感觉需要如此。
“你的生命里总要有点神圣的什么存在,不论是信仰也好,道德也好,信念也好,为之奋斗的目标也好,总之要有那个在,是你赖以活下去的借口。”??不记得谁曾对我说起这句话,一直记得,觉得有道理。
或许‘文学’就是我活下去的借口吧,虽然明知自己在这方面低能,不论如何也不会怎样,就像阳痿者面对美丽妻子的无奈。但仍旧执著着不肯放弃,其中虽然有虚荣的功利心在,更多的还有‘是自己活着的目的和意义’这样的自慰,好像只有如此,每天的平淡慵懒才值得原谅似的。
这是多么可悲的自欺心态呵。
而这世界上有多少人需要像我这样自欺之后才能酣然入睡,醒来后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心安理得地继续着每天需要继续的琐碎又无聊的一切活着呢?
下午到书店闲逛,翻阅架子上新出版的一本本书,闻着好闻的味道暗暗地感叹这么好的纸印着如此垃圾的文字是巨大的浪费,就像我如此美好的青春时光却被酒精淹没一样可惜但没有办法改变。
这世界上有多少无可奈何的事情呵,恐怕要远远多于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不明白地球为何还这么健壮地存在着而没有被这么多的无可奈何干掉。
也或许是早晚的事情吧,我猜。
卖CD的女孩子有一双大到空洞的眼睛,没有内容的目光是小白兔那么无辜地望着大灰狼手里的胡萝卜的软弱。我不堪被如此注视,只好装模作样地拿起一张端详。
“有巴赫的吗?”她摇摇头。
“没有?”我逼视她,喜欢看那么大的眼睛里的目光慌乱躲闪的惊恐。
“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懂这个??”她好像要哭出来似的。
为了减轻她的难过,我胡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