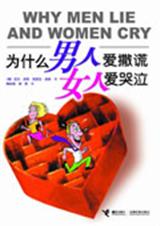城堡里的男人-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塔格米先生拎着他的公文包,里面装着柯尔特44型手枪,离去了。
我出来时一如我进去时一般,他想。依然在寻找。如果我要重返这个世界的话,依然没有我要的东西。
如果我买了一件那种古怪的、不敢确认的玩艺儿又会怎么样呢?留着它,反复检验,反复琢磨……我随后能通过它找到回来的路吗?我表示怀疑。
那些玩艺儿是他的,不属于我。
然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路……那就意味着有一条“路”。可我再努力也找不到它。
我妒忌他。
塔格米先生调转头,又往那个店走去。
奇尔丹没有回转去,他一直站在门廊里打量着他。
“先生,”塔格米先生说,“我来买一件,随你挑一样。我不信它,但我眼下正在抓救命稻草。”
他跟着奇尔丹先生又一次穿过了店堂,来到玻璃柜前面,“我并不相信。我会随身带着它,隔一段时间就看看它,譬如说隔几天看一次。如果两个月后我没看出……”
“你可以把它还过来,完全信得过。”奇尔丹先生说。
“谢谢你。”塔格米先生说。他觉得好过些。有的时候你必须冒点险,他下定了决心。没有什么丢人的。相反地,那是聪明的、认清形势的标志。
“这会使你平静的。”奇尔丹先生说。
他拿出一个小巧的银三角圈圈,饰以空心的坠子。底下是黑的,上面亮灿灿的,很有光泽。
“谢谢你。”塔格米先生说。
塔格米先生坐人力车到了普斯茅思广场,那儿有个对外开放的小公园,坐落在卡尼大街的斜坡上面,从那儿可以俯瞰地方警察局。他在阳光下的长凳上落座。鸽子沿着人行道觅食。还有些长凳上,那些不起眼的人在看报纸,或者在打盹。四处的草坪上还躺着些人,差不多都是睡着的。
塔格米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袋,上面标着罗伯特·奇尔丹先生的店名,他坐在那儿双手捧着纸袋,觉得暖烘烘的。于是他打开了纸袋,拿出新的所有物来欣赏,这个只有老年人和小草、小径的公园很幽静。
他拿着银线圈圈。在正午的阳光照射下,就像是箱子顶上稻穗之类的小件饰物,不用杰克·阿姆斯特朗放大镜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要么一一他就低头凝视着它,就像那些贵族所说的“奥妙”玩艺,像微缩点,一切都能收进去。不论是大小还是形状,至少隐隐约约都像。他继续专心致志地研究它。
它像罗伯特·奇尔丹先生预言的那样会来临吗?5分钟,7分钟。我一直坐下去。天哪,时间会使我们转手把它卖掉。我拿的是什么玩艺儿,难道还存在时间吗?
原谅我吧。塔格米先生顺着那弯弯曲曲的线路想着。压力总是促使我们奋起行动。很遗憾,他只得把这东西放回袋二f咀。最后又怀着希望地看了一眼,他再次仔细地检查一下他所拥有的一切。他像个孩子似的自言自语。模仿天真,仿照信奉。在海滨,随便摁一下,就能使贝壳类动物伸出头来,倾听着海洋智慧的喋喋不休。
这次用眼来代替耳。进人自我,告诉我做了什么,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理解浓缩为一个有限的弯弯曲曲的银圈圈。
问得太多,因而一无所获。
“听着。”他低声对银圈圈说,“销售的情况给人很多指望呢。”
如果我狠劲摇晃它,就像捧着个老不走的旧表。我上下摇了摇。或者像投骰子游戏。要唤醒它内在的神性。也许他睡着了,也许他正在旅行。使人愉悦而又有力的嘲讽。也许他正在追寻。
塔格米先生又一次狠劲地上下摇晃那个攥在手心里的银圈圈,大声呼唤它。他又仔细查看了一下。
你这个小东西,你是空的,他寻思。
他告诫自己,要诅咒它,吓唬它。
“我的耐性就要到顶了。”他低声嘀咕。
然后呢?把你扔进阴沟吗?吹吹气,摇摇,再吹吹气,让我赢吧。
他大笑起来。裹在这暖烘烘的太阳里昏头昏脑的。瞧一瞧还有谁跟着来了。现在就窥视一下,像罪犯似的。但他没看见谁。老年人都在打瞌睡。那是解脱的好办法。
他发现什么招数都试过了,祈求,默祷,威吓,甚至卖弄大道理。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只能呆在这里。它拒绝了我。机会也许会再来。然而,正如吉尔伯特说的,那样的机会不会再来了。是这样的么?我觉得是的。
是孩子的时候,想法也是孩子气的。但我现在已把孩子气的东西收起来了。现在我必须在其他范围内寻找。我必须以新的方式追寻下去。
我必须科学点。每次进入都被逻辑分析弄得殚精竭虑。要以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贵族态度自成体系。
他用手指塞住右耳,摒弃车辆和其他分心的噪音。接着他紧紧地捂着银圈圈,手背拱起成贝壳状地贴近左耳。
没有声响,没有类似海洋般的呼啸,甚至连内心的血流澎湃的喧腾声也没有。
那么还有别的感官能够领悟这个神秘么?显然听是没用的。塔格米先生闭上眼睛,开始触摸这个玩艺儿表面的每个部分。没有感触,他的手指告诉他什么也没有。闻呢?他把这个银圈圈凑近鼻子猛吸。只有微微的金属味,但那传递不了什么意思。尝一尝,他张开嘴巴偷偷地将这个银圈圈放进去,像个核桃似的咯嘣一声,当然得忍住不要咀嚼。没有什么意思,只有冰凉的硬味道。
他又把它放在手掌上。
最终又回头看这一招。看是感官的最高层次,希腊人优先考虑的准则。他得每一天都转动着那个银圈圈,他得从每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它。
我看见了什么?他自问。由于长时间耐心艰苦的研究。让我面对探究这东西的真理之路在哪儿?
算了吧,他对那个银圈圈说。你就说出那神秘的内情吧。
就像从深水里扯出来的蛙,他想。攥在手心里,下达指令宣布在水的深渊下面藏着什么。但在这里蛙连生气也没有,它悄悄地窒息,变成了石头、泥土或矿石。了无生气,在它熟悉的坟墓世界里变成了坚硬的物质。
金属是土形成的,他一边细细察看一边琢磨。从地底下,从那个最为底部、最为密集的领地出来的东西。巨人居住的洞穴,总是阴森幽暗的。“阴”界,有它最令人抑郁的方面。那是尸体腐烂、溃败的世界。还有渣滓。所有死掉的东西,滑落下来,一层又一层地在底下腐烂。那是个永不改变的魔鬼的世界,那个时代的世界。
但是在阳光下,那个银圈圈闪闪发亮,辉映着阳光。塔格米先生想到了火。那就完全没有阴冷和黑暗,没有沉重与委顿,只有生命的悸动。天国,阳界的方面:九重天,仙境。很适合于艺术工作。是的,那是艺术家的工作,从黑暗寂静的地下取出矿石,把它做成辉映着天穹之光的东西。
如同赋予死者的生命,尸体变成燃烧着的炫耀,过去服从于未来。
你是什么东西?他问那个银圈圈j黑暗死气的阴间还是辉煌生气的阳界?那银圈圈在他的手掌里跳动,使他眼花缭乱。他眯缝着眼睛,现在只看见火在飞舞。
阴的身体,阳的灵魂。金属和火统一了。外部的和内在的,我的掌心里就是微观世界。
这里讲到的空间指什么?垂直的上升。直上到天国。时间呢?进入无常的光的世界。是的,这玩艺已经流溢出它的精气:光亮。我注意地凝视着,我不能旁顾。我再也控制不住,为那闪着微光的东西而着迷,被符咒镇住了。再也没法摆脱。
现在对我说话,他对它说。现在你已诱惑了我。我想听见你的声音,从那眼花缭乱的清晰的白光中吐出,恰如我们期望仅在来世的存在中见到什么。但我不必等待死亡,等待我的精气的腐朽,它正徘徊着寻找一个新的子宫。一切令人惊恐的大慈大悲的众神,我们将躲过他们,还有那如烟的亮光。男女们在性交,除了这亮光之外的万事万物都在性交。我已准备好无所畏惧地面对死亡。看好,我不会退缩。
我感觉到因果报应的热风向我袭来。然而我坚持住。我的锻炼是正确的,我必须不畏缩于那清晰的白光,倘若我畏缩了,我将再次重新进人生与死的轮回,根本不知道自由,从未获得过解放。幻境的面纱会再次落下来,如果我……
那光消失了。
他手里握着的依然是那个硬邦邦的银圈圈。阴影遮住了阳光,塔格米先生抬眼往上看了看。
一个穿蓝色制服的高个警察正笑眯眯地站在他坐的长凳边。
“哎?”塔格米先生吓了一跳。
“我正在观赏您解难题呢。”警察说着就走上了小径。
“难题?”塔格米先生应声道,“不是什么难题。”
“那是不是你必须解开的小难题中的一个呢?我的孩子有一堆那种玩艺。有些还挺硬的。”那个警察往前走了。
塔格米先生认为很败兴。去你的。让那个白种野蛮人,那个尼安德特的美国佬给搅了。那个智商低于人类的人还以为我在弄小孩子玩的玩具。
他从凳子上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必须镇定下来。为糟糕的低级的侵略主义的种族主义者而痛苦,不值得。
不可思议的不得赎救的激情涌上他的胸臆。他穿过公园,一直走下去,他对自己说。精神在宣泄。
他走到公园的边上,上了人行道,卡尼大街,车水马龙的轰鸣声。塔格米先生站在路边。
没有人力车,他只好沿着人行道步行,他汇人了人群,你要人力车时总找不到。
天哪,那是什么?他驻足,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个不成形的东西悬在地平线上,令人惊骇。像是噩梦,滑行铁道悬浮在空中,视线模糊了。巨大的金属和水泥建筑竖在半空中。
塔格米先生转身对一个行人,一个穿着皱巴巴西服的瘦子,指点着问:“那是什么?”
那人咧嘴笑着说:“很可怕,是吗?那是全封闭快车道。许多人认为它挡住了视线。”
“我以前从未见过它。”塔格米先生说。
“你很幸运。”那人说着走开了。
疯狂的梦。塔格米先生想。必须振作起来。人力车今天都跑哪儿去了?他开始加快步伐。整个的图像有着阴郁的、如烟幕般的坟墓世界的色调。有烧焦的味道。暗淡的灰色建筑,人行道,尤其是人们来去匆匆的步伐。还是不见人力车。
“人力车!”他边加快步伐边喊道。
毫无希望。只有轿车和公共汽车。汽车就像庞大的残忍的碾压机,形状奇异怪诞。他不愿看它们,抬起头一直往前走。特别邪恶的本性歪曲了他的视觉。一种障碍在影响他的感觉空间。地平线歪曲得不成直线。就像那猝然打击的乱视现象,真要命。
必须缓口气。前面有一家小快餐店。里面只有白人,都在吃晚餐。塔格米先生推开木头的弹簧门。有股咖啡香味。墙角有架奇形怪状的电唱机在那儿哇啦哇啦响着。他退缩了一下,径直走向柜台。所有的凳子都让白人占了。塔格米先生大声喊叫起来,有几个白人抬眼看着他,但没有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没人把座位让给他。他们继续吃饭。
“我坚持!”塔格米先生大声对第一个白人,对着那人的耳朵吼叫。
那个人放下他的咖啡说:“瞧呀,东条英机来啦。”
塔格米先生看看别的白人,全都敌视地望着他,没有人动弹。
恶魔,塔格米先生想。热风吹向我,谁知道哪儿来的。这是什么梦幻?那精气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