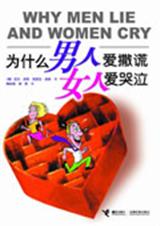城堡里的男人-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为什么要?”奇尔丹开腔问道。
保罗说:“像这样的首饰……”他又一次拿起胸针,瞄了一眼,然后关上盖子,把盒子还给奇尔丹说,“能够批量生产,要么用金属,要么用塑料,用一个模具。要多少可以生产多少。”
过了一会儿奇尔丹说:“‘无’是怎么回事?那些产品里还有‘无’吗?”
保罗不吭声。
“你建议我去见他?”奇尔丹说。
“是的。”保罗说。
“为什么?”
“护身符呀!”保罗说。
奇尔丹瞪大双眼。
“幸运护身符,穷人戴的护身符,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有人售护身符,你知道的,大部分老百姓都相信魔法、咒语和麻醉药。我听说,这可是笔大生意。”保罗的脸上毫无表情,语气平板。
“听起来,”奇尔丹慢慢说来,“似乎这里面可以挣大钱。”
保罗点点头。
“这是你的主意吧?”奇尔丹说,
“不是。”保罗说,他又不吭声了。
奇尔丹想那就是你的雇主,你把首饰给你的上级看,他认识个进口商,你的上级,或者某个职位比你高、影响比你大、权力比你大的人物,某个有钱有势的人,他和进口商有联系。
奇尔丹意识到这就是你为什么还给我的原因吧。你一点也得不到。但你知道我明白,我会去找这个地址,去拜访这个人。我是得去,我没有其他选择。我会出租设计图,或打折扣卖给他们,我和他们之间还要签订协议。
很清楚出自你的手,全部都是,你设法阻止我或者和我争论,那真不是滋味。
“你现在遇到机会了,”保罗说,“会暴富起来。”他继续目视前方。
“这主意给我异乎寻常的感觉,”奇尔丹说,“靠把这些艺术做成幸运护身符,我简直难以想象。”
“因为那不是你的生意本行,你要奉献于这个别具风味的秘密,我自己也一样。还有那些人,他们不久就会去造访你的店,我刚刚提到过这些人。”
奇尔丹说:“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不要过低地估计受人尊敬的进口商所提出的可能性。他是个精明人,你、我——我们都不会了解广大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会因得到用模型批量生产的一模一样的首饰而非常高兴,当然我们是不要的。我们所必须指望我们拥有的是独一无二的,至少是少数人拥有的稀罕物。当然,有些东西的确是权威的,而不是模型的,或者复制品。”他一直将目光越过奇尔丹,凝视着空空的空间,“不要成千上万的铸造品。”
奇尔丹想弄清楚,他是不是对正确的概念也制造混淆?诸如我店里的那些历史文物是不是赝品呢?且不说他个人的许多收藏品。他的话里似乎有一点暗示的味道。他冷嘲热讽的弦外之音告诉我一种完全不同于表面形式的信息。模棱两可,就如同你在神谕里遇到的那样……就像他们说的,东方智慧的品行。
奇尔丹认为他实际上在说,你是什么东西,罗伯特?他是神谕称之为“下等人”,或者是所有的好事都是为他的人?现在要作决定,你要么走这条道,要么走那条道,不可能走两条道,到了选择的时候了。
上等人会走哪条道?罗伯特·奇尔丹自问。至少可以根据保罗的意见来选择。我们面前并没有一位修炼千万年的天才,一位令人鼓舞的智多星,只有一个年轻的日本商人的意见。
不过起码有了一个核心,如果保罗所说的“无”,这种情形的“无”就是:不管我们个人多么不喜欢,但毫无疑问,现实就在进口商的那一方,正如神谕所言,我们的意图不好,但我们必须适应。
毕竟,那些原件还可以在店里销售,卖给行家,像保罗的朋友这样的鉴赏家。
“你再斟酌一下,”保罗察言观色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愿意单独呆一会儿。”他朝办公室的门走去。
“我已经决定了。”
保罗的眼睛倏地亮了。
奇尔丹鞠着躬说:“我会照你的建议办。现在我就去找进口商。”他拿起折好的纸条。
奇怪得很,保罗似乎并不高兴。他嘀嘀咕咕地走到办公桌边,他们都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奇尔丹考虑到。
“十分感谢你的帮助,”奇尔丹说着准备离去,“如果可能的话,哪天我会报答的,我将记住。”
但年轻的日本人还是没有反应。太对啦,奇尔丹想,我过去常说什么来着,他们是不可思议的。
保罗陪他走到门口,似乎还在想什么。他突然冒出一句话来:“美国的艺人用手工制作这些首饰,对吗?用他们的体力劳动?”
“是的。从最初的制图到最后的抛光。”
“先生,这些艺人会合作吗?我想象得出他们会去干自己的活儿。”
“我没把握能不能说服他们。”奇尔丹说,对他来说这是个次要的问题。
“是呀,”保罗说,“我也这样想。”
保罗说话的语气里,有一种东西,马上使罗伯特·奇尔丹警觉起来,那里面朦朦胧胧有一种特别的强调,它触动了奇尔丹,毫无疑问他不能模棱两可。他很清楚这一点。
当然,对美国人的努力是一个残酷的打击,整个事情浮现在他眼前。上帝不允许犬儒主义,可他把鱼钩、鱼线和钓饵都吞下去了。一步一步逼我,就是让我沿着花园小径到达结论;美国人的手工制品都不过是些模型制造的伪劣幸运护身符。
这就是日本人如何操纵的。不是自然而然,而是精细地、老练地、总体上地玩弄计谋。
上帝啊!奇尔丹发现和他相比我们简直成了野蛮人。根据这些无情的推论,我们不过是笨伯,保罗没说话,他没有告诉……说我们的艺术品一钱不值。他让我来替他说这句话。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对我的说法懊悔不已,当他从我这里听到真话时,隐隐约约做出了一种文明的歉疚的姿态。
奇尔丹几乎要大声说,他伤透了我的心。然而很幸运,他只是设法使它成为一种思想,和以前一样,他把它藏在内心世界里,秘密地不为外人所知。羞辱了我和我的民族。我是无能的,对此没有报复。我们失败了,我们就这样失败了。微妙得让我几乎察觉不到。其实,我必须在发展中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保罗的办公室的角落里有一个废纸篓,扔掉它!罗伯特·奇尔丹拿着这个不成形的玩艺,这个充满着“无”的首饰自言自语。
我可以这么干?扔掉它?在保罗的眼前结束这一幕?
他紧握着这首饰时,发现,不能扔,绝对不行,你还指望以后再见这位年轻的日本人吗?
见鬼,我无法摆脱他们的影响,无法控制冲动,所有的自发性动作都被碾碎了,保罗凝望着他,什么也不需说,他的存在就足够了。我的意识陷入了困境,就恰如一根无形的线从这玩艺儿牵到胳膊上,一直缠到心里。
想想看吧。我已经和他们相处得太久,现在想逃掉也嫌太迟了,难以回到白人中去走白人的道路。
罗伯特·奇尔丹说:“保罗。”他注意到自己的声音有点嘶哑,没有节奏,不成调子。
“是的,罗伯特。”
“保罗,我……好……丢脸。”
房子在旋转。
“为什么这么说,罗伯特?”说话语气关切,但很超然,带点关心,凌驾于一切纠葛之上。
“保罗,等一会儿。”他捏弄着那枚胸针,汗水使它都变粘滑了,“我为这件‘无’首饰感到自豪,这些决不是垃圾般的幸运护身符,我反对这种说法。”
他依然辨不出这个年轻的日本人的反应,只有张耳听着,这是惟一的认识。
“无论如何,我要谢谢你。”罗伯特·奇尔丹说。
保罗鞠了个躬。
罗伯特·奇尔丹也鞠了个躬。
“制造了这件首饰,”奇尔丹说,“是美国值得骄傲的艺术家,也包括我自己。因此说它是毫无价值的幸运护身符是对我们的侮辱,我要求你们道歉。”
难以置信的很长时间的沉默。
保罗审视着他,一边眉毛稍稍向上挑起,薄薄的嘴唇抽搐着,是在笑吗?
“我要求,”奇尔丹说。就这些,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现在他只是等待着。
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在想,求求啦。帮帮我吧。
保罗说:“请原谅我的傲慢强加于人。”他伸出手来。
“没事。”罗伯特·奇尔丹说。
他俩握了手。
奇尔丹心里开始平静下来,他知道他挨过了这段时光。都结束了。感谢上帝!上帝此时与我同在。那么其他时候呢?我还敢再敲自己的幸运之门吗?可能不敢。
他觉得忧郁,倏忽间他仿佛站立起来了,一览无余地看清楚了。
他想,人生苦短,而艺术和别的没有生命的东西能长久,无止境地延伸,就像混凝土小道,和平坦的、白色的、不平坦的道路相互交错。我站在这儿,但不再站下去了。他拿起小盒子,把埃迪弗兰克的珠宝放进了大衣口袋。
第十二章
拉姆齐先生说:“塔格米先生,这是亚塔比先生。”
他退到办公室的一隅,那个身材颀长的老年绅士迎上前来。
塔格米先生伸出手来说:“我很高兴亲自会见你,先生。”
一只衰老、干巴的手滑入他的手中,他稍稍地握了握,马上就松开了。他思忖,但愿不要有什么不顺的事。他打量着这位老绅士的外貌,给自己找乐。那张脸有一种坚定、执着的神气,显而易见的机智,一成不变的古代传统清楚无误地写在上面。这位老先生可能体现了最优秀的品质……
接下来,他才明白站在他面前的是特迪基将军,前帝国陆军参谋长。
塔格米先生深深地鞠了个躬。
“将军。”他说。
“第三方在哪里?”特迪基将军问。
“他快来了,有双重理由,”塔格米先生说,“我本人通知到了旅馆房间。”他完全乱了方寸,保持着鞠躬的姿势退后了好几步,几乎回不到直立的姿势了。
将军自己坐了下来。毫无疑问,拉姆齐先生仍然不清楚这个老人的身份,尽管帮着搬了椅子,却并未显出特别的尊重。塔格米先生踌蹰着搬了把椅子坐在对面。
“我们在消磨时光,”将军说,“令人遗憾,然而又无可奈何。”
“确实如此。”塔格米先生说。
1O分钟过去了。两人相对无言。
“对不起,先生,”拉姆齐坐立不安,终于开口道,“我先告退,有事再来。”
塔格米先生点点头,拉姆齐先生走了。
“喝茶吗,将军?”塔格米先生问。
“不啦,先生。”
“先生,”塔格米先生说,“我承认有点担心。我感觉这次要遇到麻烦。”
将军将头侧过来。
‘‘贝恩斯先生,我见过他了,“塔格米先生说,“在我家里接待的,他自称是瑞典人。但仔细看看,就会相信他实际上是个德国人。我说这个,因为……”
“请讲下去。”
“谢谢你,将军。他促成这次会见,使我猜想与德国的政治动乱有关。”塔格米先生没提到另一个事实:他知道将军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到达。
将军说:“先生,你现在正在钓鱼。没告诉一声。”他的灰色眼睛慈祥地眨巴着,不含一点恶意。
塔格米先生接受了指责。“先生,难道我出席这次会议仅仅是出于客套,为了阻止纳粹的窥视吗?”
“其实,”将军说,“我们对维持某种并不存在的假设都很感兴趣。贝恩斯先生纯粹是个生意人,是斯德哥尔摩的托一安工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