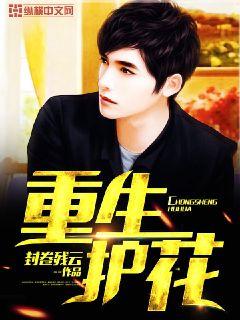皇后重生手册 (皇后当自强)-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没有答话。
然而这个夜里却并不平静。迷迷糊糊的才要睡着,便听到外间有人絮语。
身旁铺褥未凉,却有风透进来,苏恒已不在床上。床头金钩挑落了,橘色的灯火透过缠枝牡丹锦的锦帐,映得床上红艳艳的。
衣服一半搭在床边,另一半却在帐子外面。我想抽过来披着,不想将帐子带开道缝。
苏恒很快便探头进来,道:“朕出去一趟。你收拾好了,先在殿里等着。朕若传禀,你再过去。”
我说:“出了什么事?”
苏恒道:“太后说不舒服。”
我不由就愣了一愣,道:“传太医令了吗?”
苏恒就皱了皱眉头,道:“朕刚刚命人传了。”
我与苏恒独处时,向来是不让外人伺候的,我身上连件蔽体的中衣也无,一时也不好唤人过来,便用被子拢住身子。探头到帐外,道:“臣妾也去。”
苏恒也不过穿了身中衣罢了,跟前站着方生。我往珠帘外面望了望,见站着红叶与吴妈妈。我便又说了一遍,“我马上就好,让我跟你一道过去。”
能让人半夜过来传话,太后这个“不舒服”无论实情如何,都不是件小事。
我才开始管事,便出了这种漏子,实在不妙。断然没有安稳在殿里等消息的道理,否则明日言官说起事来,我就别想再有好日子过了。
我焦急的望着苏恒的眼睛,见他点了头,便忙命红叶进屋帮我收拾。来不及换新的衣服,便抽了件尚未送洗的缃青色暗绣云纹深衣穿上,草草在后面绾了个髻子,便随苏恒出去了。
不知道是谁将清扬一并唤醒了,她穿得也一般草率。红叶便上前帮她整理整齐。
月亮尚未沉下去,然而也不过一点萤火之光,照不明暗暗沉夜。天黑黢黢的,星光也不觉明亮。屋檐棱角漆黑却分明,连屋下风铎也清晰可见。沉静得重墨画出的一般。
万籁俱寂,连一点虫鸣也无。马蹄声和车轮滚起来时带了杂音的碌碌声,溅开的水一般散了,却又留了些隐隐的回音。
苏恒攥了我的手,他的手比我的还要凉,偏又有些湿,令人不适。他说:“母后春秋咳嗽是宿疾了,你不必忧心。”
我只说:“皇上也不要忧心太过。”
他便沉了声音。默默的与我上了车。
我仍记得苏恒跟我说过的事。他说是家中幼子,小的时候便比别人调皮些。每每闯了祸,太后也不责罚他,只让他和自己一道跪在父亲的画像前。祠堂阴冷,她身子不好,常常一边哭一边咳嗽,明明一句话也不说,却比打了他一顿,更让苏恒难过。
他说平阳也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家里能帮太后分忧的,便只有他的长兄苏歆。太后一直等着苏歆出息了……而后话便停在这里。
我纵然恶毒的猜测,太后是为了陷害我,故意装病的。这个时候却也说不出让苏恒揣摩太后用心的话。
毕竟是母子。一个喜欢的另一个也喜欢,一个讨厌的另一个也讨厌。真的想要陷害我的,还不知道是谁呢。
我们到长信殿的时候,外面只有孙妈妈来迎。一路进了太后的寝殿,便看到刘碧君肿着眼,挂着重重的黑眼圈在太后跟前伺候。
太后咳嗽一阵子,道:“三郎来了没?”
刘碧君一边落泪一边笑道:“来了。”
太后气恼道:“你别骗我。他眼里只有椒房殿里那个祸害,什么时候也有了老婆子我。”而后又咳嗽。
她咳嗽得厉害,声音已经有些哑,然而中气却还足。我便先松了口气。
苏恒在外面停了片刻,声音里听不出急缓,问道:“太医令来了没?”
后面便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
刘碧君听了外面说话,先慌乱的理了理发鬓,随即又沉寂下来,只起身扯了扯衣角,便下拜道:“碧君见过陛下,见过皇后娘娘。”
她身上钗环皆无,发髻已经有些松散,半堕在耳鬓。面容略有些憔悴,衣衫也带了些随意的散乱,却越发的楚楚可怜。
苏恒道:“太后怎么样了?”
太后已经在说:“没死!没让你媳妇儿整死!”
我从没见过人这么发难的。只能匆忙跪下身来,道:“儿臣不明白母后的意思,请母后明示!”
刘碧君也跟着扑通跪下来,一屋子人,片刻之间,就只剩苏恒站着,太后歪着太后怒道:“你听她还在跟我强嘴。”
苏恒沉默了片刻,道:“儿臣也不明白,请母后明示。”
太后噎了一口气,竟然就这么又倒在床上,四面的人忙涌上前去,哭哭啼啼,吵闹得人头都要炸开了。
一片杂乱里苏恒将我扶起来,道:“你先回去。”
我一时木然,抬眼看他。苏恒目光里有什么一闪,伸手盖住我的眼睛,道:“有朕在。你先回去。”
我站起身,不觉脚下晃了两晃,忙扶了门框。
其实我很想留下来看看,太后还想怎么闹。
刘碧君膝行着追上我,拽住我的裙角,仰头道:“皇后娘娘,太后是无心的。只因今夜去传太医令,却无人当值,太后娘娘心里一时气闷。并不是意指皇后娘娘。”
让我怎么说──太医令归少府管,少府在大司空治下。大司空许文本老病,手上诸多杂务都分交给大农令代理,不巧的是,大农令正是我的亲哥哥。
我俯身扶她起来,道:“诚惶诚恐,无立锥之地。太后日后也不必再生气了……”
苏恒忽然便回过头来,目光直直的望着我,我不觉退了一步,口中的话已经断掉。他上前一步,攥着了我的手,我只觉手腕都要被捏断了。
他拉了我排开众人,跪到太后跟前,平静道:“母后什么也不用说了,该死的是儿臣。”
他的声音很沉,也不大,殿内却立时鸦雀无声,连正在诊脉的太医也觳觫着叩下头去。每个人的面前都有汗水滴落下来。
太后已经攸攸的转醒过来,也不咳嗽了,只抬着一跟手指指苏恒。
苏恒抬手拉了清扬起来,对太后道:“她是神医吴景洲的关门弟子,顾仲卿的侄孙女儿。虽是女流,医术却不逊色于太医令。就暂且先让她为母后扶脉,必然周全无遗,公正无私。”
苏恒道:“命所有太医令前来会诊。着少府令、大司马、宗正前来长信殿,朕要亲自问责。”
32决裂
太后指着苏恒,眼睛瞪得大,几次张嘴,都说不出话来。
苏恒下了令,便起身要走。我被带得一踉跄,几乎要扑到他的身上。
太后眼瞳便有些上翻,底下跪着的宫女们忙上前帮她顺气。刘碧看见状,愣了一刻,忙哭着抱住了苏恒的腿,道:“陛下,人病弱时难免有些脾气,一时口不择言也是有的。太后娘娘年纪大了,陛下不要跟着怄气……”她动摇不了苏恒,便又扑倒我跟前,一边叩头一边哭道:“太后娘娘只是心里想见陛下一面,并不是想责怪了谁,皇后娘娘便劝劝陛下,多陪陪太后娘娘坐一会儿吧……”
我木然望着她。刘碧君未免太看得起我,太后与苏恒见不见面,岂是我能说的上话的?
这佞宠惑上、隔绝帝后的罪名,我是担不起的。
然而太后已发了脾气,我一开口必然就是“强嘴”,便只默默的重新跪下去。
──民间有句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后宫的女主子也从来都不是皇后,而是太后。如今太后步步相逼,真是逼得我不得不动心思,好早一日熬出头。
太后总算没再背过气去,喉咙里一句话终于挤出来,“你让他们走!哀家病死了岂不更好,省的碍了他们的眼!”
苏恒闻言,回身便直挺挺跪下,道:“母后这么说,是叫儿臣无立锥之地了。只是今日己经有人欺负了母后,又栽赃到皇后身上,儿子纵然昧弱,却也知此事姑息不得,必得即刻彻查清楚了,好给母后交代,还可贞公道。”
太后噎了一口气,捶着胸口道:“好,好。你去查。我倒要看看,你能查出个什么样的不偏不倚的结果来。”
苏恒依旧攥着我的手腕,叩了头,才起身拉我走。
太后在后面憋了口气,道:“皇后留下!”
苏恒身形略顿了顿,我默默的挣开了他的手。
他低声道:“晕过去。”
我不能分辨他的用意,只怔愣的望着他,脑中一时百转千回。
片刻后,身形略晃了晃。
他演戏果然娴熟得令人叹为观止,眼瞳缩得厉害,连声音也有些飘忽了:“怎么了?”
我说:“……有些头晕,不碍的,陛下去吧。”
苏恒屏了呼吸看着我,可是我半点不想晕倒给他看。就算我此刻晕倒了,他也不可能送我回椒房殿。一会儿我落在太后手里,万一有谁打着救醒我的旗号,给我灌下什么药去,那我便有苦说不出了。
苏恒还要装模作样,太后却是能做出这种事的。
这屋子里不会有谁怜惜我,我得自谋出路。
苏恒面色又有些不好,死死的盯了我好一会儿,终于甩了我的手,道:“方生,你留下替朕照料着。碧君,太后与皇后都病着,朕就暂时将她们留给你了。”而后便转身大步去了。
我只在帘子下边伺候着。
屋子里跪了一地的人,却半声人语不闻。一片悄寂里,更漏滴滴答答的烦响像水纹一样推开来,一声催着一声。蜡烛烧得残了,连着爆了两个烛花,殿内器物黑漆漆的影子便猛的拉长了,像猛兽般跳起来袭人。
清扬不急不躁的给太后切脉,左手切完了换右手。垂着眼睫,一声不吭。
外间隐隐有人鬼哭狼嚎的声音传进来。帘子下跪着的太医令大慨不堪老迈,哆哆嗦嗦的抬了一只袖子擦了擦汗水。
太后的眉心跟着那声音跳起来,片刻后抬了袖子掩着嘴咳嗽,刘碧君忙起身为她顺背。
太后抬了抬头,帘子下边伺候的吴妈妈忙上前道:“娘娘有什么吩咐?”
太后面上是老妇人才有的慈悲关切,“去看看,外边儿出什么事儿了,叫得哀家心口疼。”
吴妈妈忙应声去了。片刻后回来,声音就己经听不到了。然而吴妈妈脸上的骇惧却半天不消,道:“是陛下在审问。”
……看来是用刑了。
我不觉往外望,天一色柔黑,星幕低垂,万物仿佛都被吞噬了。
太后道:“审的什么人?”
吴妈妈踟蹰片刻,道:“老身没认出来。”
太后便觑着我,道:“皇后说,皇上审问谁呢?”
我垂首道:“儿臣不知。”
太后眉毛一竖,道:“不知道?你什么事不知道?”
我只垂着眉不做声。
方生忙上前道:“太后息怒,小人去看看。”
太后挥了挥手,方生迟疑不定的望向刘碧君,刘碧君悄悄的点了点头。方生这才起身去了。他的身形才消失在夜幕里,太后那边便慵懒的道:“过来给我捶腿。”
她不点名道姓,我便也不作理会。这种事本来也不该我做的,何况连我要“整死”她的话太后都说了,我十分怀疑,我敢靠前一步,定然便要挨一记窝心脚。
刘碧君目光哀切的望了我片刻,有些失望的敛眉上前,为太后捶腿。
太后恨铁不成钢的一把将她揪开,沉声道:“皇后,过来给哀家捶捶腿!”
我心里憋得厉害,便静静的望着她。这个无论我做什么,都只想置我于死地的女人,我实在不想再与她周旋。
太后目光从严厉、错愕渐至恨恼,最后抬手不知道摸到什么,便朝我丢过来。
我只觉得鬓角一湿,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擦着耳朵飞过去,将身后柜子上摆的瓷瓶撞到地上,摔得希碎。屋子里再次静默无声。清扬也跪直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