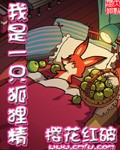悲愤是一种病-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俗约菏强恐冻苑沟娜耍退抵挥兄恫拍艿贾碌赖拢韵轮寰褪侵挥形娜耍ㄓ兄兜娜耍┎攀钦嬲挠涤械赖碌娜恕S纱宋蚁氲揭桓隼投擤ぉひ桓雠┟瘢岵换嵯笠桓鑫娜艘谎槐咴谔锛淅妥鳌急热缗缛髋┮剑槐咚底约旱睦投俏ㄒ坏牡赖拢妓换崴抵挥信缛髋┮┎呕岬贾碌赖隆!讲⒁笏械娜硕枷笏谎投ㄅ缛髋┮R桓雠┟瘢桓龃科拥呐┟袼换嵴庋皇悄馗牛牡赖戮褪撬纳硖澹奶辶Γ约八奶辶Φ慕峁ぉつ切┫事滔事痰那嗖恕⒙懿罚切┩ê焱ê斓姆选⑵还彼吹讲耸谐。谒氖卟颂埃扌杷祷埃貌蛔趴淇淦涮福氖卟司褪亲詈玫挠镅裕牡赖戮驮谒聊墓纳硖謇铮谒男孪识孕诺氖卟死铩K牡赖率浅聊牡纳硖逍缘哪嵩诮峁械模皇怯镅缘摹⒘榛甑摹⒖床患摹⑿榛玫暮退荡堑摹N娜怂担骸ò榛瓴灰硖澹系鄄灰约骸ǎㄈ馓逯皇且痪叱羝つ叶眩羁杀傻娜司褪侵话约汉湍蔷叱羝つ业娜恕ā)ぉの娜私徊剿嫡飧錾缁岬牧榛昃褪撬牵笾谡庵皇钦飧錾缁岬闹濉T谡饫锶说纳恚亩址涫滴质凳澜绲娜嗽谥魈宓匚簧系模ǔ街魈逵胍话阒魈澹┑木缘燃吨贫取N娜怂担旱赖录粗刃颉H寮医病ㄎ尬ァǎ褪且嗣嵌陨缁岬燃吨贫炔扇∫恢帜系奶取�
在中国,儒家的对于身体的蔑视〖〃君子舍利而取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历史的源头没有象古希腊的伊壁鸠鲁那样的崇尚身体、感性的反对派伦理学家,又没有经历尼采那种非道德主义哲学的冲击,所以中国的反身体、敌视感性〖感官〗、视肉体为仇寇的道德主义观念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中国人在长达几千年的过程中一直受着这些可耻的道德主义者的愚弄和欺骗,以至中华民族看起来似乎是先天就反身体的,中国人不重视身体锻炼、缺乏户外体育活动的兴趣──对身体蔑视得太久了,几千年的结果人们获得了一种种族上的身体的颓败形式,道德主义者应该为这种身体素质的普遍虚弱、体力的普遍萎靡,感官〖感性〗的普遍退化负责,〖一个灵魂主义的民族怎么不会得此体症呢?〗
我们承认人道主义的精髓在于对个体的人的自我选择和决断的权力的肯定,那么我们会清楚地发现道德主义者的文人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地反人道主义,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个体:自由自觉自主的个体,而代之以那些无个性无决断的〃群众〃。他们把道德抬高到绝对,其目的就是要无数个体放弃个性没入普遍理性和普遍意识之中。进而言之就是要牺牲无数人的个性,使他们不能成为个人,而成为道德主义者的道德容器,执行思想而不是创造思想,甚至连选择思想的权力都没有。对于世界这将是怎样一副图景?世界之舟的最上层是道德主义者〃高大〃的身影,他们振臂挥舞,是伟大舵手,而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只能在底层的船舱里划桨,对于这船划向哪里他们无权过问。他们除了划桨之外不再有任何权力。
面对道德主义者我总是对自己说:别盲信,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决断。必须认清道德主义者的虚伪的面目。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现在我们把这个世界简化到只有三个人,这是一个简化的世界模型。假设他们三人只有一个面包作为食物,这是道德主义者会对另外两个人说:〃你们应该讲讲道德,应该将面包给有病的人吃(我就是那个有病的人)。〃而个体主义者会对另外两个人说:〃你们有权选择你们对面包的态度,但是我对面包拥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我将使用这个权力。〃第三个人,他听信了道德主义者,他说:〃亲爱的道德主义者,其听从您的教导,为了道德的完善,我将面包献给您。〃第三天我们将看到道德主义者在吃了双份的面包之后满面红光,他的道德主义说辞越发凌厉辉煌,而那个献出面包的人已经饿得两眼昏花,连说一句〃给我一片面包吧〃的力气也没有了。不要相信道德主义者的说教,不要将自己降格为一个无思想无个性无决断的人,一旦我们解除了对道德主义者的迷信,人们不再相信关于上帝、圣人、大全的说辞,对于绝对主体的信仰没有了,那么相信一种超凌于个体之上的道德规范为一种绝对的普遍有效的道德规范的信念也会跟着瓦解。人们就会从这里回家,回到那个个人的立场。换句话说,没有普遍必然的道德律,道德主义者无权充当绝对主体,无权对公众指手划脚。
对于道德主义者,我天生就感到恐惧。他会用道德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你,一旦风吹草动,为了保住他道德主义的声誉,为了他的知识他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你。他们是一些只有脑壳而没有身体的怪物,而他们的脑壳里无一例外地装满了〃知识〃这个浆糊──他们是把知识变成浆糊储存在他们僵硬的脑壳里的。因而他们在生活上毫无趣味可言。他们成天就为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活着,他们读那些死去的人的书,只和那些死去的人交谈。
我宁可和那些毫无知识的人交往:他们的脑子里没有浆糊,没有圣人的条条框框,因而他们的行事依靠自己的判断,甚至本能。他们的身体保留着鲜灵灵的活力,他们不仅用脑子思考这个世界,还用自己的身体来思考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用他们身体的行动证明自己的思考。他们没有知识,可是拥有比知识更为宝贵的本能,他们知道冷暖饥饱,知道如何维持自己的存在,不会象那些所谓的学者那样标榜自己〃废寝忘食〃,把手表放到饭锅里,出门总是撞到电线杆上,他们知道一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必然的欲望: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欲望,为了存在他们早出晚归,不吝啬使用自己的身体,相反他们为自己的身体感到自豪,他们循着自己的本能在夜晚和自己的爱人作爱,他们用他们的身体表达对他们的爱人的感激和衷情而不是用夸张乏味的语言,他们渴望生育,为自己的生育能力感到自豪,他们不会象那些〃有知识〃的人那样拒绝生育,拒绝为人类的延续承担义务,他们的本能使他们自然地亲近人类的使命,而不象那些〃有知识〃的人那样拒绝生育。单纯地做一个知识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要反对知识,在一个本真地存活于世的人和一个骄矜的知识者之间我选择前者,我愿意我的身边充满了那样的朋友。他们胖胖地、松软地活着,丝毫也不因为〃知识〃的理由而变得畏缩、委琐,他们大大咧咧,对着酒瓶喝酒,在傍晚的光线中他们哼着流行歌曲回家,你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发自本能的肆无忌惮的笑声……
幽默的权利
近日从《文艺报》周末版上读到某先生的《笑里藏污》一文,有些感想。该文举了几个例子,讲到美国国旗是非常神圣的,巴顿将军、《列宁在一九一八》是非常神圣的,烈士们是非常神圣的,南京因为曾经是中国的首都也是非常神圣的,所以电影《甲方乙方》就不应该拿这些神圣的事物来幽默,而现在的《甲方乙方》则完全是〃笑里藏污〃,毒害那些不明事理的青年人。
美国的国旗自然是神圣的,《笑》文中所列举的事物也可以说都是神圣的,可是,我要问,难道〃神圣的事物〃就不能拿来做幽默的材料吗?美国人不来幽默的东西中国人就不能幽默一下吗?事实上,这位先生可能不知道,美国人对国旗的态度是庄重的,但是当要通过法令,宣布焚烧国旗是非法的时候,美国知识分子就站起来反对了,美国人可以自愿地尊崇一个事物,但是不会愿意被迫尊崇一个事物。进一步说吧,这位先生对《甲方乙方》看不惯,我想是因为这位先生把人分成神圣和卑俗两种的缘故,在这位先生看来,俗人把圣人当菩萨供着才是正理,俗人是没有权利拿圣人来幽一默的。所以,那个胖子书商只该在他的书店里卖书,是绝不应该有他的幻想的,至于幻想做什么巴顿将军就更是大逆不道了。
其实一般情况下圣人都是很随和的,圣人也是不忌讳拿自己来幽默一下的,例如,毛泽东,他就在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去见马克思〃来对自己的年老幽默一回。据说在场的人都会心地笑了,没有听说有人因此而嘲笑主席,相反大家从这个幽默中感到了主席的人格份量。这样的例子不枚胜举,〃圣人〃是不忌讳拿自己来幽默一回的,怕就怕在我们中的某些人自认为〃卑人〃,对着圣人鞠躬哈腰,在圣人面前连头也不敢抬一下,他把脑袋都给了圣人,然后自己做了没有脑袋的尾巴。他把自己的权利交给了圣人,其中甚至也包括笑的权利。
我想这位先生可能弄混了两个概念:幽默和嘲笑。幽默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活动,幽默是让别人发笑,是一种奉献、一种艺术、一种同情;而嘲笑则是取笑因而也是取消别人,漠视别人的缺陷和痛苦。所以幽默和嘲笑是不一样的,《甲方乙方》是幽默。葛优的表演是幽默,葛优长得不好看,甚至是难看的,但是他拿自己的〃不好看〃来表演是拿自己幽默给大家,这是一项崇高的艺术,这和当初他父亲的艺术还不是一回事,他父亲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幽默的,那个时候〃卑人〃也是不允许笑的,于是那个时代葛存壮这样长相的人就只能演日寇、汉奸……他只能用自己的长相接受嘲笑。
现在,我们终于赶上了好时候,〃卑人〃也可以笑一笑了,可是有的人就是对〃卑人〃的笑看不过眼,好象〃卑人〃一笑,天下就大乱了,在他们的眼里人们一提到圣人(其中包括美国的圣人,如巴顿者)的名字〃卑人〃就应该沉静肃穆默哀,一提到攻占南京〃卑人〃就应该咬牙切齿两眼含泪如丧女考 女比 才行。但是这终于是自由的时代了,某先生自己愿意这样做,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他千万别要求别人这样做。
埋身于抵抗之中
〃我意识到自己埋身于一种抵抗之中……我懂得'自由人'终会惹起'野蛮人'的怨恨,他的最初任务便是去对抗他们。〃这是《西蒙·波娃回忆录》第一卷《闺中淑女》里的一段话,这段话可以作为西蒙·波娃一生经历的主线来加以认识。自然波娃也有软弱的时候,正如她自己所说:〃有时候我认为自己缺乏力量,我可能忍受再次变得和他人一样。〃但是这不影响她作为本世纪有数的几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而享有的荣誉和尊敬。
在卢梭的《忏悔录》、萨特的《词语》等等一系列自传中中国的读者已经领略过法语作家在自传写作方面的杰出才华,他们的自传写作一方面出于对时代的责任感,萨特在他的自传中说:〃我将通过我的神秘的祭品、我的作品使得处于深渊边缘的人类不至坠落下去……我自愿成为了一个赎罪的牺牲品。〃(《词语》)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自我拯救:〃我通过我的工作和真诚来拯救我自己。〃(《词语》)因而可能将他们对于世界敏锐的感悟力,对历史、对读者的真诚以及近乎自虐的自我解剖结合起来,他们的自传达到艺术与思想的极高境界。立定于法语作家自传写作的传统之上,西蒙·波娃的四卷本回忆录完全可以和上述自传作品比肩。
对于中国的读者,西蒙·波娃的名字并不陌生,她的《第二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