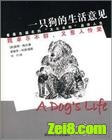谁来凭阑意-第8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是社会新闻的记者张爱,我现在在事故发生的现场,大家随着我的镜头能看到,公交车上现在还有搏斗的痕迹,车厢里全都是血迹,据了解,见义勇为的少年是英姿高中高三的学生,名字叫刑浩之,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因为失血过多不幸身亡,让我们采访一下目击者,你好,事故刚发生的时候??????”
麦吟看着电视,发出一声惨叫,跌坐在地上,我闻声跑了过来,看着电视呆在那里,电视里面说的什么?见义勇为的人是谁?
我没有听清楚,麦吟哇哇大哭起来,喊着耗子的名字。
我拽起麦吟,皱着眉向她喊道:“你哭个什么劲啊,跟哭丧似的,那个刑浩之一定是重名,一个学校又怎样,一个学校就不能有重名了,谁说一定是耗子了,耗子一会就回来了,一会就回来了。”
我蜷身坐在沙发上,抱着膝,一遍一遍的说:“耗子很快就回来了,今天不是麦吟生日么,耗子说了给你过生日的,他说过的话都能做到,他一会就回来了。”
手机在桌上响了很久,我可以忽略掉,我害怕会接到一个残酷的消息,我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中,掩耳盗铃的安慰自己。
麦吟哭得肩膀一耸一耸,伸手去拿手机,我一把抢过来,砸在地上,凄厉的喊:“别动我的东西。”
手机掉在地上摔得粉身碎骨,那个跟耗子一样的手机,像一道破碎的伤口一样,落在我的眼中。
麦吟一把将我推倒,嘴里骂着:“木科菲,你他祖母的是不是有病。”
麦吟的手机也响了,她接了起来,踉跄了一下,勉强站住,用轻的被微风都能吹散声音说:“知道了。”
放下电话,只说了三个字,剜人心窝的三个字。
她说:“是真的。”
麦吟吸了口气,颤抖的说:“医院让家属去认领尸体,走吧。”
“我不去,那不是耗子,那肯定不是耗子,耗子怎么可能有那样的英雄气概呢。”我用手捂住耳朵,痛苦的摇着头,我不能接受这个我认识了17年,像亲人一样的人就这么不在了。
“科菲,清醒一点,这是真的,我知道你难过,但是你要坚强。”麦吟忍着哭声,喃喃地说。
“你说说,坚强有什么用我一向很少在别人面前流眼泪,我一向都坚强,可是这有用么?我的坚强换回了什么,换回了我一次又一次的失去,麦吟,你知道么,我已经失无所失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么?”我瞪着发涩的眼睛看着麦吟,我的心里难过到极点,我一直在自我催眠,告诉自己,我很坚强,我很幸福。
可是,怎么样?
生活是怎么报答我的,他仁慈的赐给我一个又一个的灾难。
耗子,这个与我一起经历了童年,少年的人,就因为一个人,一篇报道,就没有了,我才不相信。
我要等着耗子回来,告诉他,刚才有多么乌龙,学校里竟然有重名的人,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有可能被授予见义勇为少年勋章呢,我要是走了,一会耗子回来看见家里没人,会着急的。
别看他大大咧咧的,他最怕的就是自己在家了,小时候,老刑留他一个人在家,他总是想方设法的往我家里钻。
有好几次被我当成贼给用扫帚赶了出去。
天黑黑。
是当时的哪个少年,他是谁,傻乎乎地同我抱在一起流眼泪?
天黑黑。
其实耗子,你当时还是个胆小鬼。那次,我被她们关起来,你可以放开我,自己跑的,因为你不必为我的错误而受那样的罪,你脏兮兮的小脸被她们的九阴白骨爪,挠成了一幅山水画。
天黑黑。
耗子,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你,一直以来你都是我心中的爬山虎,攀在我的心脏上,那些快乐的往事,很美但是刺痛的往事,全是我对你感激的眼泪。
天黑黑。
当时的那些小孩子为什么会这么讨厌我,又为什么这么坏。
他们围着我和耗子,准备往我们身上撒尿。他们都在笑,开心地笑。耗子将我护在身后,挥着稚嫩的小拳头,与他们扭打在一起,嘴里还低吼着:“你们要是敢欺负小菲菲,你们就死定了。”
这个在一出生就没有了母亲,在十几岁便再也没有一个男人会像一座碉堡一样站在他的身前,为他挡风遮雨的父亲的少年,却可以永远像一个骑士一样保护着他心中的公主。
而我呢,我在做什么,我只能躲在墙角,等待最不可饶恕的事情发生。
139 虽然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
麦吟咬着唇,问我:“医院你到底去不去。”
我摆弄着遥控器,不做声。
麦吟冷冷的一笑,说:“木科菲,你真狠心,可惜了耗子爱了你这么多年。”
麦吟转身,走得很决绝,我对着躺在床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老木他媳妇说:“妈,他们都说我狠心,可是,我觉得只要我不去,耗子就没死,他没有离开我们,你说对么?”
眼睛酸涩的厉害,却没有泪,有人说,悲到极致,无泪独心伤。
家中的门铃响,我走过去开门,看到了风尘仆仆的孔安生站在门口,憔悴的脸,青黑的眼圈,暴露了他几天没有睡好的事实。
他紧张的看着我,说:“我都知道了,木木,对不起,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
他把我紧紧地圈在怀里,我面无表情的呼吸着他身上熟悉的古龙水的味道,觉得自己僵硬的像一具行尸走肉。
眼睛瞄向外面,恍惚在一辆车里看见了我想念的身影,我推开孔安生,鞋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向着那辆车跑了过去。
孔安生在我身后紧紧的追喊,我都没有听见,我敢肯定我看见了耗子,他举坐在那辆车上向我招手,跟我告别。
一辆车急刹车的停在离我只有一厘米的地方,司机看着我大骂:“你找死啊,神经病是不是”
对,我就算找死又怎样,这样都死不了,心里难过得要死,却无法宣泄,孔安生脸绷着,扶起了跌在地上的我,仔细的检查着我又没有受伤,他恶狠狠的说:“木科菲,你要是死了,我就把你的骨灰碾碎。”
我的眼神没有焦点,看向远方,幽幽的说:“你就这么恨我?”
孔安生没有理我,叹了口气说:“我把你的骨灰化成细沙,装进沙漏,从一边流向另一边,一分一秒你都在我的时间里面。”
我的心被重重的感动了,想要说什么,几天没有吃东西,脑袋晕晕的,突然,眼前一黑,伴着孔安生的惊呼晕了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看到坐在床边的俊美面容发呆,阳光洒在他的身上,模糊了他的脸庞,我透过这个挺拔的身影,想起了一张总是对我嬉笑,死皮赖脸跟在我屁股后面叫我“小菲菲”的耗子,我伸出手,怕他突然失去般得紧紧抱着,眼眶酸涩,疼痛,却没有一滴眼泪。
我呢喃着:“耗子,对不起,耗子,对不起,别离开我,你回来吧,我以后再也不随便打你,对你毒舌了,你回来,好不好?”
修长泛白的指尖轻轻抚上我的脸颊,冰凉冰凉的触感,让我打了个大大的冷战,瞬间让我清醒,睁开眼睛,却看见孔安生无尽悲伤的望着我。
我呐呐的松开手,他却抱着我不放,声音颤抖,带着心疼的说:“木木,你难过就哭出来,哭出来,别折磨自己。”
我轻笑了一声,睁着眼睛好奇的看着他,反问道:“我为什么要哭?”
孔安生眼中的悲伤无限放大,他说:“木木,对自己好一点好么?”
我笑了,在孔安生的怀里笑得无限美好。
这笑容却刺痛了孔安生,他眼神闪了一下,犹豫着开了口,说:“木木,今天下午刑浩之的遗体火化,你不去送他最后一程么?”
我现在最恐惧的就是“最后”这个词,不顾你的反对,残忍的将一切都变成终结。
我死死地揪着孔安生的胳膊,企图让自己镇定一点,可是没有用,起伏强烈的胸腔就出卖了我,孔安生疼得倒吸了口凉气,却没有向我发火,静静地等待着我的答案。
安静的房间里除了我们彼此的呼吸声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
冗长的沉默之后,孔安生捋顺了我已经长到腰际的纠结的长发,语气温和的和我商量:“你不用怕,我会陪你去。”
我打掉他的手,重新躺回被窝,转过身去,平静的说:“我不去,你想去你去。”
孔安生叹了口气,说:“那就起来吃点东西吧,我熬了点粥,你现在身体太虚弱了,你这个样子自己都照顾不了,怎么照顾你母亲。”
说到了老木他媳妇,我一个挺身坐了起来,作势要下床,焦急地说:“忘记给她吃药了,也没给她翻身。”
孔安生安抚的一笑,说:“放心吧,我每隔一个小时翻一次身,明天会有一个专职的看护过来照顾阿姨。”
“哦,谢谢你,孔安生。”我由衷的说。
孔安生摇了摇头,说:“科菲,是我应该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解开了这么心结。”
我不明所以的看着他,想起了那封信,心里不是滋味的说:“你不是去美国追连锦笙去了么?怎么你们结婚了么?”
孔安生微微的皱了下眉,说:“木木,你说的这是哪跟哪啊,我去美国谈生意去了,很巧的跟连锦笙一个航班,下了飞机,在机场碰到,就去了机场的咖啡馆,坐下来聊了很久,解开了这么多年的心结,她还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收到了一封信,连锦笙笑了笑说,孔安生你很幸福,科菲很有勇气,为了你能解开心结,告诉了你真相,这件事情,我只对他一个人说过,安生,你要让她幸福。我当时心情很低落,说木木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把收到的照片给她看了。”
“照片?什么照片?”我惊奇的说。
“就是一张你跟戚季白抱在一起的照片,在连锦笙的提醒下,我才发现这是合成的,安宁跟我说刑浩之的事情,我就马上赶回来了。”
孔安生抱着我,他的下巴磕在我的头上,轻轻的鼻息扑在我的耳尖。
我努力的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说:“孔安生,我不是笑靥如花的女子,我有很多缺点,我家世不好,从小生活的就很艰难,现在还要照顾瘫痪的妈妈,我早就不是原来我们认识的时候,纯白如一张还没来得及涂鸦的白纸,现在这样白纸上面被泼满了墨迹,黑的快要看不出本来的样子,这样的我,你还想照顾一辈子么?”
孔安生沉默着,没有回应。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忍了许久的泪轰然砸下。
他说:“那天看到你晕倒在我的怀里,我就只有一个念头,带你走出伤痛,就像你带我走出伤痛一样,虽然那是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那样的机会。”
140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我在他的怀里哭的一塌糊涂,把这儿多天忍着的泪都哭了出来,哭了很久,到最后就变成了抽泣,我说:“安生,我想去送耗子最后一程。”
孔安生我紧握的手,说:“我陪你,以后,你做什么事情我都陪着你。”
我没有追究具体的位置,既然孔安生说带我去,就一定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坐在车上,看着窗外,已经是春暖花开,满街的丁香肆意地怒放,花香隔着车窗都传了进来,到处都是一片成绩勃勃的景象。
各路公车司机在这条宽敞平坦的马路上把巨大的公车开得像坦克,拥挤的公车里每个人都有一张被生活磨砺得麻木的面孔。
不时从公车旁边飞驰而过的名牌汽车里除了大腹便便,满脸油光的中年男子之外,偶尔也会有鼻梁上架着各色墨镜,妆容精致的年轻女性,在等红灯的空当,点一根女士烟,像模像样的抽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