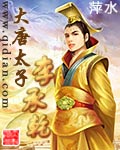唐太宗的24小时-第7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便是一幅牧民们驱赶着惊慌不安的牲畜们纷纷北逃的恐怖景象。
随即,唐军的前锋进抵定襄城下,并往城里射进了一封大唐中书令李靖写给突厥汗国颉利大可汗的劝降书信。
颉利的惊讶可想而知。他的主力大军都驻扎在定襄周围,他的巡曳游骑在方圆几百里之内自由往来广布眼线,而唐军的到来竟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报,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游骑斥候要么已经被歼灭要么正在与敌军进行苦战。这充分说明了唐军兵力之空前强大。颉利自幼随父亲启民可汗在中原游历,对中原的官制十分熟悉,他知道,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长官,是宰相。李靖以唐廷宰相北征大军统帅的身份敢于率孤军深入腹地,必是唐已倾全国之力来攻。更加令他不安的是东面的李世积大军一路扫荡迂回,自己的侧翼和后方都在其威胁之下,如今前有强兵,后路不宁,颉利几乎没有任何思考过程便作出了放弃定襄的决定,他连在定襄城停留两天集结兵力再后撤都不敢,唯恐李世积趁机去包抄自己的后路,于是在李靖兵锋抵达定襄的当天夜里仅率百余亲兵出城北逃,将定襄城和周围将近数万突厥战士牧民乃至十几万口牲畜扔给了李靖。李靖趁机轻松攻克定襄,生俘寄居于此的前朝隋炀帝皇后萧氏及皇孙杨政道。
就在李靖轻骑奔袭定襄的同时,李世积也没有让颉利失望,他先一步迂回到定襄以北,在白道设伏,将刚刚在逃窜途中收拢了些兵马准备找个地方驻扎的颉利击溃,颉利数日之内在自家腹地内连败两阵,不知唐军究竟来了多少军马,仅率数百骑仓皇北窜,最后总算在阴山东北的帻口站稳了脚跟,再设牙帐。
然而实际上这时候所谓牙帐的意义已经不大了,突厥大军的整体建制已经被李靖雷霆万钧的霹雳手段打乱了。眼见唐军将十余万失去统一指挥节度的突厥大军分割包围在定襄周围各个击破,颉利又是心痛又是恼怒,此时如果他果断率部北还,唐军的力量究竟是否足以支撑一场深入漠北的长途作战便会成为一个问题,然而对于颉利而言,此刻北还的必然结果就是放任在定襄附近过冬就食的部族和牲畜群被唐军屠杀掠夺,即便绝大多数人能够逃过唐军的扫荡回到漠北,庞大的牲畜群也回不去——回去了也会被严寒和粮荒活活饿死。无论怎么看,即便北方没有一个叫做薛延陀的部落在突厥汗国的卧榻之侧虎视眈眈,如果在这个季节强行北还,回到漠北的绝大多数突厥人都将避免不了在饥荒当中被饿死的凄惨命运。为了争取时间求得一线喘息之机,为了能够将李靖的大军拖住,为了能够挨过这噩梦般的几个月时间,为了支撑到贞观元年的夏天,为了为突厥汗国多保留一分种子和元气,颉利遣使乘快马星夜向长安发出了求和的降表。
大唐皇帝李世民在七天后接到了颉利请降表章,连夜召集重臣廷议。廷议中文武臣僚发生了激烈争执,以淮安郡王太常寺卿李神通、河间郡王李孝恭、梁国公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珪、秘书监参与朝政魏徵为代表的一派势力主张接受颉利归顺,封其于榆林之北以制衡突利;而以江夏郡王左金吾卫大将军李道宗、赵国公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右骁卫大将军侯君集、大理寺卿参与朝政戴胄为代表的一干臣子则主张乘胜追击,不给颉利以喘息恢复之机,总揽征北粮秣事的尚书右仆射蔡国公杜如晦病重,未能参与廷议。
李世民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召突厥使臣上殿,严厉斥责颉利可汗背盟不义残民弃友十大恶状,同时允其归顺,召其来朝待罪。他当殿任命皇帝旧臣唐俭为鸿胪寺卿、出使突厥使臣、假节钺。翌日,风烛残年的唐俭在一队唐军的护送下离开了长安,与突厥使臣一起赶奔千里之外的突厥牙廷宣示大唐皇帝敕旨。
然而令大臣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唐俭一离京,皇帝似乎便把这个茬忘了,绝口不再提起此事。就是朝堂之上有臣子提及,皇帝也往往将话头岔开,顾左右而言他。更加令臣子们纳闷的是,皇帝竟然连一道暂缓进兵的敕书都不给前线发出,似乎完全忘记了前方还有将近十万大军在等待着他的最后命令。
马踏阴山
李靖在中军大帐门口跺了跺脚,又跳了几下,将浑身上下的积雪抖落,又左右扭动了一下被冻得僵硬的脖子,这才迈步走进了大帐。
偌大的中军帐内鸦雀无声,定襄道行军副总管并州都督李世积长身站在中央,大大小小十几员将弁负手跨步立在两边。李靖一进来,众将齐齐抱拳行军礼:“参见大总管!”
李靖摆了摆手,直截了当地问李世积道:“长安那边有消息过来么?”
李世积抬手抱了抱拳:“大总管辛苦了,朝廷至今没有只字片语发来,倒是下个月的粮草按时运了过来,半日也未曾迟延!”
李靖走到帅案后坐下,口中哈着白气说道:“钦使那边有消息么?”
李世积点了点头:“唐俭大人的侍从几个时辰之前到大营报信,言道颉利已然答应随他赴长安面圣请罪,只是目下辖境内头绪繁多,需少待几日方能上路。这几天颉利以及突厥各部落首领特勤勋族每日均陪同天使夜宴,款待甚欢!”
“扯淡!”李靖低低骂了一句粗话,随即又笑道:“若非唐俭身入虎穴打探虚实,我们终究还不能确认颉利的牙帐位置……”
他抬头问道:“定方,道路打探清楚了么?”
苏烈大步出列,拱手躬身答道:“回禀大总管,打探清楚了,往帻口共两条路,由此直向东的大路有起码四五大个队两万多突厥骑兵巡查把守……”
“两万多?到底多多少?”李靖皱着眉头问道。
苏烈脸上一红,硬着头皮禀道:“风雪实在太大,我们的斥候又不能靠近,未能确实详知……”
李靖无奈地摆了摆手:“另外一条路呢?”
苏烈迟疑了一下道:“另外一条是小路,可直插帻口之北,只是需要穿越阴山之脊,人马本来便难以通行,现下大雪封山,走起来便更加困难了!”
李靖听毕,半晌方淡淡说道:“我们困难,突厥就不困难么?这条路既然在,我们便能过去……”
李世积眼中闪过一丝讶色,语气平缓地开言问道:“大总管决意要用兵了?”
李靖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叹道:“我们拖不起呀!当初决议用兵的时候,本来便是准备速战速决,在天气转暖之前一举解决颉利部对中原的威胁。一旦等到夏天,颉利便可以毫无顾忌地率领部众直趋漠北。三年苦心经营周密布局,劳师靡饷数以百万缗,若是打出这样一个结果,不用主上降罪,你我羞也羞死了。何况如今大雪封境,大军调度机动极为不便,将士们冻伤的好多,再这么不死不活地拖下去,真要把全军的士气拖没了,就不是我们饶不饶颉利的事情了。颉利若肯放我们平平安安返回中原,你我便要叫一声侥幸了!”
李世积沉吟片刻,缓缓开口道:“药师,你要三思而行才好。皇帝虽说一直未曾明敕我们罢兵,可是目下唐俭就在颉利牙帐之中,名为钦使,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人质。他是太上皇时的元老重臣,侍奉三朝之人,我们这边发兵倒不打紧,若是一个不慎伤了他的性命,这个责任,你我恐怕担待不起……”
李靖认认真真听完了他的话,叹了口气道:“懋功,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是你我如今身在前敌,敌情瞬息万变。我们虽说打散了颉利的指挥节度建制,但敌人主力尚在。颉利在这个时候讲和,摆明了是缓兵之计,这段日子仅我们截住的知会各部落族众归建的传令骑便有十几起,或许还有我们不曾截住的。颉利狡猾多智,不把他彻底打垮,他万万不会诚心归顺。我们若是拖延耽搁贻误了战机,不仅钦使性命不保,便是我们现下统帅的这十余万人马,能有一半活着回到长城以南便不错了!只要我们打垮了颉利,他求我们饶命还来不及,又怎肯残害唐大人性命?对这些化外蛮族,礼义廉耻不管用的,他们只相信实力,只要你有实力,他们便会跪在你的马前,认你为主人!”
苏烈抬起头想说话,嘴唇动了动,却又咽了回去。
李靖摆了摆手:“有什么想法尽管说,不要欲言又止的!”
苏烈小声道:“话虽如此说,大总管,这毕竟太冒险了,突厥人凶狠狡诈,又历来顽劣。万一他们恼将起来,真的害了唐大人性命。纵使得胜回朝圣上不追究大总管的罪责,御史们却是万万不会放过大总管的!”
李靖沉思了一阵,冷然道:“唐大人的性命重要,中原几百万户黎庶元元几十年的安宁更加重要。我是北征大军主将,现在想的是此次扫北的整体胜负之事,万不能因为一个钦使便坐失战机。将在外君命尚且有所不受,何况唐俭?我决定了,这个局面不能再拖下去,我们须即刻发兵直捣帻口。此事由我决断,令由我出,自然不要你们负责任,我是陛下任命的持节钺大总管,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李世积哈哈大笑道:“笑话,你李药师敢担责任,难道我便是没有脊梁骨的软汉子么?既然你决定了,自然是我们两人一起下令,你若把我这个副总管撇在一旁,我可不依!”
李靖笑了笑,也不再多说,简要说道:“还是老章程,你带主力向大路佯攻,吸引颉利和突厥主力的注意力,我率一万精骑,带足二十天的口粮,由小路穿越阴山,直插帻口。”
“不行!”李世积干脆利落地驳回道,“你是大军主将,又是朝廷宰相,不能再涉险了!这一遭咱们换一换,我率军奔袭,你来率主力正面佯攻!”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道:“你今年已近花甲之年,我却四十岁都不到,无论怎么说,奔袭这种苦差事都应由我来才对!”
李靖板起面孔道:“懋功,不要再争了,冰天雪地大军远袭,主帅不在军中,将士们哪里来的士气?这是我的将令,不是和你商议!”
他冷冷扫视了一眼帐中的将军们,缓缓道:“此番是天下太平的最后一战,如若不胜,我李靖上辜圣上隆恩朝廷厚望,下负苍生托付将士期盼,自无面目再回中土。诸公用命,则此战便是我们晋侯封公的最后指望,诸公懈怠,这冰天雪地万里化外便是我们的埋骨之所……”
走出帅帐,李世积跟了上来,神色踌躇地问道:“药师,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说,帐内人多嘴杂,我便没有问。”
“懋功有话但讲无妨!”李靖爽快地道。
“我记得你我受命离京的时候,皇帝曾对药师面授机宜,还给了药师一道加了黄封的手敕,要药师在遇到难决之事时即行拆看!”李世积目光炯炯地盯视着李靖一字一顿说道。
一股不可抑制的笑意自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的胸腔之中涌动上来,他强自按捺着道:“主上手敕当中的所载方略,是李靖数十年从军生涯当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谋大略,懋功想看?”
李世积有些诧异地看了这位号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绝世名将一眼,不知道却是什么样的奇妙谋略,能得此人如许评语,更不明白他为何竟是一副笑不可遏的模样。实际上,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对皇帝居然给即将临阵指挥的将军以“锦囊妙计”相授颇为不以为然,这哪像是个精通兵略的君主所为,倒似是个喜欢卖弄自以为是的马谡赵括之流喜欢做的事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