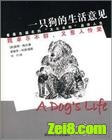爱上一只唐朝鬼-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到这,小祖母可能觉得到底不便在我们小辈面前过多抱怨,冷哼一声停了口。
我十分意外,一时接受不来,莫非他们白头偕老的美满姻缘竟是貌合神离?我嗫嚅地:“您就不后悔?”
小祖母黯然一笑:“我们那年月,讲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后悔又怎样?我和父母闹翻了脸要跟他,错也错了,有什么可悔,只得好好过日子罢了。”
我肃然起敬,这样的无怨无悔,也是现世流失了的品性吧?要有怎样浓烈的爱,才肯嫁一个明知不爱自己的人并伴他终生?
原来报纸上说得有误,陈曾祖父嫁女并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受女儿要胁的无奈之举。
我想象哭灵受伤的祖父躺在病榻上,陈二小姐殷勤看护,柔情缱绻,祖父只是置之不理,但二小姐还是感于他对姐姐的一往情深,宁愿以身相许,以一生的情来感化他,抚慰他。怎样的爱?怎样的爱?!
整个下午,我和黛儿都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久久不能平静。
好容易等到入夜祖父才扶醉归来,但是兴致倒好,听我们讲起小祖母的委屈,他不以为然地微笑:“是那样的吗?”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陈祖父的笑里有一种阴森。
然后他便沉默了,可是他的眼光渐渐柔和下来,用呓语般的语调轻轻地说:“她是美的,很贪玩,很浪漫,也很痴情。大户人家的小姐,却总喜欢打扮成农家女孩儿的模样从后花园溜出来到处逛,专逛那些卖小玩意儿的巷子。那次她忘了带钱,我偷偷跟上了她,看她在小摊前徘徊把玩,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又三番几次地回顾。我把那些玩意儿一一买下,有荷包儿,有绣样儿,还有藤草编的蝈蝈草虫儿,都是孩子玩艺儿,不贵……我跟着她,一直走出集市,追上去把东西送给她,她很惊讶,睁大眼睛看着我,整张脸都涨红了,那时候太阳快要下山,到处都是红色一片,她那样子,那样子……”
开始我还以为他说的是小祖母,但这时已明白其实是指陈大小姐。陈祖父情动于中,满眼都是温柔,我听到他轻轻叹息,顿觉回肠荡气。
眼前仿佛徐徐展开一幅图画:夕阳如火,照红了满山的花树,也照红了树下比花犹娇的女子。而那女子脸上的一抹羞红,却是比夕阳更要艳美照人的,她低垂着脸,但是眼波荡漾,写满了爱意缠绵,闪烁着两颗星于天际碰撞那样灿烂明亮的光芒。她打扮成朴素的乡下女子的模样,可是丽质天生,欲语还休之际早已流露出一个千金小姐的高贵妩媚。她手上拿着外祖父赠送的小玩意儿,不知是接还是不接,要谢还是不谢,那一点点彷徨失措,一点点惊喜踌躇,一点点羞怯窘迫,不仅完全无损于她的矜持端丽,反而更增添了一个花季女子特有的羞涩之美,当此佳人,谁又能不为之心动呢?这就是关关睢鸠为之吟唱不已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于是爱情一如参差荇菜的疯长,在那个彩霞满天的黄昏诞生蓬勃,令情窦初开的良人君子溯洄从之,左右采之,心向往之,寤寐求之……
那个时代的爱情哦,竟有这样的绯恻缠绵!
黛儿忍不住插嘴:“原来她也喜欢小玩意儿,这倒有点像我。”
陈祖父抚着黛儿的头发,痴痴地说:“不光这一点像,你长得也和她很像,像极了。我认识她的时候,她也就你这么大,一朵花儿的年纪……她是为我死的,这么多年来,想起这个就让我心疼。”
他的眼角微微温润,而我和黛儿早已听得呆去。
可是陈祖父的神情却在这时一变而为冷厉,恨恨地说:“你小奶奶一直想取代她姐姐,怎么可能呢?她哪里会有她姐姐那份真情?所以,我一开始就定了规矩:先奉你大奶奶的灵位成亲,然后才续娶你小奶奶,上下家人都只能喊她二夫人,永远把正室夫人的位子留给她姐姐,让她永远越不过她姐姐的头上去!”
陈祖父说最后几句话时,竟有几分咬牙切齿的味道。我听得不寒而栗。身份名位,在我们的时代尚不能处之淡然,何况他们的时代?小祖母以处女之身,下嫁于祖父,却一上来就担个续弦的名头,岂不冤枉?然而,谁又能责怪祖父对陈大小姐的一番痴心?
黛儿不以为然:“可是小奶奶对你也很好呀。你们已经一块儿过了半辈子了,没有感情,怎么会共度金婚?再说,陈大小姐再好,也是过去的人了,真正陪你同甘共苦的,还是小奶奶呀!”
陈祖父不屑地冷哼了一声,一脸厌恶:“她?她有她的心思。她肯嫁我,不过是为了要我帮她对付自己的亲哥哥!共度金婚?呵呵,共度金婚……”他呵呵笑起来,笑声中充满苍凉无奈,令我不忍卒听。五十年,整整半个世纪,难道用五十年岁月累积的,竟然不是爱,而是恨么?
我们还想再问,像陈大小姐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祖父又为什么会突然远离,还有,祖父究竟是怎么样被小祖母的柔情打动的,陈曾祖父又为什么要反对祖父与祖母的婚姻等等等等。可是祖父的酒劲却已翻了上来,口齿渐不清楚,黛儿只得唤上海厨娘来伏侍他睡下。
晚上,我做了梦。
朦胧中,看到有女子怀抱婴儿走近,面目模糊,但感觉得出十分清丽。我问:“你可是陈大小姐?”
这时候电话铃声响起,导游说:“要出发了。”
嘿,如此刹风景!
第四章 伤痕累累的西大街
回程飞机上,我同黛儿说起我的梦。
黛儿叹息:“我渴望这样的爱情。”
“哪样的?是你祖父对陈大小姐刻骨铭心的爱,还是你小奶奶对祖父那种无怨无悔的爱?”
“都渴望。因为他们都是那样地强烈、震撼、缠绵,与痛苦。”
“痛苦?你是说你希望痛苦?”
“是的。”黛儿望着我,认真地说,“小王子说,当你给一朵玫瑰花浇过水,它就不一样了。爱也是这样的,你得为它做点什么,它才是属于你的。我渴望有一天,自己会遇到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能让我快乐,而且能让我痛苦。他得让我为他流泪,伤心,痛不欲生。那样,我才会爱上他,把整个儿的心交给他。”
我望着黛儿,她的眼里充满着对爱的渴望,是一只鲸游在金鱼缸里的那种不足与渴望。
她不是没有爱,只是不满于她所得到的爱。
她想要得更多。
她想要整个大海。
虽然那里也许充满风浪,但那毕竟是大海。
回到北京,黛儿收敛了许多,连穿着打扮也不比以往暴露,变得淑女起来。然而再普通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也别有一种风情。
一天上古文欣赏,黛儿穿了件半袖翠绿色衬衫,同质地窄腿七分裤,袖口与裤管均密密地绣了一圈儿花边,平时飞散的长发今天梳成两只麻花辫子搭在胸前,辫梢还系着绿绸带的蝴蝶结儿,清灵秀丽得就像刚从民国时期的旧画儿里走出来的一样,连古文学老教授都被惹得频频从讲义上抬起眼来。
我忍不住叹息:“黛儿,如果我是男人,我真的也会被美色所迷。”
怎敢再骂那些迷恋黛儿的男人爱得肤浅?美色当前,谁又是深沉的智者?
她变得沉默,更变得忧郁,一双大眼睛越发漆黑如星。而且疯狂地迷上电脑,拒绝了所有追求者上门,一下课便揣着上机卡躲到电机室里做网虫。
开始我以为这一切的变化是为了阿伦,但是不久便发现自己错了。
傍晚,窗外阴雨如晦,黛儿在宿舍里大声朗读安徒生童话《雪人儿》:“雪人儿看到了火炉,那明媚的火焰正是爱情的象征,没有一双眼睛比它更加明亮,没有一个笑容比它更加温暖,它照亮了雪人儿的心,于是那颗心变得柔软而痛楚,它感觉到身上发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它不了解,但是所有别的人,只要不是雪做的,都会了解的。”
黛儿抬起头问我:“艳儿,你了解吗?”
“了解。小心防火,危险勿近。”
黛儿没有笑,却忽然没头没脑地问出一句:“艳儿,如果我想去西安工作,你会不会帮我搭线?”
“去西安?为什么?”我惊讶地停下笔,毕业考在即,我连年优秀,可不愿在最后关头痛失晚节。但是黛儿的提议太过奇突,我知道她父母是早已计划好要她一毕业即出国的,怎么竟会忽然想到去西安?
“因为子期不愿意来南方。”黛儿低下头说,“他说他父母都在陕西,不方便远离。”
“子期?子期是谁?”
“子期就是子期呀。”黛儿责备我,“还是你帮我牵的线,怎么倒忘了。”
我想了许久才想起香港咖啡座的那次邂逅,恍然大悟,“是他呀,你们后来联系上了?”
“我和他一直都有通信。”
我这才知道黛儿天天去机房是为了同高子期网上聊天,不禁叹息:“原来世上真有一见钟情这回事儿。”
黛儿低下头:“在遇到他之前,我也不知道爱情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她说得这样温柔缠绵,我亦不由认真起来。“那么,现在进行到哪一阶段了?可有谈婚论嫁?”
“没有。”黛儿的眼中竟难得地有了几分忧郁,她略带彷徨地说,“我已经决定去西安找他,我想天天见到他,你帮我好不好?”
“可是,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你原来不是打算一毕业就出国的吗?”
“原来我不认识子期。”
“这么说,你的前途将为子期而改写?”
“我的一生都将为他改变。”黛儿很坚定地说,“男人和女人的恋爱是一场战争,谁先爱上谁,谁就输了。我输了,我愿意!”
“我愿意”,这像是新婚夫妇在教父前永结同心的誓言呢。我诧异,黛儿这回竟是来真的。她眼中的光焰炽热而坚决,有一种燃烧的姿态,令我隐隐不安。谁看过雪人的燃烧?那样冰清玉洁的一种毁灭,便如黛儿的爱吧?
回到西安,我立即着手四处张罗着给自己和黛儿找工作。
父亲说:“其实何必到处应聘呢,唐禹那儿正缺人手,你们两个一起过去帮忙不是正好?”
我却不愿意继续仰唐家人鼻息,只肯答应介绍黛儿给哥哥做秘书。
在他的心目中,女友是女人,女同事却是老虎,尤其与自己同工同酬同等职位的女同事。
可是正因为对方已经出此下策,如果我接招,就等于把自己和他划了等号。而且他是男人,可以骂脏话,我却不能,骂了,就是泼妇。
男女同工同酬,女人却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的压力和管束,真不明白男人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意见。
我到楼下转了一圈又一圈,努力地劝自己平息怒气,不要七情上面,弄得大家尴尬。很多事都是这样,你可以做,我却不能说,说了,就是小气。这是文化人的游戏规则。
直到气定神闲了,我才重整笑容上楼走进办公室,见到张某人,如常微笑问候。他的笑容也真诚亲切,完全看不出刚刚才否认过我的存在的样子。
他的虚伪,我的无奈,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吧?我很怀疑这种竞争会有什么正面效应,但是主编坚持认为有竞争才会有进步,我们也就只有为了他的一声令下而厮杀拼搏。
像不像一盘棋,无论将帅兵卒,都不过是奕者手中的一枚棋子,本已贱如尘芥,棋子与棋子却偏还要自相残杀,更加贱多三分。
坐下来,我开始整理自由来稿,张金定走过来说:“主编让我把稿子送过去,你看完了吧?”
按规定,我们除了负责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