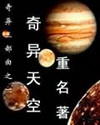栀子花的天空-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回家的路上,我老公开车,我就又跟他说起了这件事。我问:“你觉得怎么样?咱俩的名字拼一块儿就是孩子的名字 ?”
我老公姓傅,我姓程,我本来想,如果是男孩的话就可以叫傅诚,如果是女孩就可以叫傅程程。
我老公没反对,他点点头说:“嗯,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来着,将来咱们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叫傅雪扬。”
这句话说完,他突然噤声,意识到自己弄错了什么,而那一刻,我只觉得五雷轰顶。
雪扬这个名字,是我老公前女友名字的谐音。
我没有用化名,我知道把这个帖子发出来,认识我们的人可能就知道是谁了,包括他前女友。
可我已经觉得自己没什么好遮掩的了,就算这会让他们俩重新走到一起,我也还是成全他们好了……
我对着电脑屏幕,久久无法动弹。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
我慢慢地伏下来,趴在桌子上。
当初,我还是一名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有人把我宠得浑身是刺刀枪不入,似乎什么样的离别都不能让我流泪。
其实我只是不知道当时的自己究竟放弃了什么,赶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他那样好的一个人,我得来得太容易, 太容易,于是我以为这样的人在这世上到处都存在着,赶走了一个,另一个就算不是接踵而至,迟早也会补上这个空 缺。
如今我是一名法官,一身熟女模样,却抱着自己缩在转椅上像个丢失了全世界的小女孩一样嘤嘤哭泣。
只是那个为了把我哄停而大半夜抱着电话对我大声唱出“求求你给我个机会”的男孩,那个只因为我哭了一场就要带 我去吃好吃的补身体的男孩,他再也不会出现了。
他已经是别人的丈夫,而且将要成为一个父亲。
良久,我重新坐起身来,移动鼠标,打开我的歌曲库。
那里有一首歌,自四年前快要离开北大时起,我就再也没听过。
每次遇到别人在放,我都会用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借故走开。
而此时此刻,我想要听它,虽然知道它会让我原形毕露遍体鳞伤,我也还是想要听它,听它一遍一遍地对我说——
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似的深夜里,你是 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初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
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我第一次听见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个人对我说:咱俩永远不分开好不好?不然以后再听到这首歌,你说得有多难受啊 ?反正我肯定受不了!
他说得真对,真对。可为什么我当时轻轻松松答应了他,后来却没有做到?
这年春节,夏珩回来时,照例请我吃饭。
他已经研究生毕业,留在北京一家大型国企工作。
他有了新的女朋友,而且这次这个前景光明,房子正在装修中,初步定在国庆结婚。
我们正吃着饭呢,有人打我手机,我掏出来一看,乔野淳。
最近他突然对我改了称呼,让我总有些不习惯不自在,说了他几次,他死活不肯改回来,我也就由他去了。这个电话 他是邀请我去柳州:“扬扬,你不是爱吃螺蛳粉吗?我爸做得特别好,你来让你吃个够!”
我觉得这个邀请很可爱:“好啊,下回有空去尝尝你爸的手艺。”
他听出了我的敷衍:“我说的是现在,就这几天,你来我们这儿过年!当帮我忙好了,我爸说明年我要再不带女朋友 ,他就不让我回家过年了!”
和乔野淳扯完皮之后,抬头对上夏珩似笑非笑的眼神。
“干嘛?”我一边把手机收起来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薛扬,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肯接受我?”他突然问。
这是一个要问就应该好些年前问、当时不问现在问就很奇怪的问题。
不过我们俩谁跟谁呀,我照直回答:“你花心。”
他从不跟我计较:“唔……所以,你前男友的问题是说错了一句话,我的问题是花心。”
他顿了顿:“那这个小伙子呢?他有什么问题?”
我愣了一下,完全没想到他这个话题最终是要着落在这里。
我想了想,说:“他比我小,而且不够高,不到一米八。”
夏珩很意外:“他看起来挺成熟懂事的呀,而且个子也不矮啊。他比你小多少?”
我说:“三个月。”
夏珩噎了噎,又问:“那他多高?”
我说:“178。”
夏珩用一种“我都懒得说你了”的眼神望着我。
我第一次在他面前觉得不好意思,是一种近乎于无所遁形的不好意思。
我只好扭头去看窗外。夜色已浓,玻璃变成镜子,映出我的脸,讪讪的样子,蛮好笑的。
于是我无声地笑了起来。
还真是,我真好笑啊。
第二天乔野淳又给我打电话,这回是中午,打到我家的座机。
我正在睡午觉,我妈生拉硬拽地把我拖起来接。
我抱着话机重新躺回被子里:“老大,什么急事啊?吵人睡觉是会折寿的!”
他很惊讶:“你在睡午觉?”
“啊。”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扬扬,你不是不睡午觉的吗?”他问。
“谁说的?”
“你小时候就从来都不睡午觉啊。你在我妈的托儿所里的时候,中午总是偷跑起来出去玩,我还陪你玩过跷跷板呢。 不过算了,说了你也不记得。”
我坐了起来:“我记得!”
我记得,小时候在外公外婆家,他们送我上街道的托儿所,我每天都不肯睡午觉,所有阿姨都为我头大。
“你妈是托儿所的阿姨?”这回轮到我惊讶了。
“是啊。你经常自己不睡觉还闹别的小朋友,我妈好多次都不得已把你带回我家睡,又唱歌又讲故事才能偶尔把你哄 睡着一次。”
“你是那个陪我玩跷跷板的男孩子?我记得你!”
小时候我最大的折磨就是每天的午睡,第二大折磨则是每次中午偷跑出去都没人跟我玩,而那天那个从天而降的男孩 子,我觉得他简直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人儿,那是我整个童年里最最快乐的一个中午!
“后来我妈发现让你带我睡,你就会给我讲故事,像个小大人一样抱着我拍拍,哄我睡着,然后你自己也会睡着。以 后你就都在我家午睡了,我们俩经常一口气睡掉一整个下午,不过你好像只上了一个学期的托儿所就不上了。”他回 忆得津津有味,末了似乎还有些遗憾。
我吃吃地笑起来,忽然又觉得困了,索性闭上眼睛:“乔野淳,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我老说你是我的洋娃娃,回桂林 后我还想了你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每天,都很想你……”
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刚满28岁。
这是陈坤组织的同学聚会,特意定在这年国庆,以便外地的同学也能抽身出席。
聚会的名头很重大很煽情:纪念我们相识十周年。
十年!原来已经有那么久了……
我不知道其他人看到这个聚会邀请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自己是被噎住了,不仅仅是话语,而是整颗心都被噎住了。 一些支离破碎却又流畅连贯的片断拼接成一组快速播放的镜头在我的脑海里淌过,刚满十八岁第一次见到那个男孩的 那个傍晚又渺渺地在眼前浮起——
那是大一上学期的九月底,我选的通选课中有一门是我们院开的《法律社会学》,时间是晚上七点,地点在理教。
那天夏珩给我过生日,于是我去清华吃饭,回来晚了,跑到教室门口的时候已经上课。
好在是阶梯教室,门在讲台的两侧,不会一眼就被老师看到。于是我站在门口寻找岳萦,她冲我招手。
我开心地一笑,而就在那一瞬,我看见了她后排座位上有一个高大健硕的男生,黧黑的肤色,面容沉郁,目光定定地 凝在我脸上。
那目光像是有质感有份量的,压在身上很沉,像是再也推不开。
他似乎有些忧伤,好像就是我让他忧伤的,可为什么我又舒服又快乐,特别特别愿意他那样看着我,一直那样地看着 我。
我还记得那天我头上戴着两只大大的布质蝴蝶结发卡,此时它们便飞旋在一些朦朦胧胧的困惑、或者是顿悟里——
原来,我是那样地,从一个小女孩忽然长成一个大姑娘的……
这次同学聚会上,我见到了傅泠熙。
算起来六年多了,就算再上一次北大,我们连研究生也都毕业了。
他走过来,静静地看着我。
我望向人群簇拥之下的程佳影,她正抱着漂亮的小女儿,接受大家的赞美和逗弄。她早已退役,还生了孩子,可是并 没有如她当初所担心的那样发胖,整个人只显得丰润鲜丽,是位心满意足的母亲。
傅泠熙同样也对她说错过一句话,比对我的那次错得还要离谱。
可是她的选择,是留住自己已然握在手中的幸福。
以前我老是觉得她小白,其实她比我聪明多了,她的确比我更值得傅泠熙。
我对傅泠熙微笑:“小丫头很漂亮,结合了爸爸妈妈的优点,长大了一定了不得。”
我该问她叫什么名字,奈何这是一起不便询问幼儿名字的特殊案例。
是傅泠熙自己提起来的:“她小名叫程程,大名叫雪扬,她妈妈给她写在户口本上的,说是很漂亮的名字。”
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好望向一边,假作在关注大家的动向。
傅泠熙仍然看着我,低声说:“她是个女儿。我和佳影说好,只会生这一个孩子。”
我有些说不出话来,可我必须得说些什么。
至少,我欠他一个抱歉。
我抬头,望向他的眼睛里去:“傅泠熙,对不起,你当初只是说错一句话,我却将你错判死刑。”
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望着我,瞳仁深处渐渐有水光潋滟。
我想告诉他,其实我也为自己的错判付出了代价,我自己也服了数年苦刑。
可是,惩罚已经实现就好了吧,没必要非得说出来寻求世人的承认。
从同学聚会的饭店出来的时候,乔野淳已经等在门口。
他迎上来,我惊问:“你不会一直在这儿干等着吧?”
他微笑摇头:“自然不会,我有到附近逛,婚纱样式和戒指都已经选定,你是要惊喜还是自己亲自去把关?”
我想了想,挽住他的胳膊:“惊喜就好了啦,相信你的眼光!”
他揽紧我,低头在我额上一吻:“那咱们回去吧。”
“嗯,你吃过饭了吗?没有的话我陪你去吃。”
“好,顺便把你养胖点,那套婚纱对上围很有要求的哦!”
“不要再让我长胖了啦!还有,不许嫌我上围不够丰满!”
“哈哈好好好,夫人这样就是恰到好处,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
十月的北京,天气真正是好,往昔如同金黄的银杏叶一般从心头翩然飘落,在谈笑之间盈盈然灰飞烟灭。
结局二、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
第32章 (上)
我回到家好几个月之后,才在一次契机中对我爸妈提起我和傅泠熙分手的真正原因。
我以为他们会为我而愤愤,不料他们听罢只是一阵静默。
我爸似乎想说什么,我妈用眼神制止了他。
然后,我妈对我说:“这也没什么的呀,大多数人都是想要儿子多过女儿啊。他也就是那么一说,你生气之后他难道 没给你道歉?”
我觉得不可思议,把筷子往桌上重重一拍:“妈,有人要你女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