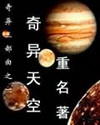栀子花的天空-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惊讶得腾的一下坐起来:“什么意思?这什么人啊?那他自己有北京户口吗?”
她“嗯”了一声:“他就是北京人。”
我怒了:“拜托他也找个好点的借口好不好?这政策早就变了多久了呀,夫妻俩只要有一方是北京非集体户口就不会 存在孩子是外地户口的问题了!他要不是北京户口我还反问他一句凭什么要求你是北京户口,他是北京的我还真就无 语了啊,这种理由说出来,他要不要脸啊?”
义愤填膺到了最后,我又觉得自己失言,这么说岳萦不得更难受了?
于是我话锋一转,牺牲自己来安慰她:“唉,好歹他也没说如果将来你怀上的是女儿就打掉哈。”
岳萦那边半晌没有作声。
我以为她还是难受了,正着急着该怎么补过呢,她却幽幽地开了口:“扬扬,其实……你觉不觉得……傅泠熙是不是 也没错得那么严重啊?”
我愣了一下,回过神来,立马把一句否认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怎么没有?这早就是定案了,咱们不提了啊!”
我明白岳萦的意思,而且说实话,打心眼儿里,我也觉得还是她那个混蛋前男友更不可原谅。
可我不能承认。
要是承认了傅泠熙的错没那么严重,那岂不是说我错了吗?
如果是我错了怎么办?
我不会认错,因为在傅泠熙面前,在我的爱情里,我从来都没有认过错。
从我们第一次吵架开始,我就从没认过错,不管是什么事,不管是谁的问题,永远是傅泠熙来负荆请罪,到后来我们 甚至都没什么吵架的机会了,因为他会在发现最初的苗头时就毫不含糊地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
因为不会认错,所以我只好不犯错,或者说,不承认自己犯下了错。
春节过后的那个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有个留在北大读研的同学在qq上给我留言说:“我们从万柳搬回学校的新研究生 楼住了,还是像咱们本科宿舍那样的公共水房,不过宽敞明亮得多。我在那儿洗衣服,在镜子中看见有人走进来,却 十之八九都不认识。
忽然很怀念过去在水房一起嘻哈的日子,想起你这个水房女皇,每晚一边洗衣服一边不停地讲话。”
我看着这条留言,一个劲咕咕直乐。本来都快忘了的,她这么一提醒,过去自己在水房里的表现就开始像过电影一般 地在我脑海里轰隆上演。
那时候在水房,我的确几乎没有一刻安静的时候,傅泠熙常常说我聒噪,我跟他说你还没见过我真正聒噪的时候呢, 就算水房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也会不停唱歌,最深受其害的就是紧挨着水房的那间宿舍了。有一天中午她们时不时就 出来一个人上厕所,一进水房就狂赞我:“你唱歌好好听哦!”不幸的是我直到洗完衣服回到屋里才明白过来人家是 被我吵得不行了。
有人在的时候当然就更不得了了,我一定会逮着谁就跟谁猛侃。如果是不太熟的人,我跟人家说的话都还算正常,而 一旦遇到很熟的人,我就总免不了娶妻纳妾玩恶心,然后就不停有先前被我嫁娶过的人跑进水房来吃醋,引得水房里 一片尖叫大笑,伴着回声嗡嗡作响。
傅泠熙又气又笑道:“怪不得!”
我问他:“什么怪不得?”
他说:“大一的时候有一次上课前——我还记得很清楚,是上宪法,大课,一进教室就听到你坐在第一排甜甜地叫了 声‘宝贝儿’。我还以为你有男朋友了呢,刚怒目而视就听见岳萦嗲嗲地应了一声‘哎’,后来马上又发现她也是弄 错了,你叫的是那谁,就那回族女生,叫什么来着?总之大家眼瞅着岳萦就怒了,冲到你跟前指着你的鼻子就恶狠狠 甩了一句:‘哼,你这个人尽可宝贝儿的东西!’”
我捧着肚子直接笑倒。我记得那天的事儿,当时岳萦话音一落,整个第一排都齐刷刷笑趴了。
而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些人也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了,傅泠熙,他更已经是个故人。
结局一、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第29章 (上)
我回到家好几个月之后,才在一次契机中对我爸妈提起我和傅泠熙分手的真正原因。
我以为他们会为我而愤愤,不料他们听罢只是一阵静默。
然后,我妈对我说:“这也没什么的呀,大多数人都是想要儿子多过女儿啊。他也就是那么一说,你生气之后他难道 没给你道歉?”
我觉得不可思议,把筷子往桌上重重一拍:“妈,有人要你女儿去打胎耶!你居然觉得没什么?我是不是你亲闺女啊 ?这种事是道歉就可以了的吗?那我杀了人还道个歉就完事呢!”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是个小书记员,跟的法官是民事庭的莲恩姐。莲恩姐看起来既年轻又有气质,可她告诉我:“我 都30了,有个5岁的儿子啦!”
第一个给我介绍相亲的人就是莲恩姐,不过那已经是我们一起工作了两年、混得非常非常熟以后的事了。在那之前没 人给我介绍对象,毕竟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也有不少人追。
追我的人条件参差,良莠不齐,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某法官的儿子,他上来就说:“你是北大的呀?你真是北大的呀 ?不可能吧,北大有这么漂亮的女孩?漂亮女孩不是学习都不好吗?那你是不是北大的校花呀?”
听君此言,我很想把程佳影介绍给他,可是程佳影……
呵呵,她大概已经和傅泠熙修成正果了吧?
对了,一年后乔野淳毕业,也到桂林来了,工作比我好,在一家效益超卓的民营企业,后来他们公司上市,他少说也 是一夜变成百万富翁。这个数字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不值一提,可在我们这儿还是很有点份量的,何况他才刚 进公司不久,前途无量,俨然已是新贵。
我问他:“你怎么到桂林来了?清华的人不出国也得留北京上海呀!”
他反问我:“你还北大的呢,北大的人不也不出国也要留北京上海吗?你怎么回桂林来了?”
这孩子,跟我抬杠呢,他跟我能一样吗?这是我家,再说我当初不是失恋吗?
而且对于他而言,就算是回广西,那也应该是去首府南宁,或者他的老家柳州,好歹是工业城市,经济比桂林好,就 他的专业而言,发展前景光明多了。
后来莲恩姐给我介绍那人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给我们相亲。那天莲恩姐说约我去体育馆打羽毛球,有几个朋友一起 ,我就去了,到了才发现其实只有一个朋友,以及朋友的爸妈。
那小伙子家庭条件很优越,老爷子是自治区的高官,从高中起就把他送英国去了,现在29了才刚回来的,他妈妈特别 操心他的终身大事,恨不得他年内就马上娶一个回家。
莲恩姐跟那男生一起打羽毛球的时候,他爸爸妈妈一直在跟我聊天,很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妈妈特喜欢我,跟我说了一 通她儿子的感情史,中心思想是这小伙子条件好,历来都是富家千金倒追,可他没对谁太认真过,感情基本上还可算 是白纸一张。
其实我是挺招家长们喜欢的,我嘴甜,您别把我请回家发现我什么活都不会干还特懒不愿意学,那您一般都会觉得我 是理想儿媳。
后来大家一起吃饭,他妈妈甚至连这种话都说出来了:“北大毕业的在这里屈才呀!我们家小子也就是这两年在这儿 历练历练,然后就该提拔上去了,到时候他爸爸给你调自治区高院是分分钟的事啊!”
我有点明白了。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莲恩姐再跟我一说,就更明白了。
她说:“昨天那一家人对你都特别满意,我那朋友让我跟你说,要不你们就先处处看?”
我喷了。
不是说那男孩儿不好,不说别的,他的皮相就是我回桂林后见到的最亮眼的一个,气质谈吐也都没得挑,到底出身良 好兼以留洋多年;再看他打羽毛球的架势,也就不奇怪他年近三十还能保持那么挺拔紧致的身材。
可也许是我老了,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一看见傅泠熙就再也放不下的小女孩,虽然一直以来都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要 找个硬件不输于傅泠熙的,只要硬件不输于傅泠熙就可以考虑,可是现在再要动心,怎么连又高又帅这几个字都不够 了?
而且我还从来都没有过相亲的心理准备,早几年在最偏激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介绍相亲就跟给动物配种没什么区别。
尤其是这种一家人一起来的,我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他看上我了还是他爸妈看上我了。
莲恩姐觉得我不可理喻:“不都一样吗?再说让我问你能不能先处处这话是他自己说的,他能没看上你吗?哎我说, 你别走啊,我话还没说完呢……他爸妈看上你还不好?嫁过去你就是少奶奶,跟这种高干公婆处得好多不容易呀!”
我陪笑着回头对她称谢不已:“您费心了,不过还是算了吧。”
毕业两年半后,我第一次回北京出差。
冬天尚未结束,空气冷得凛冽,像冰凉的水一样脉脉涌来,无声无息将你拥抱和穿透。北京还是那么糟糕的空气,可 就是这个“还是”,让人的心为之溶化,因为他什么也没有改变,就好像一直都在相信你会回来、并等着你回来一样 ,尽管他什么都不说;而且,就是因为有缺陷,这缺陷让他显得那么憨厚敦实,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可怜,让你觉得更 得好好疼他了,更舍不得不留在他怀里用生命去陪伴他了。
再次站在北京的街头,我忽然想起这里曾经有一个男孩子,一次一次反复地对我说:不要,不要离开北京,扬扬,不 要离开北京,就留在北京。
不要离开我,扬扬,我在这里,留在我身边……
我悚然心惊地发现,原来,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
他一定早就知道一旦离开北京我会想念这里,会在再次踏上这方土地的时候心痛难言。一生之中最美丽的青春年华都 留在了这里,要我如何不把它当作另一个故乡?
他比我还清楚我的弱点在哪里,他一直都想要保护我,他心疼我,舍不得我有一点点伤心,他是为我好……
临去前已经联络了好些要好的同学,约好了到时候大家一起吃个饭。
本来还有点担心会不会很多人因为太忙而过不来,结果却发现我是最后到的一个。
到底是离开北京已经这么久,当初还在这儿的时候还是很少在校园外奔波的学生,如今对这里越发升级的堵车情况根 本完全没有概念。
可大家都那么准时,打开包厢房门时扑面一片温暖的笑脸。
也许这已是朋友的全部了吧,未必近在咫尺,却会让你无论在任何时候思念起这座城市,都知道有那么一群人,在对 你有所期待,当你回来的时候,有那么一片心,会收留你,并用不断漾开层层无尽的笑意,修饰着你的脸,和你的心 。
饭桌上见到了陈坤和茶果,他们俩刚刚领了证,准备五一办婚礼,那段时间他们新装修的房子还上了生活频道的一个 栏目,大家一见到他们就忙不迭地道喜称羡。
我当然没有找傅泠熙。
事实上,我已经没有他的联络方式了。
其他同学自然有,可我不问他们,他们也不会主动跟我提他。
其实三年来,一直有常常冒出一个念头:他会不会向同学们问起我?同学们会不会对他提起我?
具体到这一次,我老是忍不住地去猜测,直猜得自己心里像是有一只猫爪在不停地挠:
会不会有人告诉他我回来了呢?
我是不会主动去找他,可还是不由自主地希望他来找我。
哪怕只是隔着茫